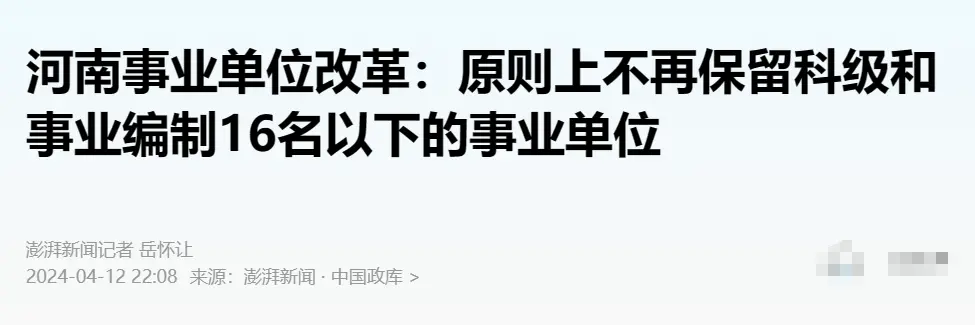走出苦难——根据孙占春同志的自述整理
前言: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中国人民灾难深重。一个家庭曲折的经历,可以说是中国从民不聊生到幸福安定的缩影。
孙占春,1933年生,13岁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岁因伤退伍,回到老家山东省莱州府掖县午城王家村(现莱州市朱桥镇盛王村)参加农业劳动。本文记录了他和父亲从挣扎在死亡线上到英勇不屈的抗争,从参加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到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走上安定生活的一段经历。
父亲孙常肖,1899年出生。因生活所迫,早年闯关东,曾经当过长工,参加过伪满洲国军,后来不堪日本鬼子的欺压,带了四、五个弟兄投奔了杨靖宇领导的红军。据他说,还认识赵一曼、金日成、李杜等抗日英雄和名人。可惜老人家八十年代已去世了,参加红军、义勇军、抗联的很多故事都成了谜,他在世时,我们仅听他讲了一小部分。
(1932年11月杨靖宇被派往南满,他按照中国工农红军的经验整顿当地游击队,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任政委。“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关于建立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精神传达到南满后,杨靖宇从南满实际出发,立即把这一指示精神贯彻到实际斗争中去,明确提出动员一切力量,联合抗日,改称抗日联合军,简称抗联。)。
由于日本鬼子残酷的扫荡,杨靖宇他们只剩下五十多人,被迫撤入深山老林坚持斗争。因父亲几次下山号粮(征集粮食)都很成功,在断粮的紧急关头,杨靖宇的警卫又指派他下山去找粮食。
日本鬼子将老百姓赶入“集团部落”(当时农民称之为“归大屯”)。“集团部落”,就是把散居各地的人家强行集中一处。周围筑两丈左右高的围墙,四角建炮楼,墙外挖壕沟,拉上铁丝网。驻扎警备队,有的是伪军,有的是日军。平时进出搜查,粮食、盐、布匹等等,凡是“抗联”需要的一切,严禁带出“部落”。人还要登记,叫“挂号 ”。来客人要“挂号”,串亲戚要“挂号”,不“挂号”就会被视为“通匪”。来客人要有“居留证”,串亲戚得办“行路证 ”,上山打柴,下河抓鱼,都得有证。
日本鬼子为了统治东北,极其残酷的镇压东北人民正义的反抗行动。一旦发现谁反满抗日,就将其全家杀绝,连小孩、亲属也不放过,名曰“连根拔”。
因有人告密,伪警备队在晚上突然包围了他落脚的岳父家,屋前、屋后都是敌人,我的母亲一看事情不好,赶紧将有关抗联的东西投入火墙中。因东北的冬天极其寒冷,每家每户都建有火墙不停地烧火取暖。伪警察冲进来后什么把柄也没发现,当场开枪打伤了我的舅舅,把父亲抓进了警备队严加审讯。
敌人为了从父亲口中掏出口供,对他使用了当时治安队所有的残酷手段。先是将两脚拧成螺旋状,父亲咬紧牙不招供,敌人又灌辣椒水、上电椅子,他一口咬定只是出去做生意刚回来。敌人一看也没有办法,只好将他暂时的押入大牢。
在监狱中,父亲有幸遇到了以狱医身份做掩护的地下党员(可惜不知真实姓名和以后的下落),这名同志鼓励他说:“老孙,你一定要坚持住,我想法给你把身体治好,救你出去“。
由于遭受残酷的刑罚,父亲的两只胳膊、两条腿如同散了架,痛苦万分,几次想自己了断。
每天早晨八、九点钟,日本鬼子都要杀人,有时一次杀四、五个。
重犯的牢房门口都有一个垒成锅台状但比家中锅台要小得多的台子,台子上面有自来水龙头,牢门上留有一个口,可以与外面的的人对话,送饭时狱卒点到谁的名,谁就将头探出来取,也可以把其它东西从这个口中递进去。口子的上、下各安装一个卡子。准备杀害人时,狱卒也点姓名,有的犯人不知啥事,探出头来张望,卡子迅速卡住脖子,发不出声音,刽子手戴着大皮套,身上缠着红布,一刀将犯人的头砍下,犯人的血流进台子上的凹状池子中,底部有孔,再用自来水冲洗血迹,从孔中流入下水道。
然后,鬼子指使监狱中的偷窃、诈骗等刑事犯罪分子用针和线把被杀害的抗日仁人志士的头胡乱缝到脖子上,头朝什么方向的都有,有的甚至缝到了朝后。尸体被扔上汽车运走,有的被曝尸示众,有的被拉到镇子西头喂了野狗。凶残的野狗如同日本鬼子一样,把尸体撕咬的七零八碎,惨不忍暏,以此来恐吓抗日的中国人。
1938年,通过疏通关系(鬼子也可能有想通过家属感化的目的),母亲曾经抱着五岁的我去探监。
看到了妻子和孩子,父亲悲痛地说:“我是活不出去了,你们娘俩快远走高飞吧”,说完就要把头从门的口子上伸出,来个自我了断,狱医一看急中生智,为了不引起鬼子的怀疑,从铁门的缝中伸进腿,一脚把父亲踢开,“你想早死,没门。”
父亲在监狱期间,母子二人一直靠要饭勉强活命,亲朋好友没有敢收留的。
因为鬼子什么证据也没找着,在狱医的周旋下,地下党采取了积极地救援活动,可是放了父亲又不甘心,就给父亲判了五年徒刑,后来又改为四年。
出狱后,靠四处打短工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计。因四年来的生活磨难、担惊受怕,母亲不幸积劳成疾,在父亲出犾后不久撇下我们爷俩洒手西去。我们只能砍倒仔粒还没有成熟的青高梁桔,把遗体包起来埋葬。
如果父亲出狱晚几个月的话,我可能沦为没有人管的孤儿也死掉了。
我成了没娘的孩子,跟随父亲四处漂泊,以后来到抚顺煤矿。父亲给鬼子养鸡兼给煤矿工人做饭,爷俩相依为命。
可是,这样的“好光景”也不长。一天,年仅九岁的我背着高梁米回工棚去,从把头的门口经过,一个日本鬼子挎着东洋刀,腰挂王八盒子枪,嘴里叽哩哇啦地打着手势,招呼我。我不知咋回事,心情非常紧张,惶恐不安的走过去。
原来是鬼子喝酒喝得酩酊大醉,两眼发直,口干舌燥,想找水喝。但是方圆周围根本没有可以喝的水,我连忙打手势解释没有水。
残暴的鬼子一把掌将我从额头刮到嘴巴下,瘦骨嶙峋的我怎能受得了,当场眼冒金星倒在地上,凶神恶煞的鬼子丧尽天良,一手握着我一只干瘦枯细的小脚,倒提着用力将我向门外摔去,摔过了二道铁轨,头部碰到了冰冷坚硬的铁轨上,昏死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估计可能有半个来钟头,铁轨开始震动,传来了火车开来的声音,随着火车的临近,车轨震动加大,我逐渐地苏醒过来,艰难的把身子翻到铁轨的外面,刚翻下不一会儿,火车风驰电掣般地急驶而过,就这样我捡了一条命。
父亲下班后看到我躺在工棚里不能动弹,赶忙问怎么回事?我一五一十地讲了过程,父亲差点要气炸了肺,又问高梁米哪去了?我回答说还在把头的屋里。父亲去把高梁米背了回来,看到鬼子象死猪一样躺在屋里睡觉。
父亲准备了一根一尺多长的铁棍,用布包起来,打算寻找机会收拾这个鬼子。开始几天,这个鬼子可能也心虚,煤矿中有十多个坑道,父亲从这个下去,鬼子可能从那边上来,一直没有下手的机会。父亲一想,事情不能太急,就不再去了。
日本鬼子只顾掠夺中国的煤矿资源,安全设施是不管不问的,电线拉的乱七八糟,坑道中支撑的木头有的已经腐朽的快要断了,这下正好可以利用。
一直等到了第十四天的晚上,坑道中的工人都集在一块吃饭,父亲看到这个鬼子下了坑道,就推倒了一根撑坑道的木头砸断电线,这时电灯熄灭,坑道中一片漆黑。
工人们都招呼没电了,鬼子不知怎么回事,打着手电深一脚浅一脚的到坑道中去查看。
父亲悄悄的从后面跟上去,将满腔的怒火集中到铁棍上,一棍将这个欺压中国工人、残害中国儿童的鬼子打的呜呼哀哉,结束了这条恶魔的狗命。然后把尸体放到坑道中的铁轨上,用轱辘马(运煤的矿车)从头上压了过去,制造了鬼子在黑暗中自己碰了矿车,不慎摔倒引起矿车滑动,造成工伤事故死亡的假现场。
父亲除掉这个鬼子后,迅速回到伙房,将铁棍藏了起来,把布条烧掉,继续做饭。
虽然铁棍用布包了,打到头上表面看不出外伤,但用矿车压的偏了一点,鬼子勘查现场验尸时还是有所怀疑。
一时间,宪兵队、伪警察如临大敌,各种先进的仪器及警犬都用上了,将工人逐个的审问,也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离开伙房这段时间只有一个中国把头知道,但他不清楚父亲到了哪里、离开多长时间。父亲警告他不要乱讲,如果冤枉了好人天打五雷轰,只要我不死就一定饶不了你。
这个平时欺压同胞的中国把头,不知是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还是被父亲的正气威风吓破了胆或是没有证据,连忙说:“老孙,你放心,我只知道你一直在伙房做饭,咱哥们不会给你添麻烦”。
鬼子一直也没有嗅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过了几天侦察有所放松,伪警察也撤走了。父亲想继续待下去会有危险,就找了个机会,领着我远远地躲到了乡下,靠抗长活、打短工维持生活,我则给大户人家放猪,挣口饭吃。
在日本鬼子的残酷统治之下,哪里有中国人的活路?在这个偏僻的乡村,又差点死在鬼子的屠刀下。
一天,父亲给人干活去了,我与一群七、八岁的孩子在一起玩,天真无邪的孩子们看到鬼子的马队(骑兵)在村头休息,好奇地跑过去围观,我吃过鬼子的亏,没有靠前,可是看到小伙伴们都跑过去了,迟疑了一会儿,也往那里去看光景。突然一个鬼子拿刺刀挑死了两个无故的孩子,其他几个孩子看到惨状,有的吓呆了不会动弹,有的转身就跑,其中一个被鬼子兵开枪从背后打死,夺去了稚嫩的生命。
有个年纪很大的日本兵,可能是被军国主义强征来的,看到这个血腥场面,踢了我一脚,用勉强听懂的中国话说:“你的,不要在这里”,又朝其他的鬼子示意了一下,鬼子不再开枪,剩下的几个小孩才捡了条小命。
1945年八月十五日,日本鬼子被迫投降,十四年的亡国奴生活结束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东北创建根据地,当时我军进入东北在国际上不事声张,而用东北义勇军的名义。父亲听说共产党的军队又来了,非常高兴。
9月20日(入伍档案上的记载)父亲找到了东北义勇军,自我介绍说:曾参加过杨靖宇领导红军和东北抗日义勇军。有个首长提了一些问题让父亲答,父亲回答后,首长认为确实懂得一些革命知识和军事知识、,又问擅长什么,回答说:我步枪、机枪、小钢炮都会,喊号子(队列训练)也比较拿手。首长说:“我们从山东赶过来,正在抢占地片,创建革命根据地,大力扩充革命队伍,干部紧缺,你就当排长吧”。
这样,十三岁的我也成了一名东北义勇军战士(先后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第四野战军),在连部当通讯员,身上挎上了一支小马枪,感觉非常的神气,每天到各部门传达命令,指导员有空时还教我识字、读书,给我讲精彩的战斗故事。虽然战争时期是艰苦和危险的,但对在日本鬼子屠刀下挣扎出来的我们爷俩来讲,还怕什么苦呢?
父亲看到八路军不但收留了爷俩,而且还让他当了干部,十几年前的豪气又焕发了出来。
可以理解,一个十几年来受尽日本鬼子的欺压,在迷雾中漂泊失散的老红军、老抗联战士,一个领着孩子到处奔波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遇到自己人的队伍发展壮大了,在革命的大家庭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该是多么的高兴!
可是,日本鬼子的残酷刑罚、四年监狱的非人折磨,再加上生活艰辛的摧残,使他力不从心了。这位当年抗日义勇军的连长,领着新兵咬牙坚持练了二天的队列,又找到首长请求说:“日本鬼子把我的腿和胳膊都拧坏了,给新兵做示范动作做不出标准的样子,全身痛的要命,再说我已经四十六岁,年纪也大了,看来练兵我是干不了,可是我当过厨师,就给同志们做饭吧”。
就这样,1945年9月底,爷俩被编入辽宁省军区后勤部,父亲当炊事员。以后又转至后勤部被服厂。
1946年10月,在四保临江的时候,由于当地老百姓对我党我军不了解,甚至还抱怀疑态度,我军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所到之处,家家关门,商店停业。战士们的吃穿都跟不上,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战士们身上露出棉花的破棉衣抵挡不住长白山的寒风,把草捆在身上御寒。部队一部分打了出去,开展敌后斗争,把敌后搞个翻江倒海解决给养,一部分进入长白山,来年春天带上锯子和绳子到山中开出一片空地,种上粮食,也种点大烟(鸦片)当药材。
有一次,部队用马车拉上收获的粮食出山,却遇上了胡子(东北称土匪为胡子)。当时胡子十分猖狂,有的大股胡子甚至上千人。这股胡子人数也不少,冲到了车队中,抢走了二马车的粮食,胡子看到我年纪小,把我抓到了车上,幸亏父亲枪法好,一枪一个,撂倒了几个胡子才把我救出,跟上大车队冲了出来。接应我们的部队战斗力很强,装备有小钢炮和机枪,打退了胡子的追击。
1947年3月转到修水河子卫生所、1947年10月四野后勤部警卫连工作。年代久远,好多细节记不住了,所幸的是参军后的档案还在。
1948年7月转四野后勤警卫团, 10月参加攻克锦州的战役。
有道是无巧不成书。打锦州前,有一天伙房进来一个连长,联系连队吃饭的事。双方一开口,彼此听出的说话口音相似,父亲问:“你老家哪里?”
回答说:“山东人”,“我也山东人”父亲说。
父亲又问:“山东哪里?”。
“莱州府掖县”来人回答说。
双方一听,在千军万马的战场上遇到了老乡,心情更加激动。
父亲连忙问:“你是什么村?”,
“午城王家村”
“我也是”,
“你叫什么名?”
“我叫孙常肖”
“哎呀,你是二哥,我是三弟呀”,双方抱成一团。
我三叔小时候跟随乡亲闯关东谋生,以后失去联系,家里认为早没有了。三叔说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在一次战斗中被解放军俘虏,成为解放战士。经过在革命的大熔炉里的锤炼,在战斗中成长,现在已是某部连长,带队准备参加锦州战役。
三叔问:“你这边还有什么亲人?”
父亲说:“只有你侄子了”,父亲把我叫过去,“快,快叫三叔”,三叔抱着我亲了又亲,说:“我们家有后人了,死了也不怕”。
在这一段时间两支部队靠在一起,可以说是三人陶醉在亲人相见的喜悦中。
在十几天后的攻克奉天(沈阳)的战斗中,三叔他们那个连担任主攻,大部分伤亡,全连只剩下了两个人,从他们口中得知了三叔不幸英勇牺牲的过程。因三叔是在东北参加的解放军,家中根本不知道,所以成了无名英雄,因而解放后家中也没有享受烈属待遇。
辽沈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急令四野百万大军迅速挥师入关,只得在入关的路上整顿、总结部队。
有几次在电视上播出四野大军南下的记录片,上面有个炊事员挑着担子,很像我父亲,当然不一定碰得那么巧,正好让记者照下相片。也可能不是,因为当时的炊事兵很多是挑着炊具行军的。
后勤部得到苏军援助的二十部轻便的嘎斯车,国民党不知从哪儿得到的情报,天天派飞机轰炸。
有一天,正逢集市,路被赶集的人堵住了。先是来了一架侦察机转几圈,不久又来了四架战斗轰炸机。俯冲时扔下炸弹,又打了一串机关炮,我和战友们招呼群众快卧倒,忽然觉得帽沿在冒烟,摘下一看,被机关炮穿了一块去,弹头从脚尖边穿入地下,打起尖土,留下一个弹洞。
往前跑了不远,听到“轰”的一声巨响…….
飞机飞走后,各连赶快清点伤亡情况,有人发现我不见了,连长组织战友们去寻找,在炸弹坑不远处发现一条人腿露在外面,拽出后才知道是被炸飞的。再仔细一看,下面还有一条人胳膊,拽也拽不动。战友们一齐动手,很快扒出一个土人,除去土一看,有眼快的战友惊呼:“是小孙!”。
军医过来听了听,还有口气,挖去我耳朵、鼻孔中的尘土进行抢救,过了一会儿活了过来。
经分析,炸弹是在我后方爆炸的,巨大的气浪将十五岁的我掀到空中,又被落下的土掩埋。要不是发现的早、抢救的及时,也就“光荣”成小烈士了。
抢救我的军医是日本人。第四野战军在抗战胜利后收编了很多日本工程技术人员。我们的军医和护士里面有许多日本人,他们技术非常高,在我党、我军的教育和感化下,同我军一样吃苦耐劳,不怕流血牺牲,对待受伤的战友照顾的无微不至。
我们的解放军队伍真是法力无边,不但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把我这样的流浪者由文盲培养得能读书看报,有一定的思想觉悟的战士,而且还能将昔日的战争对手、法西斯分子转化成我们队伍中的一员,将魔鬼改造成人甚至可以改造成天使,为解放全中国抛头颅、洒热血。
人民军队是多么伟大啊!用宽广的胸怀、无比的真诚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俘虏过来的日军逐渐认识到侵华战争的罪恶和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从而自愿自觉接受改造,并最终选择投入人民军队温暖的怀抱。 能将最凶残、最顽固的敌人感化、改造成自己最信赖的同志、最忠诚的战友。
在战斗生活中,我们与这些日本战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安排他们回国时,我们恋恋不舍,我与许多战友流下了泪水。
后来听说有原在四野解放军的日本人曾回中国访问,不知有没有我以前认识的日本战友。
部队为了避开敌机轰炸,晚上行军,白天开会、学习。
连长命令我照看生病的排长,开车的司机白天得不到很好的休息,疲劳过度,加之晚上开车走山路,看不清楚路况,不幸出现翻车事故,排长和两个护士扣在车下牺牲了。我身子被摔在车外,肩膀压在车厢的框下,虽然经军医精心治疗,但因伤势过重,战争年代医疗条件所限,左胳膊失去了大部分的功能,成为残疾人。
1949年3月,转后勤部辎重二团。12月转四野后勤司令部。
我们部队且战且进,一路凯歌南下到广州。以后随大部队解放了海南岛。我们尽多在海南岛待了六、七天,奉上级命令北上武汉,被安排在中南军区后勤部机关直属队,安排我负责接电话、传令等较轻的工作。
1950年10月,转四野后勤留守处。1951年3月四野后勤高干队。
在部队上。因为年纪小,比较机灵,干部、战士都很喜欢我。在解放军这个大学校里,学到了文化知识,虽然一天正规的学校都不进去过,但是读书、看报和写信,一点也不成问题。我的老师,在作战部队时是待我亲如兄长、爱若父辈的指导员;在机关时是我所敬爱的科长、秘书们,他们都热情地教我学习文化。
1952年,虽然抗美援朝战争还是继续,但国内各行各业的经济建设已经掀起高潮。父子俩人一老一少需要转业到地方工作了,上级征求我们的意见,是到新疆建设兵团还是复员回山东老家。当时家中的祖父、祖母来信说,给我们家分了房子和地。首长说,到建设兵团去吧,刚去时可能艰苦一点,但长远来看,毕竟军队的条件能更一些。
父亲考虑到,从开始闯关东到全国解放已经离开山东老家接近三十年了,我这个出生在东北的孙子已经十九岁了,还没有见过爷爷、奶奶,现在家中又有房子又有地,决定我们俩人一起转业,回到了山东省掖县午城区王家村(现莱州市朱桥镇盛王村)。
离开部队时,上级动员我们残疾程度较轻的同志,将来要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自觉将残疾等级降级,以便减轻国家的负担,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同志都这样做了。我最后被评为“三级甲等”残疾。
回乡后,虽然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生活比较清贫,但毕竟比旧社会不知要好了多少倍。现在,国家为我们这些战争年代流血流汗的老同志,每月都发生活补贴,让我们过上了幸福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