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史修了二十多年,还出不来?
清史,修了二十多年,依旧没有一本真正的“定本”面世。有人说,学者能力不行,资料太多整理不过来,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现象。真正的问题是——“怎么写”,在逻辑上早就卡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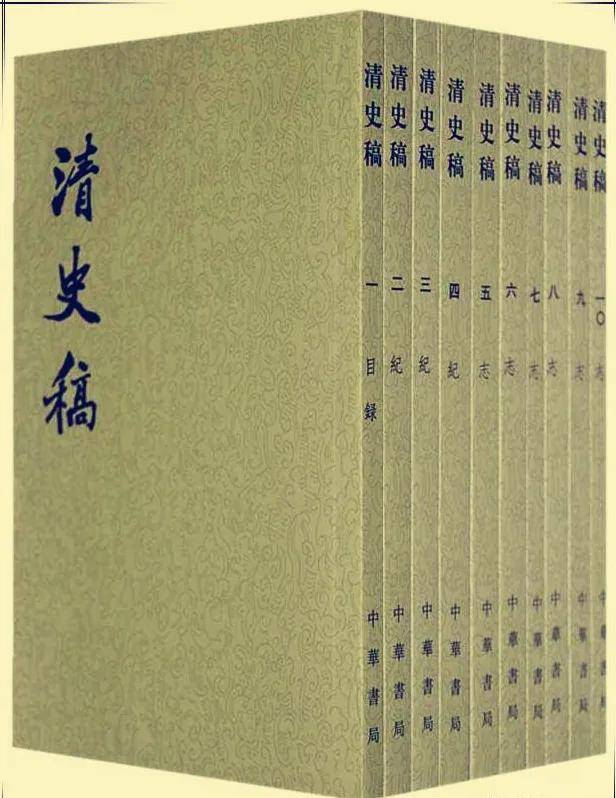
从2002年国家启动清史纂修工程,到今天整整二十余年,三千多万字,近十亿字史料,像一座史学金字塔,但最后连盖棺定论都不敢。为什么?因为这是一块烫手山芋,烫到手心发烫,烫到没人敢握稳。
先别急着说历史无用,先问一个现实问题:为什么非得修清史,而且还得“修得漂亮”?“漂亮”的意思,不是文学好看,而是符合国家利益,政治正确,又不伤害民族感情。听上去很简单?那你就低估了这事的复杂度。
翻开明朝地图,你会发现一个很尴尬的事实:所谓疆域,其实不完整。东北大片,蒙古草原,藏区,甚至西南羁縻地区,明朝几乎没管到。清朝呢?《尼布楚条约》之后,1300多万平方公里帝国版图初步成型,现代中国的疆域基础,几乎就是从清朝继承来的。如果清朝被定性为“外族殖民政权”,现代边疆法理就会打折扣。清史的第一条逻辑线就是:为了国家版图完整性,必须承认清朝正统性,而不是单纯的异族入侵。
然而,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第二条逻辑线,是情感层面——民族记忆的创伤。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历史伤痕,早期革命史观里,清朝就是侵略者,是非我族类,要打倒的目标。可现代团结史观强调56个民族是一家,这就带来了深层矛盾:你不能一边说大一统、一边让汉人被清军屠戮的历史消失。
于是,修史者面对一道选择题:史可法、阎应元的抵抗,应该怎么写?尚可喜、洪承畴、吴三桂投降或引清入关,又该怎么定义?有人甚至提出把尚可喜包装成“顺应潮流的民族英雄”。听上去荒唐吧?可这就是历史与现实撕裂的结果。
如果把三条逻辑拿出来排个优先顺序,你会发现:实事求是、团结史观、人的良知——三者最多选其二。你想既维护事实,又保证团结,还让所有人良心安稳?抱歉,这不可能。清史本质上就是一场逻辑上的不可能三角。
更麻烦的是,国外的声音一直存在。以美国为首的新清史学派,把清朝解读成一个多元帝国,而不是汉地政权的延伸。他们强调满洲、蒙古、西藏的地位,把“中华”与“清朝”剥离开来,这在国内几乎是绝对禁忌。强调多元和强调团结,本质上是镜像关系——过度强调清朝的多元性,给外界提供了解构中国的钥匙。
如果你对这个逻辑链再细致一点,就会看到清史的尴尬:阶级史观?那清朝是封建地主和满洲贵族联合压迫,团结就打折。汉本位史观?那清朝是殖民政权,领土法理受损。团结史观?那清初投降、屠杀同胞的刽子手,也许就可以被合理化。选择哪条路,都是踩雷。
清史还不仅是文字工作,它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三千多万字的稿子,最终卡在了“过审”上。因为一旦盖棺定论,官方必须为逻辑漏洞背书。更现实的风险是,如果哪条逻辑稍微歪一点,被外界或者国内的不同群体拿来批判,政治成本太高。于是,最安全的方式,就是让它永远处于“在修”的状态。
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更是文化与政治的现实博弈。高大上的文化工程,最后往往以沉默收场。历史书,能盖得住真相吗?往往不是,因为历史从来不会温顺,它比任何政治需求都更顽固、更真实。
看看教科书里的民族英雄施琅,你会更明白这个问题。施琅平定台湾,剿灭海寇,是清朝忠臣。但为了剿灭郑氏政权,他联手荷兰殖民者。历史上,这叫“引狼入室”,在当地百姓眼中,他就是汉奸。站在“大一统”的叙事下,他又是统一的功臣。评价的尺度随着视角移动,游移不定。
这种游移甚至波及“侵略”的定义。清兵入关算不算侵略?如果清朝是正统,入关不是侵略;如果清朝是殖民政权呢?当年日本的大东亚共荣理论,声称自己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被我们坚决唾弃——这逻辑一旦用在清朝身上,又会变成另一种荒谬。
再细想下去,你会发现一个可怕的事实:我们对清史的处理,实际上在不断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认知基础。如果清朝手段过度美化,抵抗外侮的道德正当性也会被稀释。日本当年的话:“崖山之后无中华,我们是来帮你们恢复王道的”,放在清朝逻辑下,有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熟悉感。
所以,清史争议之大,并非史料问题,也不是学者不努力,而是我们还没有想好,面对那段“长着辫子”的历史,要用什么样的灵魂。
我们对清朝的认知,还在被情绪、现实、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绑架。修史者每写一个字,都可能触碰某种政治雷区,每翻一页,都可能撕裂某段民族感情。于是二十多年过去,三千多万字稿子仍然在案头晃悠。
更讽刺的是,这场史学大工程,最终成了政治安全的“缓冲器”。不出版,不定论,就是最安全的选择。出版了,哪怕写得再精准,都会被质疑、被拆解,甚至成为舆论工具。古往今来,文化工程中这种“悄悄束之高阁”的现象,从未缺席。
说到底,清史不仅是书写过去,更是面对现实的投影。它反映出:我们如何在历史事实、政治需求、民族情感之间找到平衡,而事实是,这种平衡几乎不存在。每一条史料,每一个人物,每一次战争,都可能引发逻辑裂缝。
这也是为什么修清史的难度,远远超出普通人的想象。它不是学术能力的问题,也不是勤奋的问题,而是你必须面对三个层面的冲突:现实利益、情感认知、道德判断。三者交错,形成一个没有出口的迷宫。
最终,我们可以总结一句话:清史之难,源于我们对历史的近距离恐惧。它离我们太近,近到辛亥革命的合法性仍挂在它的尸体上。我们对它的每一次评判,都不是对过去的纯粹认知,而是在与现实、情感和政治的拉锯中自我折磨。
上帝没有留下完美的史观,只有充满补丁的解释包。后人选哪一条路,都是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妥协。而清史,更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的历史观、价值观和逻辑能力的不足。

所以,修不修清史,永远都是一场博弈。三千多万字的稿子,如果真的出版,无疑是政治勇气与学术能力的极限考验。至于它最终会以何种形式面世——没人知道,也许它永远停留在“在修”的状态,成为一块烫手山芋,警示后人:历史,不仅是过去,更是当下的试炼场。
而读者你会发现,清史不仅仅在讲一个朝代,更在拷问我们:面对复杂的历史与现实,你能承受多少矛盾?你能容忍多少逻辑裂缝?你又能否在情感、道德与国家利益之间,找到哪怕一点点平衡?
清史之困,注定不是学者的孤独,而是整个时代的镜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