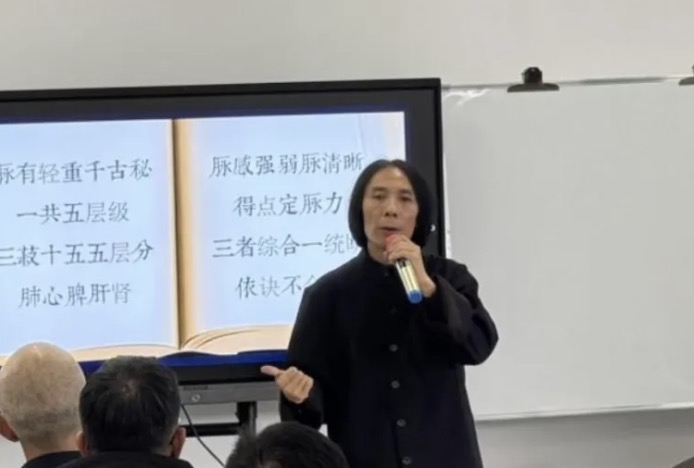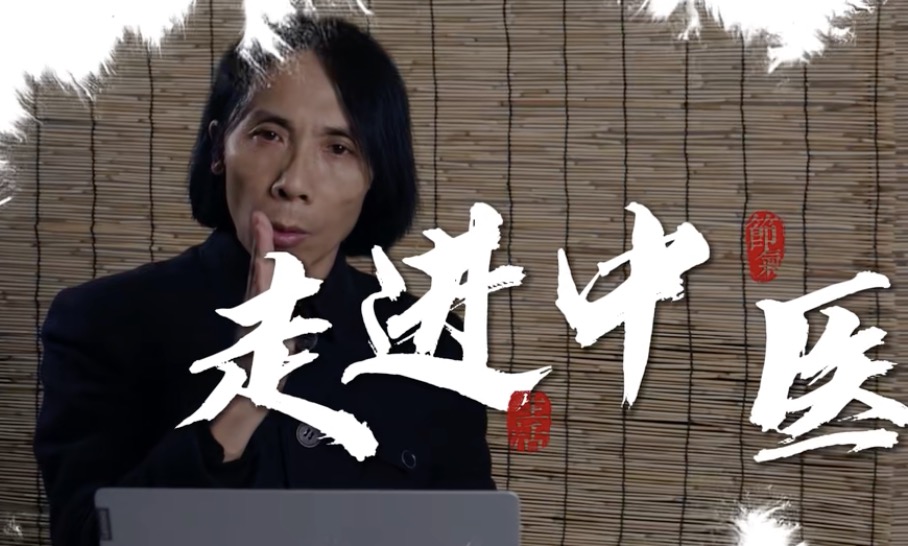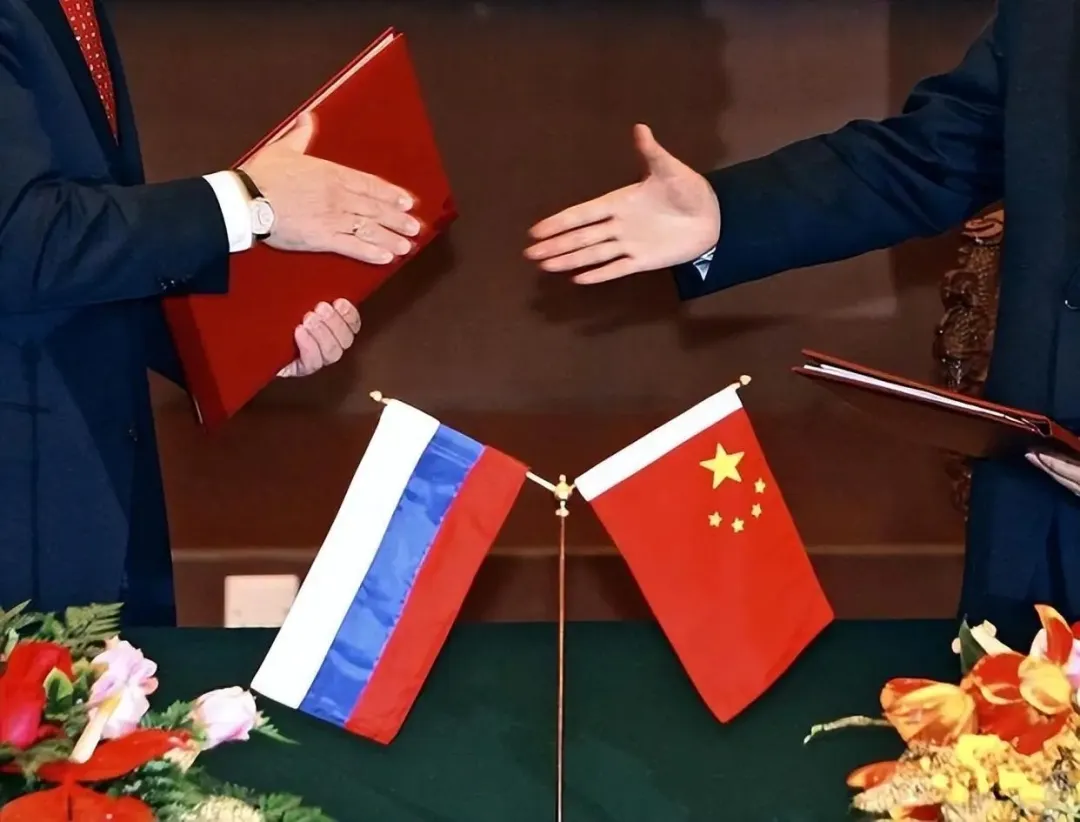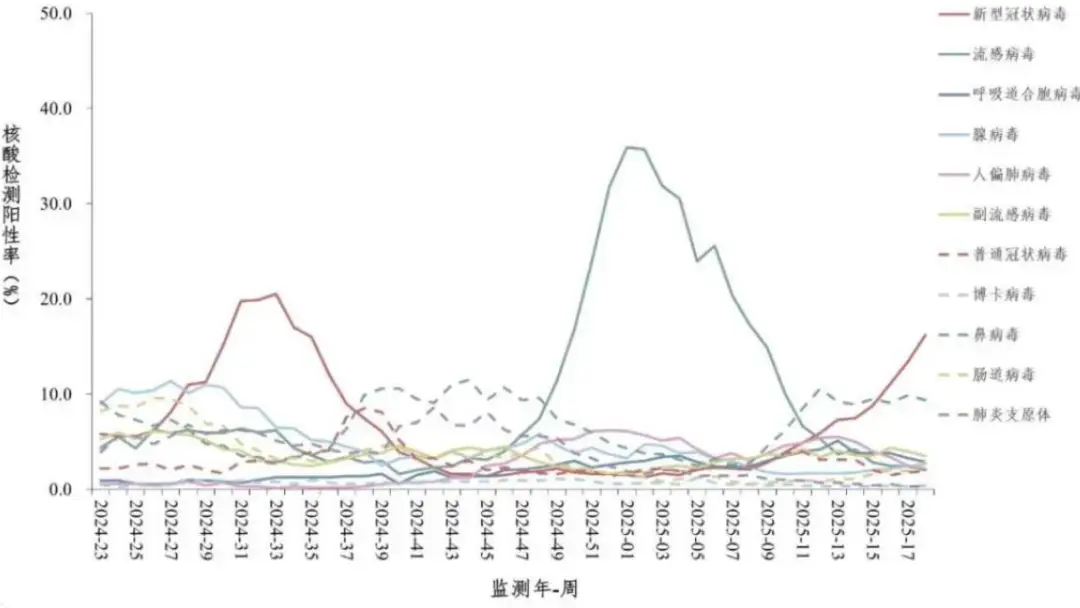石家庄一中医院“中药液”涉嫌添加安眠药,官方通报:立案调查
14:05:27 热点热搜 记者
“争气机”歼-10为何再次牵动世界的目光
14:05:09 时事财经 记者
我们对天龙人的要求越来越低,但天龙人的底线也越来越低
14:05:10 自媒体号 倪刃
毛主席的医疗路线才是中国老百姓的底线
14:05:16 评述毛泽东 教员的追随者
在京东当外卖员的调查情况
10:05:14 工友之家 我在深圳做保安
列宁同志是如何度过人生低谷期的?
10:05:40 历史 莫斯客
现在很多的瓜,都是自己炫富暴露的
10:05:36 自媒体号 徐鹏
时隔近12年,党中央修订这一重磅文件,有新变化
08:05:41 时事财经 余晖
拜登确诊前列腺癌,癌细胞已扩散至骨骼
08:05:01 国际观察 记者
胡锡进:演员戴疑似天价耳环炫富事件
08:05:58 时事财经 胡锡进
乌军F-16突然坠毁!细节曝光
08:05:53 国际观察 记者
上滑加载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