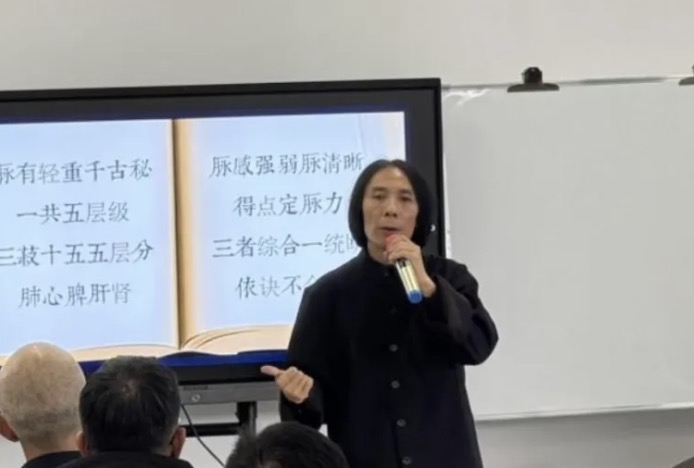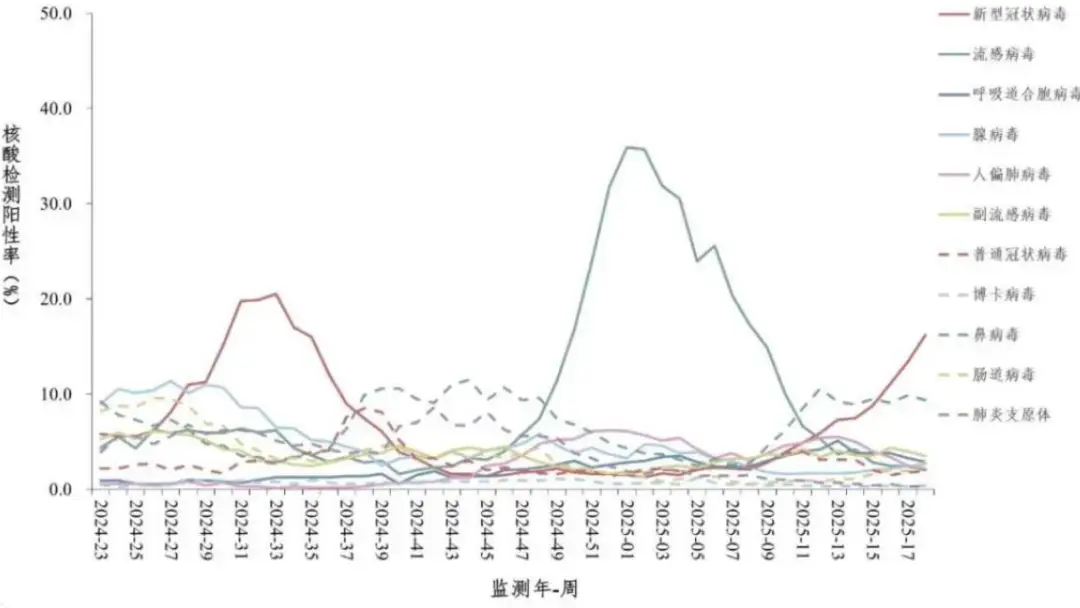11:05:58 时事财经 胡锡进
11:05:53 国际观察 记者
11:05:41 时事财经 余晖
10:05:36 自媒体号 徐鹏
10:05:14 工友之家 我在深圳做保安
10:05:40 历史 莫斯客
08:05:01 国际观察 记者
05-18 18:05:44 时事财经 记者
05-18 18:05:12 国际观察 记者
05-18 18:05:22 时事财经 记者
05-18 18:05:12 时事财经 记者
05-18 17:05:29 学者观点 张文木
05-18 14:05:57 网友杂谈 教员的追随者
05-18 14:05:42 历史 陈红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