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这次到韶山,是凭吊之旅、寻根之旅和汇报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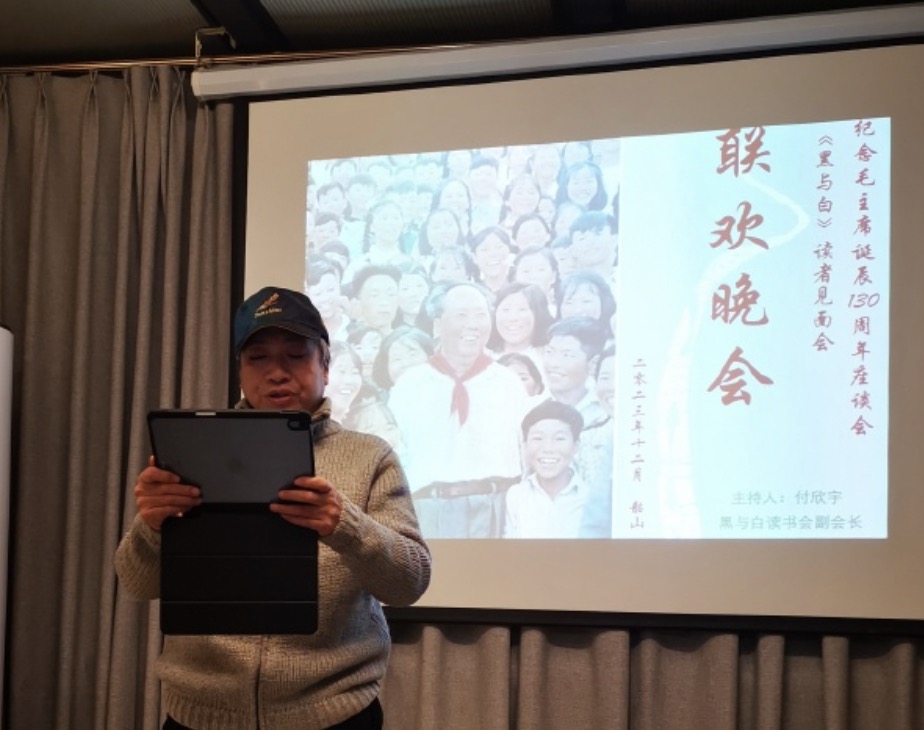
今天,我们相聚在韶山,纪念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诞辰130周年,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从素不相识到亲如家人,这都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毛主席。我相信各位跟我一样,心情都很激动。刚才,余义伟先生的致辞已经把这种心情表达的很充分。这里,我想跟大家讲讲我几次到韶山的经历。
我不知道各位都是第几次到韶山,在座的有不少年轻的同志和大学生,我从参会人员名册上看到最小的才十九岁,这些青年可能是第一次到韶山,年长的同志可能就不只是第一次,比如我就是第三次来韶山了。
我是60年代出生的,已进入花甲之年。在座的还有不少同志是50年代生人。总的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青少年时代对人的一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以及人格的塑造在青少年时期就基本上形成了,所以我们这代人对毛泽东时代以及毛主席,始终怀着一种近乎神圣的感情,这种感情,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很难理解的。
正是由于对毛主席的这种感情,韶山在我们心中也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韶山不仅是毛主席的故乡,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而且是中国乃至世界革命的圣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韶山和井冈山、延安一起被称为三大革命圣地,从全国以及世界各地来韶山朝圣的革命群众不计其数,文化大革命期间,韶山更是成为了红卫兵串联的首选之地。那毛泽东时代,歌颂和描写韶山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最有影响的如歌曲《火车向着韶山跑》,散文《韶山的节日》、《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韶山的节日》的作者是创作过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的著名作家周立波。此外,著名画家李可染、傳抱石、关山月、吴冠中、黄永玉等也都创作过以韶山为题材的美术作品,其中如黄永玉的《毛主席的故乡韶山》,现在在市场上的价格高达数千万元,其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这代人对韶山的特殊感情,与这些文艺作品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但这种影响到八十年代初就戛然而止了。八十年代,是非毛化最严重最猖狂的时期,随着文化大革命被全盘否定,伤痕文学的盛行,毛泽东时代(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前三十年”)和毛主席本人成为了右派精英们集中攻击和诬蔑的重点目标。在许多文人笔下,毛时代比解放前的旧中国还要黑暗贫穷,毛主席比封建皇帝还要昏康无道。所谓“饿死三千万”的谎言就是在那一时期出笼并流布到全世界的。右派文人们一边想方设法贬损毛主席,一边企图制造出新的“偶像”来取代毛主席在人民心中的地位,例如他们把周恩来塑造成了政治和道德上的完人,一提起他就是“敬爱的周总理”,以至敬爱一词仿佛特指周恩来。而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敬爱”这个词是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专称,如“敬爱的毛主席,心中的红太阳”,“英明的统帅,伟大的领袖,敬爱的毛主席”等等。精英们一面宣称反对个人崇拜,一面制造他们自己的偶像,他们就是这样通过贬低毛主席进而达到篡改历史的目的的。
八十年代末,我正在上大学。当时在武大开讲座的专家学者,没有不控诉文革攻击毛主席的,而且听讲者座无虚席,场面十分热烈。所以现在反毛最狂热最顽固的就是在八十年代接受大学教育的这批人。这批人至今在体制内特别是知识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样的氛围一直持续了整个八十年代。也就是在八十年代即将结束的那年,我第一次到了韶山。我是和几位同学一起到的韶山,在那种氛围下,我们并不是像六、七十年代的人们那样,怀着对毛主席的崇敬和朝圣的心情来到韶山的,仅仅是当作一种旅游,而且还因为韶山距武汉比较近,交通便捷。当时的韶山没有任何旅游设施,纪念馆、铜像广场等等都还没有兴建,看上去跟普通的山村没有什么区别,去毛主席故居参观的人也寥寥无几,我想起小时候从新闻和文艺作品中看到的那种熙熙攘攘、络绎不绝的场景,心里有一种怡然若失的感觉,这使我的第一次韶山之行,仿佛是对自己的少年时代和消逝已久的毛泽东时代的一种凭吊和缅怀。离开韶山前,我和几位同学在毛主席故居前面拍了一张合影。这张合影至今保存在我的相册里。
我第二次到韶山,距第一次到韶山过去了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不仅中国和世界发生了翻天震地的变化,我自己的生活、写作和思想也发生了许许多多始料未及的变化。其中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从九十年代的先锋写作,在21世纪初开始向“底层写作”转向,思想也逐渐从自由主义转向“新左派”,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新世纪初到一零年代中期我的一批中短篇小说、随笔文论以及长篇小说《人境》。
2016年的12月,我第二次来到了韶山。那时,《人境》刚出版不久,我的写作越来越与主流文坛格格不入,我像一个脱离部队的散兵游勇,在与主流文坛渐行渐远的同时,尚未找到新的归属,心里有一种孤独彷徨的感觉。此时,我同文坛极右势力和腐败团伙的斗争大幕已经拉开,面对比我强大得多的对手,我预感到即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因此,我这时候来到韶山,多少有一种寻找精神力量的愿望在里面。
与第一次到韶山不同,我第二次到韶山是只身一人。由于是毛诞节,韶山的大小酒店都人满为患,我好不容易才在铜像广场附近一家简陋的客栈里找到住处。
那次,我是12月25日到韶山的。从武汉到韶山乘坐高铁.2个小时的车程,上午10点多钟就到了。我连午饭都顾不上吃,便有点迫不及待地向广场走去。中国人传统的祝寿时间一般是从前一天下午和晚上,一直到次日,由于刚刚中午,广场上的人零零星星的,长方形的广场显得有些空旷,也使矗立在广场上的毛主席铜像,在苍松翠柏的衬托下显得格外高大挺拔。
我见时间还早,便去广场旁边的小餐馆吃午饭。花了也就半个小时吧,当我再次回到广场时,发现人忽然多了起来,刚才还有些空旷的广场上变得人头攒动,熙熙攘攘,通往广场的每条道路和入口像打开了闸门的水渠,人流一拨拨、-股股地从四面八方向广场汇聚而来,几乎是一眨眼的工夫,广场上就变成了一片人的海洋,人们穿着不同的服装,操操不同口音,男女老幼,成群结队,有稚气未脱的少年,有耄耋之年的老人,每个人脸上都浮现出庄重的表情,这是农村给老人祝寿时常见的那种表情。不断有人抬着花篮在毛主席铜像前举行隆重的敬献仪式,但大多数人都是合掌肃立,以中国人最朴素的方式,向毛主席铜像三鞠躬,绕完铜像一圈,也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继续在广场上流连徘徊。
这时,我看见靠近铜像的石级下,有两男一女三个人,其中一男一女约莫五六十岁,另一个男的年轻些,30多岁的样子,脸色粗糙黝黑,像是来自于农村,他们向毛主席铜像并肩而立,双手合掌放在胸前,像是在祷告,满脸肃穆的神情,面前地上还放着一包打开的香烟,年纪大的男人单膝跪地,显得异常虔敬地点燃一支烟,放在石级上,嘴里一边轻轻念叨:“毛主席,晓得您老人家爱抽烟,我给您买了包烟,您抽吧!”活音未落,旁边那个女的扑嗵一声跪下了,连叩了三个头,抬起头来时,多皱的脸上已经泪流满面……
我被这个场面震撼了,正想过去跟他们攀谈几句,突然过来一个维持秩序的警察,要求他们离开。但他们沉默着,站在原地没有动,警察大声喝斥,态度粗暴地挥着手,做出驱赶的样子。地上那支香烟还冒着袅袅的青烟。我上前质问那个警察,他们在这儿妨碍了广场的秩序吗?警察听了一愣,回答不上来。这时又有几个人围上来,警察见状,只好离开了。后来,当我在广场上转了一圈回来,见那三个人还站在石阶下,朝毛主席铜像肃立着,面前还放着那包香烟,那支点燃的香烟只剩下一堆余烬……
那天晚上,我在铜像广场一直待到后半夜,此时的广场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铜像前面的花篮摆了一圈又一圈,工作人员刚称走,很快又摆满了。人们放起了烟花焰火,绚丽璀璨的焰火照亮了黑沉沉的夜穵,也照亮了高大巍峨的毛主席铜像。人们高举毛主席的巨幅照片,打着写有“毛主席,我们想您!”“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社会主义好!”等标语的横幅,列队从广场上走过,一边呼喊口号,一边唱着颂扬毛主席的歌曲,深情嘹亮的歌声波浪一般此起彼伏,传到很远的地方。歌声将铜像广场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人们把12月26日这一天当作了自己的节日,人民的节日。我脑海里又浮现出给毛主席敬烟的那三个人的影子。从他们以及千千万万汇聚在韶山铜像广场上的人身上,我强烈体会到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对毛主席那种亲人般的感情,这种感情已经上升为信仰,具有一种超越时空的力量,深深融入到了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心中,成为最可宝贵的一种民族精神。我忽然感到心里沉睡已久的记忆被唤醒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回到了人民中间,如同一个在外面浪迹多年的游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那次的韶山之行,让我从彷徨和迷惘中走出来,仿佛经受了一场灵魂的洗礼,开始真正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这个信仰就是马克思主义或马列毛主义。2020年,我在一篇《要为真理而斗争》的访谈中说,在经历过2017至2020年的那场斗争之后,我已经从一般意义上的“左派”,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今年,我在毛主席诞辰130周年之际第三次来到韶山,无论是形式和心情,都与前两次有了很大的不同。《黑与白》的主人公王晟经历了左一右一左的三次思想转变,对我来说,三次到韶山,也见证了我从一个迷惘者到信仰者的思想转变过程。如果说前一次我是来韶山寻找精神力量,是寻根之旅,那么,我这次带着《黑与白》来韶山,则是一次汇报之旅,我是来向毛主席汇报的。昨天在铜像前献花篮时,我就在心里对毛主席说,作为您的一名小学生,我合格吗?我这些年的所思所写和所做的一切,您满意吗?
我不知道毛主席会怎样回答。但无论怎样,我都将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永远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为人民写作,为人民呐喊,像魏巍老前辈在遗嘱中说的那样,继续革命,永不投降!
最后,我以一首小诗作为结束语吧:
红朝旌旗奋,
导师暮年泪。
黑白四十载,
梦醒已无痕。
谢谢大家!
【文/刘继明,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