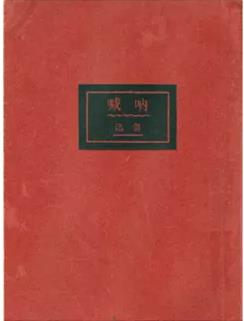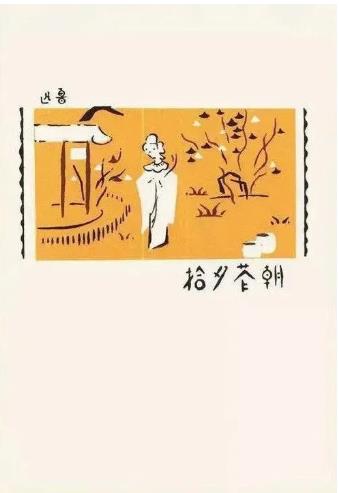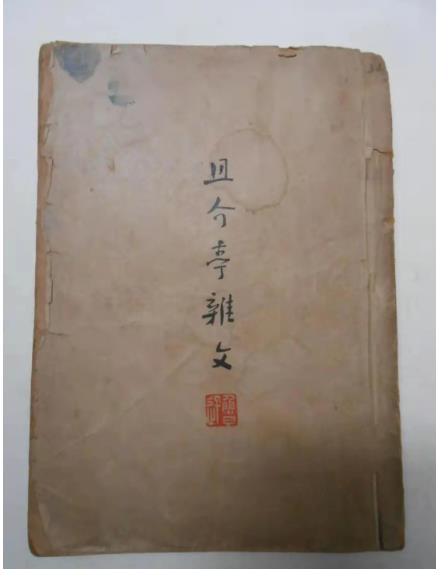【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从体制人到革命人:鲁迅与“弃教从文”
编者按
今天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的日子,保马推送《从体制人到革命人:鲁迅与“弃教从文”》一文以示纪念。
鲁迅先生曾在教育界任职十八余年,自1927年从中山大学辞职后便再未涉足教界,这不仅是他的一次人生转折,于学界而言也具有深刻意义。在保马今日推文中,张洁宇老师结合鲁迅先生二十年代后期的思想和经历,重新审视“弃教从文”的前因后果,为研究鲁迅对 “文”和“从文”方式的观念认识提供新思路,给予了读者一些关于革命与体制之间张力存在的思考。确实,在那样一个充斥双重暴力风雨的大革命时代,知识分子面临着难以承受的困境与痛苦。所幸,独立精神在裹挟中艰难崛起,作为知识分子代表的鲁迅,转移阵地后为自己开辟了新的战斗路径,那么,从“体制人”到“革命人”这一身份的转变,是脱离政治还是对政治的新的回归?是对体制的反抗还是一种在革命与体制之间创造新的历史可能性的尝试?这一转变所体现出的知识分子与体制和权力的关系,并没有随着鲁迅先生的离开而消失,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变得愈加紧迫,值得进一步摸索探寻。谨以此文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
本文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4期,感谢张洁宇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从体制人到革命人:鲁迅与“弃教从文”
文 / 张洁宇
引言
鲁迅一生“走异路,逃异地”,在“本没有路”的地方孤独求索,其路必多阻难和曲折。但正如毛泽东所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1 鲁迅的道路——无论是通途、弯路还是转折——也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道路的代表,即便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现实环境中,始终具有反思和借鉴 的意义。
关于鲁迅一生中的转折与选择,无论是他本人还是研究者都非常看重1906年的“弃医从文”事件。在《呐喊·自序》中,他将之描述为人生道路的一个重大转折,“想提倡文艺运动”的念头从此终断了他的医学梦想,开启了一条漫长的文学道路。但是,前些年就有研究者指出:“在鲁迅一生中,还有一个重大的转折,那就是在文学与教育之间的徘徊与抉择。” 2 姜彩燕在《从“弃文从教”到 “弃教从文”——试析鲁迅对教育与文学的思考和抉择》一文中提出:“从1909 年鲁迅迫于生计‘弃文从教’,到新文化运动开始文教两栖,再到1927年的‘弃 教从文’,鲁迅终于彻底回归了青年时期立下的志向:文学。”这个回归,既体现了他对中国教育历史与现状的失望和批判,同时也说明了他“始终把写作看作 ‘志业’,而教书只是‘职业’”。该文对鲁迅“人的文学”与“人的教育”观念的相互渗透分析得甚为深入,呈现出鲁迅文学启蒙思想与现代教育理念之间的 关系。遗憾的是,该文发表后至今,对于鲁迅“弃教从文”的关注和进一步研究仍不多见。本文重拾这一话题,意在结合鲁迅1920年代中后期的经历与思想,重 审“弃教从文”的原因和意义,尤其关注其与鲁迅“左转”之间的关联。在我看来,“弃教从文”与“左转”确需放在一起讨论,前者是生活和斗争方式的选择,后者是思想立场的变化,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伴相辅、互不可分的关系。换句话说,生活与斗争方式上的“弃教从文”为思想上“左转”的完成提供了准备,而思想上的逐步“左转”又为“弃教从文”的过程提供了动因与推力。
鲁迅,《呐喊》,新潮社出版,1923年。
鲁迅并不讳言自己思想的转变,他对生活道路的每次选择也都深思熟虑。他后来坦言:“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 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此外,他还表示: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3 正如有研究者所提出的:“鲁迅的话实际是在说明自己的转变,早在1927年广州清党时就已经开始,正是对这场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的幻灭,促使他寻找新的道路,而革命文学论争只是一个促动而已。” 4 可以说,1927年的离开 广州“弃教从文”,是鲁迅人生中的又一极为重要的转向,其意义甚至不亚于二十年前的“弃医从文”。因为,弃医从文是鲁迅的自我启蒙,是他从科技现代化道路转入现代思想启蒙阵营的标志;而弃教从文既是从思想启蒙和个性解放的立场转向政治革命,同时也包含了对于现代社会与知识分子本身的深刻反省,是在整体化的现代性道路上开辟出一条更明确、更现实的文化革命之路。两次转向 相比,前者仍内在于启蒙时代现代知识分子道路选择的洪流之中,带有明显的时代共性;而后者则不仅更体现出现代中国的历史复杂性和现实的具体性,同时也更体现出鲁迅本人的思想与性格的独特性。
蒲力汗诺夫,《艺术论》,光华书局出版社,1930年
从“弃医从文”到“弃教从文”,看似同归,其实殊途。因为当我们提出 两次“从文”的说法时,就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差异。正如“人不能两次踏入同 一条河流”一样,两次“从文”其实意味着在从事了十八年的教育和二十余年的文艺之后,鲁迅对于“文”的观念和理解、对于“从文”的方式和道路,以及对 于“文”与现实历史的关系、与其理想抱负之间的关系等,都生出了不一样的认 识。换句话说,“弃教从文”并不是对于“弃医从文”的重复或回归,恰恰相 反,与第一次相比,这更是一次调整和转变。这一次重新出发,也蕴涵着对于 “从文”之路本身的新的理解和探索。
一
从“文教结合”到离职教育部
鲁迅1906年“从文”之后,于1909年归国即开始任教,曾先后在杭州浙江两 级师范学校、绍兴府学堂、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校担任教师、监学及校长;1912 年应蔡元培之邀任职教育部,曾为社会教育司科长、佥事;随部从南京迁至北京 后,又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任兼职国文系讲师。其间,尤自 1918年起,他的小说、杂文、散文诗以及各种翻译和学术文章大量问世,其作为 文学家和翻译家的影响也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承认。1926年离京后,鲁迅先后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文科教授、文学系主任及教务长等职,最终于1927年10月辞职离去,从此未再涉足教界。从1909年到1927年,鲁迅不间断地在教育界任职 长达18年之久,此间他几乎始终是身兼文教,两种身份角色互补互进,共同构成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形象。这种文教结合的状态至1927年结束,离开中大之后,鲁迅定居上海,成为“且介亭”中的独立思想家与自由文化人,直到走完 他人生的最后十年。从弃医从文到身兼文教,再到弃教从文,鲁迅的道路不仅体 现了他本人的思想转变,同时也折射出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直至后五四时代中 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构成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重要话题之一。
“幻灯片事件”与弃医从文的故事已无需重复,值得关注的是,鲁迅在那时对文学道路的选择和对文学的理解体现了从辛亥到“五四”的代表性观点。虽然他的“从文”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但他对于此事的追叙却是在“五四”之后,其中表达出来的思想观念必然带有言说时的时代特征。因此,在“五四” 时期的启蒙语境中,鲁迅的“从文”思想体现着典型的启蒙姿态。他说:“我 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 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5 由此可见,“那时”鲁迅“想提倡” 的“文艺运动”是一种涵义比较广泛,以改变人的精神为“第一要著”的启蒙 主义文艺运动。在这个思想基础上,他开始了最初的论文编译、文学翻译、 办刊和写作。严格地说,写作——尤其是文学创作——在这一文艺运动之中 是位列较后的。1906年他编写《中国矿产志》,翻译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地底 旅行》;1907年筹备文艺杂志《新生》未成之后,写作数篇文言论文,翌年发 表于《河南》杂志;1909年携周作人一起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直至1913 年,他的第一篇小说《怀旧》方才刊于《小说月报》。可见,从弃医到回国, 鲁迅的从文之路的确是从提倡和从事文艺运动开始的,相比于个人的文学创 作,他在那个时候更加看重的是翻译、编书和办刊,其目的则直接指向现代思 想的启蒙。而在那个时候,他那支文学家的如椽巨笔还未真正发动,他的思想 与情绪都是围绕着这个广义的“文”而展开的。
鲁迅、周作人,《域外小说集》,上海群益出版社,1921年
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鲁迅自归国开始就一直在教育界任职,除了留学生归国的义务和经济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他“提倡文艺运动”的观念中,现 代教育正是内在于这个宏大的“启蒙”与“文艺”的系统之中的,甚而就是“文 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鲁迅的师友章太炎和蔡元培在1902年发起中国教育会 时,就曾明确提出“教育救国”的主张,对此,鲁迅必然是了解和认同的。事实上,在新文化运动的提倡与实践者看来,文艺运动与社会教育都是思想启蒙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像陈独秀曾有名言:“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教师也。” 6 文艺的社会教育功能甚至并非新文学所特有。因此,文教并重,让现代文艺与现代教育相辅相成,这本就是新文化运动的 理想和策略之一。弃医从文的鲁迅秉持这一思想认识,投身文艺运动,以编书、 办刊、翻译、写作的方式开启民智、实现社会教育和思想启蒙的理念,是非常自然和必然的。因而,他此时所理解的文艺,也就自然而必然地包含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艺术、教育甚至学术研究等多个方面。
1909—1927年间,鲁迅在职业身份和具体实践上都很好地结合了文艺与教 育两个方面,尤其是在1918年开始白话小说和以“随感录”为代表的杂文写作之后,其文艺道路的重心也明确为新文学的写作实践。他的写作既是他枯燥的教育 部工作与兼职授课之余的一种调剂与补充,也是受到《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 激发后的一种自觉与新文化界呼应互动的方式与结果,就连作为大学课堂副产品 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成为现代学术的重要成果之一。可以说,文教之间的和谐相成,不仅切实体现出鲁迅本人统一宏观的文艺和文教思想,同时,从鲁迅的个案也可看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大背景下的文艺运动的整体性和关联性。五四时期,在教育部、现代高校和以《新青年》为核心的现代知识界和文坛之间,曾经有过较为和谐默契的良性互动关系,鲁迅等人正是在这样的关系中将文艺开展为一种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现代中国的新文化革命。
杨荫榆,1884-1938
但是,这种关系在“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事件”前后发生了剧变,鲁迅的道路也由此出现转折。“女师大风潮”爆发于1924年,起因是学生反对校长杨 荫榆的专制统治。杨荫榆之所以引起学生的不满:一是她对女学生的管理非常粗暴专制,被鲁迅称之为“寡妇主义”;二是她配合当时“尊孔复古”的逆流,推行文言,反对新文学,与章士钊和《甲寅》一流相符,也受到鲁迅的强烈反对。在“驱羊运动”中,鲁迅站在学生一边,曾退回女师大聘书、宣布辞职;代学生 拟定《呈教育部文》,要求撤换杨荫榆;邀集其他教员联名在《京报》发表《关 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并曾写下《忽然想到·七》《“碰壁”之 后》《流言和谎话》《女校长的男女的梦》等文章,一面鼓励学生,一面揭露事情的真相。1924年8月,在军警入校伤人之后,学生得到外界声援,北洋政府被迫撤走军警、宣布允许杨荫榆“辞职”,继而颁布“女师大停办令”,教育部决定将女师大改组为“国立北京女子大学”,由教育总长章士钊亲任女大筹备处长。8月12日,章士钊呈请段祺瑞免除鲁迅教育部佥事职务,并于第二天明令批准, 8月24日,许寿裳等人发表了《反对章士钊宣言》,抗议非法免去鲁迅职务,教育部中有多人发出声援,鲁迅最终被恢复职务。在这次斗争中,身兼教育部与女师大两职的鲁迅与北洋政府、教育部,以及支持政府的部分教授名流之间发 生了尖锐的冲突,在《碎话》《“公理”的把戏》等文中都有直接的体现。许广平后来在回忆中说:“女师大事件,就是当时北京的革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卖国的军阀政府之间斗争的一个环节。”“本来,女师大风潮不是单纯 的一个学校的事情。......这个斗争,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之后,走向分化的具体反映。” 7 这次斗争之所以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分化,正是因为在原有 的启蒙共识中出现了观念的变化和立场的差异,而这种变化和差异导致了双方 的激烈矛盾。
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上进行“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
二
闽粤经验与“学院”的反动
仅仅离开教育部并未解决问题,他本来“少则一年,多则两年”13 计划在现实中被迫改变了。从1926年8月离京赴闽,到1927年10月离粤赴沪,经历了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的两次辞职,下定决心到上海不再涉足政、教两界14 ,鲁迅这才 算彻底告别了教育行业,不仅告别了教育部,也摆脱了学院知识分子的身份,更远离了与之相关的体制。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从此不再关心启蒙和教育,而是从此他通过脱离体制而改变了生活和斗争的方式,完成了真正的“弃教从文”。
从离职教育部,到彻底告别教育界,这中间的变化与闽粤经验密切相关。因此,必须了解鲁迅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的经历与思考,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他 “弃教从文”的原因与意义。
1926年8月至1927年10月,鲁迅先后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执教。闽粤时期是他的“低产”期,也是重要的转折期。这段时间,鲁迅更深入地观察和反思了 “学院政治”,并对“教育界”感到幻灭和绝望。怀着对北洋政府治下的教育部 和在京高校中的“正人君子”的不满,鲁迅选择了厦门大学,这无疑是怀有期待与乐观态度去的。但是,到达的第三天,他即在与友人的通信中直言:“今稍观察,知与我辈所推测者甚为悬殊。”15 他的失望一面来自校长的尊孔复古,另一面则因“谁有钱谁就有发言权”的校董制,加之学院内部保守僵化且对“现代 评论派”名流多有追随奉承,鲁迅在厦大的处境和感受可想而知。难怪他感慨 地说:“学校是一个秘密世界,外面谁也不明白内情。据我所觉得的,中枢是 ‘钱’,绕着这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没有希望的。” 16
再次选择离开,鲁迅对“革命策源地”广州又再次抱有期待,但实际上, 在中山大学的苦闷较之厦大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在“四一五”之后,目睹了革命内部的背叛和青年的牺牲,他不仅“被血吓得目瞪口呆”,更在愤怒和沉痛中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就在被他自己称为“大夜弥天”“虽生之日,犹死之年”的状态中,他深刻地反思了大革命时代中知识分子道路选择的问题。他深深地认识到:“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17 因此,在反思和发言的同时,他最终决定辞职而去,以实际的行动为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
“四一五”反革命政变
广州期间,鲁迅回顾自己“从文”以来的道路时说:“我曾经叹息中国没 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而今何如?你也看见,在这半年中,我何尝说过一句 话?虽然我曾在讲堂上公表过我的意思,虽然我的文章那时也无处发表,虽然我是早已不说话,但这都不足以作我的辩解。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还有,我先 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18 这不仅是严厉的自省,更是对环境变化及方向调整的思考。他的意思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和写作如何与革命和时代相呼应?在“大时代”的面前,“写什么”“怎么写”,乃至“怎么活”都变成需要重新思考和选择的问题。这不仅是鲁迅与空洞无聊、不敢或无力介入现实的“正人君子”的决裂,也是对于自己曾经的——但是可能已经失效的——写作和斗争方式的反思和调整。
1927年5—6月,鲁迅连续翻译了鹤见佑辅的《读的文章和听的文字》《书斋生活与其危险》《专门以外的工作》等七篇论文,从内容看,对篇章的选择正应和了他自己的思考,或者说他也是借助翻译来清理自己的想法,并以译文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在《书斋生活与其危险》中有这样的表述:
专制主义使人们变成冷嘲......专制之下的人民,没有行动的自由,也没有言论的自由。于是以为世界都是虚伪,但倘想矫正它,便被人指为过激等等,生命先就危险。强的人们,毅然反抗,得了悲惨的末路了。然而中人以下的人们,便以这世间为“浮世”,吸着烟卷,讲点小笑话,敷衍过去。但是,当深夜中,涌上心来的痛愤之 情,是抑制不住的。独居时则愤慨,在人们之前则欢笑,于是他便成 为极其冷嘲的人而老去了。
书斋生活要有和实生活,实世间相接触的努力。我的这种意见,是不 为书斋生活者所欢迎的。然而尊重着盎格鲁撒逊人的文化的我,却很钦仰 他们的在书斋生活和街头生活之间,常保着圆满的调和。新近物故的穆来卿,一面是那么样的思想家,而同时又是实际政治家......读了穆来卿的文籍,我所感到是他总凭那实生活的教训,来矫正了独善底态度。19
鹤见佑辅,《思想·山水·人物》,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社,1929年。
这显然也是鲁迅自己的思考。对于空谈和实践的取舍、对于书斋与街头的选择,这是鲁迅一直极为关注的问题。1925年借“青年必读书”之题加以发挥的就正是这个问题,而在1927年广州更为严峻的现实状况下,他对此无疑更有深切体会。让鲁迅忧虑和警惕的是,在日益高压的专制统治下,会有更多的知识分子遁入独善其身的书斋,他们的冷嘲也必然早晚沦为空洞的“废话”。因而,身处广州“大夜弥天”之际,鲁迅更意识到重提介入“实生活”“实世间”的必要性。为了防止各种因恐惧或绝望而导致的消极逃避,必须重提实践斗争的重要性并重振投入革命的勇气,愈是在残酷的革命低潮期,这样的提醒和鼓舞才愈是重要的。
究竟是“闭户读书”还是“出了象牙之塔”?这不是鲁迅一个人的问题,甚至也不仅是鲁迅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问题。鲁迅的思考看似是个人性的,但实际上具有代表性和启发性。鲁迅自己也是身体力行做出选择的。他不做学院派,最终选择以自由写作的方式与“实世间”短兵相接;不在校园里与青年们师生相称, 而是以自由平等的身份与青年们一同“寻路”,甚至是一同彷徨。
事实上,从“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事件中,鲁迅已经开始对教育界 与北洋政权之间关系进行反思,并在具体问题的背后寄托了更大的思考,即知识分子与政权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思考在闽粤经历的激发中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因而在离穗抵沪二十余天后,鲁迅在题为《关于知识阶级》的讲演中,更明确地提出了“知识阶级”要“为平民说话”“注重实行”等原则,尤其强 调真正的知识阶级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说:“知识阶级将什么样呢? 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20这里充分体现了鲁迅对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核心认识。也就是说,如何处理与专制者之间的关系,是鲁迅判断是否是“真的知识 阶级”的最重要的标准。事实上,自“女师大风潮”之后,鲁迅就在批判专制统治者的同时,更加严厉地批判那些与专制统治者同流合作的教授们,尤其是新文化阵营中的自以为公正的“正人君子”们。鲁迅警惕的是这些新文化知识分子与保守势力合流的危险。同时,他也犀利地指出了“进研究室”“进艺术之宫”或“住在‘象牙之塔’”这些堂皇借口背后的怯懦与退避,指出这些人成为专制统治者的帮凶的可能。
从参与女师大的斗争到亲历“四一五”的这段时间,鲁迅对原有的文艺运动之路不断做出反思,逐渐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生存形态的认识层次,大致可归 纳为:书斋—学院—体制—政治的四重结构。这个结构不仅包涵了从传统文人到现代知识分子存在方式的不同层面,也指示出某种发展变化的道路和方向。事实上,这也就是鲁迅自己走过的道路。从绍兴会馆的书斋式生活到投身于新文化 运动并在以现代高校为中心的教育界中从文从教,这是1912年到1927年间鲁迅的道路,这里包含了传统书斋到现代学院的独善到启蒙的两种形态。但是,这两种形态在1927年这个“大时代”来临之际,被鲁迅彻底舍弃了,其原因就在于他曾 认同的现代学院式生活也随着党国体制的建立与强化而失去了独立性与革命性。鲁迅由此转向批判教育界之外的更大的体制,他说:“我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世事大概差不多,地的繁华和荒僻,人的多少,都没有多大关系。”21 这意味着,鲁迅的失望已不仅是对学院中的某类人或某类现象的失望,更是对其背后体制的势力与本质有了更清醒也更绝望的认识。因而,他从此以后“对于一切学校的聘请,全都推却”22 。并且预言:“北京教育界将来的局面,恐怕是不大会好的。”23
从女师大到中大,从北京到广州,从“三一八”到“四一五”,现实环境和 局势的变化推动了鲁迅的反思和批判的一步步加深,直至升级为一个关乎生死去 留的大是大非问题。鲁迅曾称“三一八”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虽然他 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 言语?”24 但他还是接连写下《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 《记念刘和珍君》《空谈》《淡淡的血痕中》等文。而在“四一五”之后,他几 乎只字不写,只在《〈朝花夕拾〉小引》中以一句“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写 出些许“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25 。由愤怒到沉痛,鲁迅显然陷入了更深的绝 望,或许正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更清醒地看到了“五四”思想运动与大革命时 代的政治斗争之间的差异,并由此反省到自己的使命与斗争方式。是留在体制内 继续通过启蒙式的写作,成为一个“做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 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却令他们在“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 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26 。还是寻找一种新的 方式与青年们一起寻找未来的革命道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自己负责。27 事实上,在“四一五”的血雨腥风中,鲁迅做出的是一 个必然的选择。
鲁迅,《朝花夕拾》,1928年9月北平未名社初版
总而言之,鲁迅的“弃教从文”看似出于一些具体的人事因素,但其深 层却蕴含了一个大革命时代知识分子道路选择的大问题。对部分知识分子及学 院政治的不满固然是一方面,但鲁迅的决定并不是离开厦大和中大再去另寻一所大学,而是决心彻底脱离教界和政界。这意味着他与整个体制的决裂,也表 明了他对于知识者与权力及体制之间关系的明确态度,即对体制内知识分子与体制之间的依附关系的批判性反省。鲁迅当然也知道,北洋政府与广州革命政府之间是存在差异的,但与此同时,他也深刻地看到了二者之间的某种相似。他曾说:“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缧绁之忧’了”28 ,“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样是华盖罩命,晦气临头”29 。也就是说,表面上的差别并不能掩盖其内在相同的反动本质,二者的 差别至多不过就是:北方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南方的“共和使人们变 成沉默”。而这也就对知识分子提出了更大的考验,因为,“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30。知识分子如何保持独 立,成为重大的原则问题。
自“三一八”到“四一五”的过程中,鲁迅从血泊中得来教训,对于北京和 广州两种体制的真相有了深刻的洞察。于是,在对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进一步自 觉和强调中,他选择了上海,这当然也并不说明上海是体制之外的净土,但至少 存在着某种新的可能——摆脱旧体制,甚而参与建设某种新的革命体制的可能。对鲁迅本人而言,从书斋到学院,再到脱离学院和体制,走向一种新的政治空 间,他生活与斗争的方式和依托都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三
“且介亭杂文”与“革命人”
1925年10月,在女师大斗争的高潮期,鲁迅完成了短篇小说《孤独者》, 1926年11月,已任教厦门大学的他又在钟楼里写下了回忆性散文《范爱农》,两 篇作品虽然体裁相异,但人物、事件和情绪都有明显的关联,其主题也都共同指 向了知识分子“怎么活”的问题。
魏连殳是个“新党”,“所学的是动物学,却到中学堂去做历史教员”,他信仰进化、热爱青年,相信“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坚信“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然而“渐渐地,小报上有匿名人来攻击他,学界 上也常有关于他的流言”,在最终“被校长辞退了”之后,一贫如洗。在鲁迅的 笔下,魏连殳的遭遇并非个别现象,因为几个可托的朋友境遇也都和他差不多: 生计不堪、窘相时露,渐渐在精神上也颓败了。开始还希望“有所为”,“愿意 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但灭亡是不愿意的”。但是,困境 中的挣扎渐渐剥夺了他的信仰,曾经“自己也还想活几天的时候,活不下去”, 最终走投无路、绝望地选择了一条自暴自弃的死路,加速走完了自己的余生。他说:“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魏连殳并非真的自甘堕落,事 实上,一直到死他都没有真正妥协,他在棺材里仍是“很不妥帖地躺着”,“在 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 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至死都保持清醒的魏连殳其实是在无可选择中选择了这 样的结局。鲁迅的挚友、可被视作魏连殳原型的范爱农也曾任职师范学校,身为 监学的他一腔热诚,“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他办事,兼教书,实 在勤快得可以”。然而,他的教职终究还是“被孔教会会长的校长设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景况愈困穷,言辞也愈凄苦”。“什么事也没得 做”,终于也没有人“愿意多听他的牢骚”,只能在孤独绝望中郁郁而终。范爱 农的尸体“是在菱荡里找到的,直立着”。作为深知他的挚友,鲁迅“疑心他是 自杀”,并且相信“这是极其可靠的,虽然并无证据”31 。范爱农最终的“直 立”姿态,让人很容易联想到魏连殳“很不妥帖”地躺在棺中的样子,前者的宁 折不弯,后者的格格不入,似乎都是其生前性格与精神的最好象征。
《孤独者》与《范爱农》都是直面知识分子困境与出路问题的重要文本,尤 其涉及与教育界乃至政界的关系。两人最初同鲁迅一样,是“想提倡文艺运动” 并投身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而他们令人痛心的遭遇也成为鲁迅寄托深思和借以 反省的重要依托。如何在现实中生存?如何“有所为”?如何在保证生计的同时 避免精神的“沦亡”?这是鲁迅深切关注和严肃思考的问题。事实上,在《伤逝》《高老夫子》《幸福的生活》等同期作品中,这个思考时时会闪现出来。涓 生所谓“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感悟里,其实也包含了这一层意思。可以说,这个思考与鲁迅“弃教从文”的决定密切相关,当他萌生脱离学院和体制 的想法之际,他必然要考虑如何寻找新的生活和斗争的现实依托,这是他在“大 时代”中思考“怎么活”的题中必有之义。
当然,1927年的现实环境已不同于魏连殳和范爱农的时期:一方面,政治 斗争、党派政治以及帝国主义势力的介入和强化,使得思想领域的斗争形式也有 所升级,进入更为严酷的阶段;而另一方面,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虽然斗争更严酷,但或许可选择的道路却也相对更多。在鲁迅本人的面前,事实上就存在着新 的可能性,让他有可能从中山大学辞职,前往上海,走向一种新的政治空间。
鲁迅对于“弃教”的决心是干脆的,但对于去哪里、做什么,还是经过了 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逐渐明确了方向,并确定了相对长期稳定的生活和行 动方式。上海之所以能为“弃教从文”的鲁迅提供可能,首先就是因为其作为 租界半租界的特殊环境。曾有人说过:“鲁迅到上海的种种考虑和真实原因, 却是因为上海有租界,而且特意选择日本人聚居的虹口区。”“他明白上海, 尤其是上海的租界,是当时中国各地的最佳选择,在上海待下来,他可以有一 个进退回旋的余地。”32 这是实际的话,但却只说对了一半。鲁迅考虑定居上 海,确实有对于自身和家庭的安全的考虑,但同时更有其对于斗争之便的考 虑。上海的租界不仅提供相对的安全和回旋的余地,同时也因其文化市场的商 业化程度,提供了报刊出版的便利。鲁迅在上海期间,程度不同地参与了《语 丝》《莽原》《奔流》《萌芽》《新地》《朝花周刊》《朝花旬刊》《前 哨》《北斗》《十字街头》《申报·自由谈》等报刊的编撰,他的大量杂文 分别发表在不同刊物上,造成了极大影响。此外,他翻译的《小约翰》《思 想·山水·人物》《近代美术史潮论》《壁下译丛》《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 题》《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毁灭》《表》《死魂灵》等,也都获得了出 版的机会,既为他提供了“饭碗”,也继续了“五四”以来的思想传播。因而 可以说,鲁迅之定居上海绝非出于胆怯或退避,而是一种“壕堑战”,是他对 于生存与斗争方式的新的选择。诚然,包含租界和现代出版等因素在内的上海 文化环境也是一种“体制”,但与鲁迅企图脱离的党国体制相比,起码在那个 阶段确实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上海不是世外桃源,事实恰恰相反,上海是斗 争的前沿,鲁迅自己就曾说:“沪上实危地,杀机甚多,商业之种类又甚多,人头亦系货色之一。”33 但鲁迅选择了新的斗争方式,这个方式既是直接的,也是策略的;既是智慧的,也是勇敢的;既是有所依托的,也是极为独立的。正像他 自己所说:“但我却非住在上海不可,而且还要写东西骂他们,并且写了还要出版,试验一下看到底谁要灭亡。” 34
如果把“弃医从文”之后的“文”归纳为“文艺运动”的话,那么,“弃教 从文”之后的“文”则不妨直接称之为“且介亭杂文”。因为,鲁迅新的生活与斗争方式正是依托于上海的租界与商业出版之便进行的以杂文写作为中心的革命实践。对此,鲁迅是相当清醒和自觉的,1935年底,他以“且介亭杂文”命名了 两部杂文集,并在《且介亭杂文》的序言中再次严肃讨论了杂文的意义与价值。他说:
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 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 来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 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绝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 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 他的用处的东西。
正如后来的研究者所言:“随同‘杂文的自觉’一同来到的也是对自己人生境遇的自觉;对自己同这个时代的对抗关系的自觉;......正是通过这个过程, 通过持续不断的对抗和冲突,鲁迅的写作同它的时代真正融合在一起,杂文作为一种时代的文体方才确立下来。”从1919年的“随感录”系列到1934年的“且介亭杂文”,鲁迅逐渐在摸索和反省中建立了一种新的“从文”的自觉。1927年前 后,“辛亥革命以来民国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此刻使鲁迅从隐痛状态变为公开的激烈对抗,从此鲁迅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同共产党领导的阶级对抗一直是一 种平行关系,没有直接的交点,但确实彼此呼应,有着共同的未来指向”。“杂文变成了语言中的行动和实践意义上的形式。” 35
鲁迅,《且介亭杂文》,新华书店版,1948年。
鲁迅对于“且介亭”的生存方式和“且介亭杂文”的生产方式都确乎是自觉的,他自己其实也多次在文章36 的末尾署以“记于上海且介亭”之类来强调 这一点。对于这种依托于半租界环境进行的壕堑战式的斗争方式,他高度自觉, 也高度自信。1935年12月31日,当他照例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为自己的杂 文编集并撰写后记的时候,他突然做了一个有趣的统计。他说:“我自己查勘了 一下: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 十八年,但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 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37 这几个数字所反映出的加速加 量的特征,本身就很好地说明了鲁迅对于杂文写作的高度重视和高度自觉。可以 说,“且介亭杂文”式的斗争,是鲁迅上海十年最重要的行动方式。杂文的主观性、思想性、批判性使得它成为一种更真实、更直接、更具行动力和战斗性的现 代文体,正如瞿秋白所总结的:“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 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 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 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不但这样,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 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自然,这不能够代替 创作,然而它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 38
的确,正是通过杂文,鲁迅将文学写作变成了一种更真实、更直接、更具行动力的战斗方式。通过杂文,他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和独立性。杂文的写作和发表,为他提供了生存的依托和行动的方式。杂文以其高度的现实关联性和巨大的艺术涵容性,令鲁迅在那个“大时代”中,从一个体制人变为一个自觉的独立的批判的思想家。
就在“四一五”前夕,鲁迅在黄埔军校发表的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 讲中说:“好的文艺作品,想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 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39 在我看来,那时的鲁迅已经在努力成为一个自觉的“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的“革命人”了。随后不久,现实与命运就逼迫并成全他,完成了“弃教从文”这一重大的人生抉择,成为一个更符合 其自身要求的“革命人”。
余论
“革命”与“体制”的张力
上海10年的写作与行动,是“革命人”鲁迅在新的革命体制形成过程中对于自身道路和体制的双重探索,其间也必然存在痛苦、矛盾与困惑。比如,他对商 业书店的投机逐利、国民党政府的文化高压,以及左翼阵营内部的分歧冲突,都有过观察与批评,甚至产生过失望、苦恼和愤怒的情绪。他曾多次感叹“上海的 出版界糟极了”40,“此地书店,旋生旋灭,大抵是投机的居多”41 。在文化高压下,“虽然还出版着一大堆的所谓文艺杂志,其实却等于空虚。......革命者的 文艺固然被压迫了,而压迫者所办的文艺杂志上也没有什么文艺可见”42 。这些 情况自他1927年定居上海直至1936年病逝,都未能发生真正改变。因此,他一面 呼吁“需要肯切实出书,不欺读者的书店”43 ,一面亲自全力从事翻译、编译、 著述等“切实”的工作。他的态度是:“我若存在一日,终当为文艺尽力,试看 新的文艺和在压制者保护之下的狗屁文艺,谁先成为烟埃。......无论如何,将来总归是我们的。”44 这正是鲁迅作为“革命人”的信念与斗志。在他看来,只有全力的、切实的行动才是反抗压制者的唯一有效方式。
鲁迅为纪念左联五烈士而参与编辑并题写刊名的《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
上海十年,斗争的形势日趋复杂。“左联五烈士”的牺牲让鲁迅更加认识 到:“统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于是一面禁止书 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 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至今并未宣布。这一面固然在证明他们是在灭亡中的 黑暗的动物,一面也在证实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营的力量。”45 多年的斗争 经验让鲁迅一面坚持着孤独的、韧性的战斗,一面也在反思个人力量的有限。因而,他对“组织化的力量”——尤其是“以革命人群体为行动主体”的力量—— 抱有一定的希望。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鲁迅后来的‘左转’和走向革命阵 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用一种‘双管齐下’的方式......:一方面继续强调改造国民性,另一方面试图寻求一种组织化的力量以革新令人失望的制度安排。”“他的 ‘左转’本身已经暗示了他思想中对于以革命阵营为先锋来改造社会(旧社会在 他那里呈现为充满既得利益者的糟糕制度安排)的重视。自然,他的这种重视伴随着担忧。”46 他同样注意到革命阵营内部的新问题,比如有人“摆着一种极左 倾的凶恶的面貌”47 ,也有人“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 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48 ,等等。所以,如何防止革命体制内部的权力扩张或失衡,也成为他高度警惕的问题。不能不说,1936年离世的鲁迅并没能 看到革命体制的进一步形成与演变,因而也无法以其现实经验来应对更多的新问 题与新矛盾,但他有生之年的思考与行动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他不仅指出了 可能、看到了问题,而且,他所坚持的态度本身——即在革命的进程中探索革命 的方向、在“本没有路”的地方寻求可能的道路——也同样值得继承和发扬。
事实上,革命与体制之间的张力是必然存在的,革命也正意味着一种对既有 体制的反抗。鲁迅在自身的斗争生涯中——正如他所认同的孙中山一样——秉持 着“永远革命”的信念,以行动性的写作作为革命的方式,并进而探索以革命人 群体为行动主体的新体制的建构,在革命与体制之间,尝试创造一种新的历史可能性。他的选择或许并不能真正解决革命人与体制之间的矛盾,但是,作为中国 知识分子的代表,鲁迅的道路始终具有发人深省的力量。
滑动阅览注释
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2 姜彩燕:《从“弃文从教”到“弃教从文”——试析鲁迅对教育与文学的思考和抉择》,《西北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3 鲁迅:《〈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4 邱焕星:《国民革命时期的鲁迅》,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5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39页。
6 陈独秀:《论戏曲》,《安徽俗话报》1904年第11期。
7 许广平:《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许广平文集》第2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8 18 26 鲁迅:《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3卷,第473、476~477、474页。
9 许广平:《关于鲁迅的生活·因校对〈三十年集〉而引起的话旧》,《许广平文集》第2卷,第187页。
10 鲁迅:《“碰壁”之余》,《语丝》第45期,1925年9月21日。
11 林语堂:《林语堂自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1页。
12 鲁迅:《致台静农》,《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6卷,王世家、止庵编,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卷,第336页。
13 鲁迅:《致李秉中》,《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7卷,第167页。
14 鲁迅:《致翟永坤》,《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8卷,第449页。原话是:“我先到上海,无非想寻一点饭,但政,教两界,我不想涉足,因为实在外行,莫名其妙。也许翻译一点东西卖卖罢。”
15 鲁迅:《致许寿裳》,《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7卷,第261页。
16 22 鲁迅:《致翟永坤》,《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8卷,第25、500页。
17 鲁迅:《〈尘影〉题辞》,《鲁迅全集》第3卷,第571页。
19 鹤见佑辅:《书斋生活与其危险》,《鲁迅译文全集》第3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 版,第179~180页。
20 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8卷,第226页。
21 鲁迅:《致许广平》,《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7卷,第327页。
23 鲁迅:《致章廷谦》,《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9卷,第226页。
24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第3卷,第289页。
25 鲁迅:《〈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第2卷,第235页。
27 鲁迅:《北京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54页。
28 鲁迅:《通信》,《语丝》第151期,1927年10月1日。
29 鲁迅:《革“首领”》,《语丝》第153期,1927年10月12日。
30 鲁迅:《小杂感》,《语丝》第4卷第1期,1927年12月17日。
31 鲁迅:《范爱农》,《鲁迅全集》第1卷,第327页。
32 陈丹青:《笑谈大先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0页。
33 鲁迅:《致台静农》,《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4卷,第113页。
34 鲁迅:《致山本初枝》,《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S卷,第232页。
35 张旭东:《杂文的“自觉”(上)——鲁迅“过渡期”写作的现代性与语言政治》, 《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1期。
36 参见《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抄〉序》《白莽作〈孩儿塔〉序》《曹靖华译〈苏联 作家七人集〉序》等。
37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鲁迅全集》第6卷,第466页。
38 何凝:《序言》,《鲁迅杂感选集》,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39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第437页。
40 鲁迅:《致李霁野》,《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0卷,第226页。
41 43 鲁迅:《致李霁野》,《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1卷,第45、45页。
42 47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第310、304页。
44 鲁迅:《致韦素园》,《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3卷,第18页。
45 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鲁迅全集》第4卷,第284页。
46 钟诚:《鲁迅文学经验与中国的国家转型》,《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5期。
47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第5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