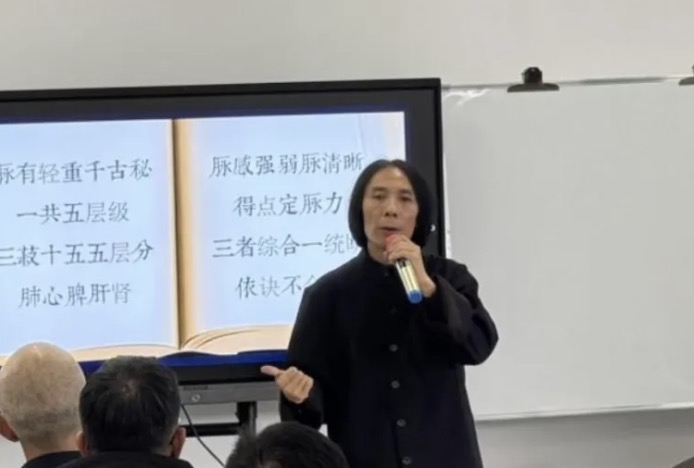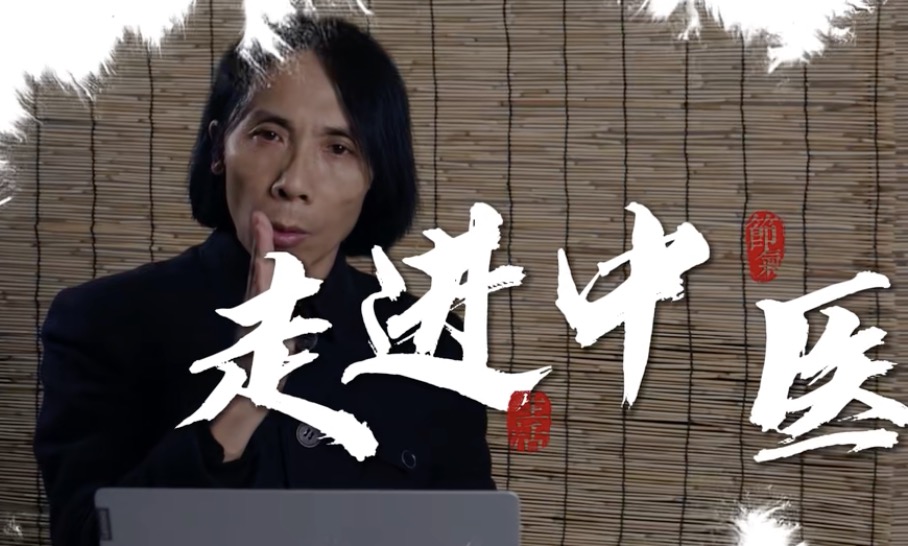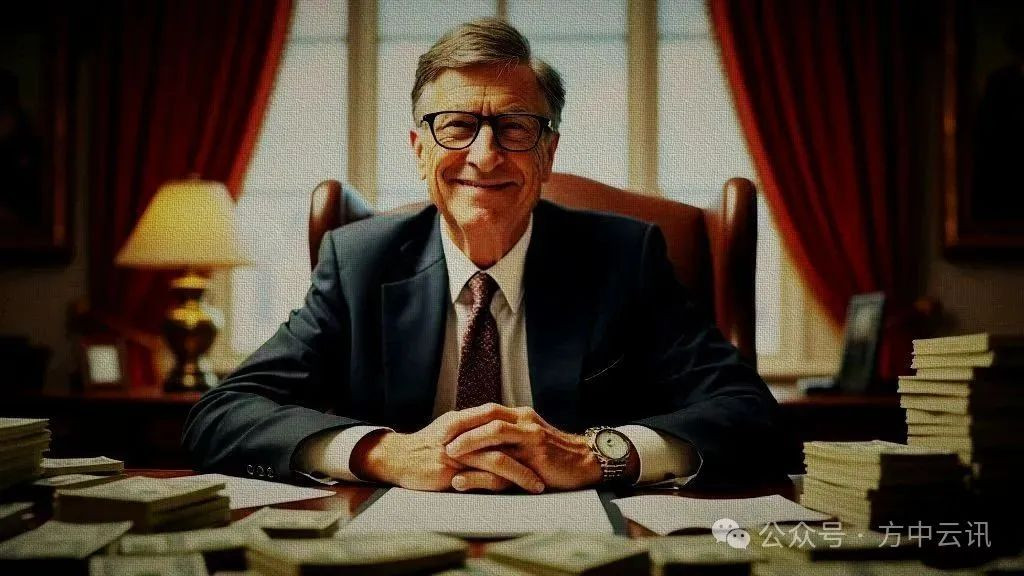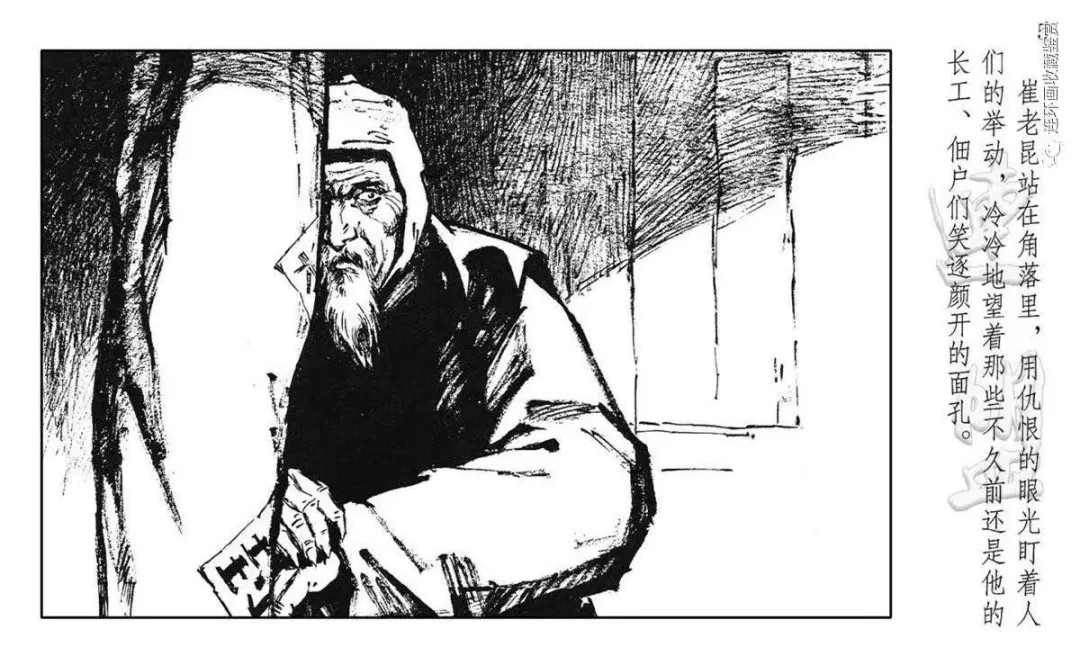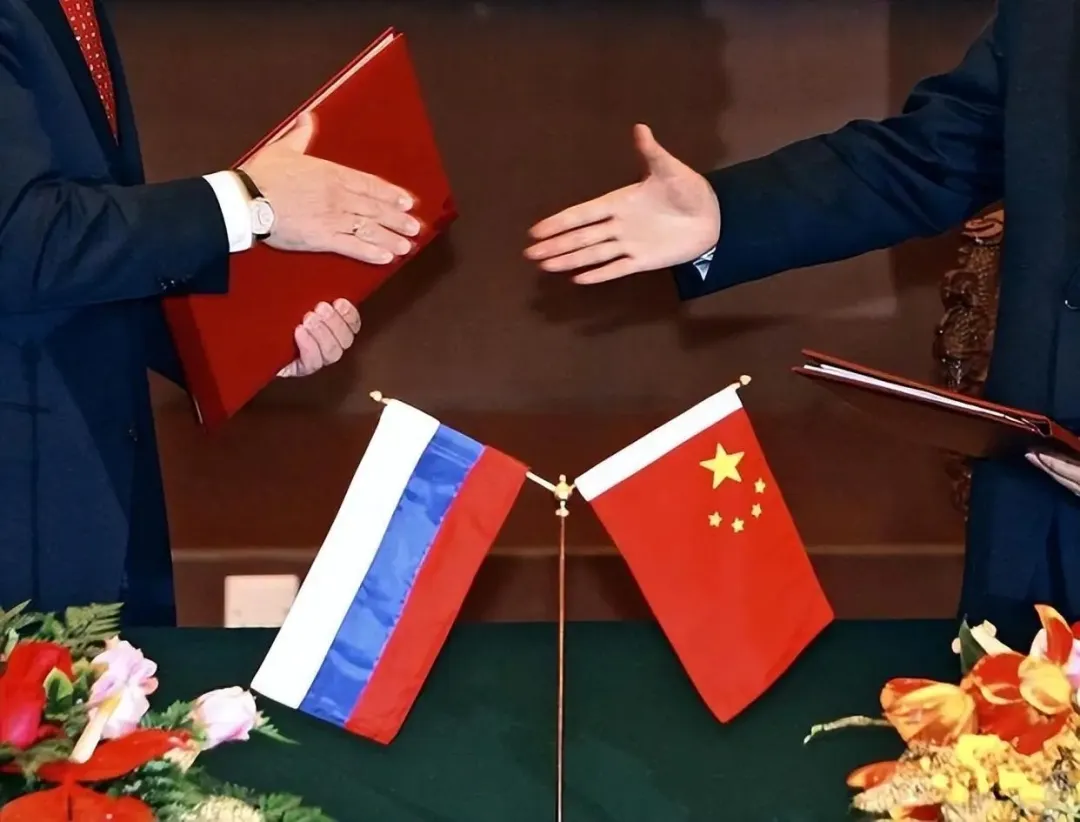建行、招行下调存款利率,一年期利率破1%
09:05:31 时事财经 记者
环球时报:奉劝一些印媒尽快回归事实与理性
09:05:45 国际观察 记者
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洗白,为侵略者站台意欲何为?
09:05:04 自媒体号 相如连山
有人走私600公斤稀土?海关回应
05-19 17:05:20 时事财经 南宁海关
“争气机”歼-10为何再次牵动世界的目光
05-19 17:05:24 时事财经 记者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必须说清楚这三个尖锐的问题
05-19 17:05:05 历史 铁穆臻
做大“蛋糕”为什么越来越难了?
05-19 16:05:03 网友杂谈 阿华
历史虚无主义?背后其实是官僚和资本!
05-19 15:05:49 网友杂谈 辛辣锅
我们对天龙人的要求越来越低,但天龙人的底线也越来越低
05-19 14:05:10 自媒体号 倪刃
毛主席的医疗路线才是中国老百姓的底线
05-19 14:05:16 评述毛泽东 教员的追随者
上滑加载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