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知青叙事:农村和劳动带来成长与收获
导 语
在“伤痕文学”的主流叙事中,知识青年一直以政治“牺牲品”的形象存在。对上山下乡苦难的渲染,也为知识青年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霾。在这段由伤痕文学构筑的畸形关系中,农民与大队干部成为知识青年苦难的根源,也因此在一次次的“诉苦”浪潮中,被动且沉默地被贴上施害者的标签。
然而,现实中的人绝非脸谱化的,现实中的关系也是。在伤痕文学的叙事之外,始终存在着另一种没有被主流话语湮没的声音。一些知青在以亲身经历呐喊,为他们的农民朋友正名。据本文张知青回忆,下乡岁月伴随着生产生活的智慧,以及农民与知青相互扶持的温情。在“安家费”“修水库”“分红”“过春节”等一系列事件中,知青与农民既是朋友,也是战友,还是彼此的老师。知识青年为农村带去了大量的新思想、新技术,却也从农村汲取了养分,获得了远超课堂的生产生活技能与精神财富。
这俨然是一段极其健康的关系,正如张知青所说,“在这里我学会了坚强,学会了勇敢,学会了谦虚,学会了礼让。”而这些,恰恰是他的农民朋友教会他的。
作者|张师傅

1970年2月20日早上,也就是阴历正月十五,我们武汉市十几万69届的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老三届”的学生是1968年下乡插队落户的,所谓 “老三界”实际上是六届,就是66、67、68三届的高中毕业生和66、67、68三届的初中毕业生,合称为“老三届”。我们是69届,比他们低一届。我们为什么到70年才下放?因为1969年我们毕业的时候,大部分人不满16岁。当时国家有个规定,不满16岁可以不下乡。等到1970年2月份,拖了半年以后,大部分人满16岁了就可以下乡了。我们班上还有几个同学没满16岁,没下乡,后来直接上了高中,上完高中直接上大学。大学毕业以后不是博导就是教授,他们赶上好时机了。
我们是正月十五那一天坐火车到枣阳新市区插队落户的,到枣阳新市区简单地交接以后,我们班上的五个同学就跟着农民坐牛车,前往前湾公社朱家湾大队一小队,那就是我们落户的地方。
1、初识中国农民
在牛车上我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农民,想不到这个农民后来竟成了我50年的老朋友。这位农民在牛车上自我介绍说他姓郑,叫郑秀荣,方圆十里八里只要认识他的人都喊他“老歪”。当时我很惊讶地问他:“为啥有这个雅号?”老歪说:“因为修水库我是个搬迁户搬到这来的,这里的人都认为我办事不按常理,他们受不了,所以叫我老歪。以前我在金沟那边生产队的时候是生产队长,在那边我很活泛,我的话社员们都爱听。说句不该说的话,我当队长时半夜三更趁驻队的干部睡熟后,还给社员们搞过私分呢!”
看着他神秘兮兮的样子,私分肯定是件违法的事,当时我对农村一切都感兴趣。因为我对农村的认识都是一片空白。我问他私分是咋回事?老歪跟我讲,那个时候农民交了公粮,留够了口粮,多的粮食都要卖给国家,支援城市建设,支援国家建设。上面的干部为了政绩,把农民的口粮压得低低的。这样的话,农民就可以给国家多卖粮食,他们就有面子,而农民为了吃饱饭只能私下分粮。有关私分这个问题,毛主席有个讲话我看过,大致意思是支持农民私分。他老人家总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为人民着想!
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老歪指着山梁子那边一道冲说:“这是我们队产粮的主打冲,叫简冲,有60多亩好水田。”他又指了山梁子东边的一道冲两边的房子说:“这就是我们生产一队,共55户,245个人。”村里的房子大部分都是土坯墙、茅草顶,砖瓦房寥寥无几。老歪指着远处一座比一座高的大山说:“我们这里是桐柏山,我们这离河南胡杨镇只有二三十里,离随县三河店只有十多里,是个两省三县交界的地方。过去这里是个藏土匪、打游击的好地方。”听说有土匪,我们几个知青来劲了。我们问他:“我们村有吗?”老歪说:“听说有一个,其实他也是个穷苦人家,为了躲壮丁才上山当土匪的。”他说这个人是个老木匠,这个人不错,待左邻右舍不薄。要不是犯了个错误,当个公社书记没问题。喜欢打架的小林问,那个老木匠姓什么,住在什么地方?有机会我们兄弟几个去会会他。老歪说:“朱家湾就他一户姓朱,他就住在你们下沿。”
村里来了五个洋学生,队里的男女老少都来看热闹。我们住的三间牛屋里面人满满的,还有不少人站在外面。生产队给我们的家是三间牛屋,屋里的地铲了好几遍,垫了新土。墙上用石灰水刷了几遍,屋顶又用泥巴和茅草铺了厚厚的一层。一间是我们五个男知青的卧室,一间是灶房,一间是堆柴草、放农具的杂物间。社员的热情是没话说的,老队长当众指派了我们的生活辅导员和生产指导员。我们几个知青也表了态,要听毛主席的话,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农村扎根一辈子。
2、“老土匪”
最后老队长说:“今天晚上的晚饭,小青年们的左邻右舍一家一个,还有一个到我家。”我们的晚饭就是这样解决的。我被一个身高一米85还往上的壮汉,像牵一只小绵羊似的拉着手去了他家。那天是正月十五,是过年的最后一天,农民家过年的菜还没吃完,随便热热便是一桌子。闲聊的时候我问了这位壮汉,我说你贵姓呐?他说我姓朱。听说他姓朱,我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看来他是老土匪的儿子。胡思乱想了一阵,我才安定下来。我想,文化大革命都好几年了,要相信贫下中农。就算是个真土匪也会被改造的老老实实的,不敢乱说乱动。他要真想加害我,我随便喊一声,左邻右舍都能听到。再说老歪介绍老木匠时说老木匠人还不错,我的思想通了,人也就不紧张了。菜到齐了以后,老朱给他的大儿子秋生说:“小鲁是毛主席派来驻队的,把你爷叫起来陪着吃餐饭。”老木匠可能辟谷,也就是不吃晚饭,已经上床睡觉了。
所谓的老土匪终于出场了!老人家70多岁,说话中气十足,两眼有神,腰板挺直。陪我喝了两大碗黄酒以后,把他的历史说给了我听。老木匠说,他年轻时是为了躲壮丁才上山当土匪。一九三几年,红军在这建根据地,打土匪分田地,深得民心。这周围十几个山头的土匪都投降了红军。红军的人马最多时达一万多人,势力最大的时候,还攻打过枣阳县城。当时枣阳共产党的负责人是程克绳,这个事情在枣阳县志上有记载。当时共产党打土豪得到的银元很多,就分散保管。老木匠分到了200块大洋,他在山上挖了个坑埋了起来。后来红军北上抗日,要他把钱交出来,他跑到山上一看,银元不知被谁挖走了。这事成了他一生中的污点,因此解放后给他定了个土匪。听到这个重要的信息我很高兴,在他家又喝了两大碗黄酒便告辞回家。实际上我还想再坐坐,但因为还要回家铺床,还要收拾东西,不得不走了。
回到家后,我把重大的信息分享给了四位同学,同学们议了一下。如果银子真的是被人挖走了,那就冤枉了老木匠。如果被他自己贪了,算是私心严重还是算是犯有严重的错误?最后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要相信政府。既然老木匠没被列入被管制的人员,那他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3、宗族问题
同学们还对我说:“刚才接到公社的电话通知,明早公社召开全体知青紧急会议。”所谓的紧急会议是由公社管知青的韩会计组织的,韩会计讲了三件事。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宗族问题。
韩会计说:“我们公社有很多宗族,最大的是姓付的一族,和姓郑的一族。对你们这些城里的小青年来说,宗族可能是个从未听过的新鲜事物,可在我们农村司空见惯。一点点小的孩子,辈分却很大,满嘴都是胡子的老汉都得听他的话。为什么?人家的辈分搁在那。
比如朱家湾大队有个姓付的伤残转业军人,在火车站盐库工作。他在家娶了个媳妇,生了三个娃。这个老付在他们姓付的宗族里辈分是最高的,他和下面最低的辈分要差十辈。他媳妇姓陈,在生产队当社员。社员们喊老付是大脚老太,叫老陈是小脚老太。因为老付脸上有几颗麻子,社员们不能当着老陈的面说麻字。什么芝麻、麻绳、麻花,只要带个麻的都不能说。谁说她就扳着指头数数,她长你八辈儿,她就骂你八辈儿的祖宗,长你五辈,他骂你五辈的祖宗。
现在宗族问题愈演愈烈。大家知道不出五服,同姓不能结婚。那一个姓付的长辈,跟一个姓郑的晚辈结了婚,在宗族里辈分是按男的算还是按女的算?当今社会讲究男女平等,这确实是个大问题。但任何问题都有解决的办法,我们不操这个心。问题是你们小青年来了,你们该怎样处理这个宗族问题?昨天公社革命委员会专门开了个会议,把这个事情定了下来,由我来向你们传达。公社革委会决定,无论哪个宗族,无论哪个辈分,只要比你们年龄大,40岁以下的男子你们称哥,40岁以下的女子叫姐。需要说明一点,这是对贫下中农而言,地主富农入另册。”
随后,韩会计讲了语言问题。他希望知青们尽快学会本地的语言,这样好跟贫下中农交流。最后,他无不遗憾地说:“我们公社是个穷公社,本该留各位吃顿饭,吃了饭再走,可是我们没钱。去年天旱收成不好,一半的大队要吃周转粮。”
这里介绍一下周转粮。周转粮也叫返销粮,周转粮是指生产队交了公粮,留下的口粮不够吃怎么办?当时是这样子的,不管你够不够吃,先把公粮交了。交了公粮,如果口粮不够吃,第二年春天,国家返销卖给农民。返销粮也不是说你想吃多少斤就能吃多少斤,返销粮是按国家的价格——在我们那是这样子——不分男女老少,每个人每月25斤。这叫周转粮,也叫返销粮。
韩会计说:“去年收成不好,一半的大队要吃周转粮。毛主席教导我们穷则思变。昨天公社革委会决定马上修60亩地水库,水库修好了,水渠开通了,本公社基本上可以解决吃饭问题。我希望修水库的工地上,能看到你们知识青年的身影。”下农村的第二天上午,在公社开了这样一个紧急会议。
4、家 访
回生产队以后,跟管知青的副队长李永昌商量,决定下午他带着我们挨家挨户搞家访。后来看搞调查是很有必要的。当时我拿着小本本记着,挨家问户主的姓名、成分、家庭状况,特别是户主的年龄。
印象最深的有三户,一户是老地主。我们村里就只有这一户地主,地主老两口在一起生活。李队长说,老地主是“五保户”。“五保”是哪“五保”?就是保吃、保住、保穿、保看病,死了保安葬。队长说地主是五保户,当时我们很不理解。贫下中农的孤老吃个五保还说得过去,地主也吃五保,我们有点想不通。李队长说这是党的政策。老地主没儿子,只有一个姑娘,早就嫁出去了。他姑娘跟他们老两口多年都没往来,按国家政策算老地主够吃五保。下农村的第二天就接触到这些从没遇到过的事,当时的感觉是非常兴奋。
印象较深的第二户就是小脚老太家。管我们知青的副队长姓李,在生产队,他家是独门独姓。所以他从不跟姓付的也不跟姓郑的套近乎。还没进院子。李队长就喊起来了:“老陈,小青年来看你来了!”老陈把我们迎进他家的堂屋。一进屋就让人的眼睛猛地一亮,对着门的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的画像。左边墙上全是大脚老太在部队上和转业以后在单位上获得的奖状。右边墙上贴着他的三个孩子在学校获得的奖状和老陈五好社员的奖状。看到这些奖状让人肃然起敬。韩会计的一面之词,让人觉得老陈是个蛮不讲理的泼妇,而这些奖状刷掉了污蔑老陈的不实之词。
当得知老陈只有37岁时,我对李队长说:“按公社的要求,我们是不是该叫他陈大姐?”队长点了点头说是的。随后队长向陈淑英讲了公社革委会的决议,老陈听后非常高兴地说:“我坚决拥护公社革委会的决议,给五个洋学生当姐,我很高兴!”他又对着我说:“兄娃,以后庄上有人欺负你们,告诉姐,看我骂他娃子。”这话说得蛮对我们武汉人的胃口。我对她说:“大姐以后你多关照我们啰!”她笑着说:“那是一定的!”
5、第一次为人民服务
来到印象特别深的第三家门口,李永昌喊了一声:“老华房,来客人了!”一个30多岁的女子,带着三个男孩,抱着一个吃奶的男孩,从屋里走了出来。看是我们知青,她笑呵呵地说:“是来访贫问苦的吧?上这儿算是找对人了,我们家世代贫下中农。”李永昌问她:“老洪浩呢?”华房回答:“他病了,在床上躺着。”“咋了?”她回答说,“还是腰疼那个老毛病,过年都没下地走走。”我们进屋看了看付洪浩。他躺在床上说,本地的医院看了半年,也不见好转。有人建议他去武汉大医院看,可是一提到来回的路费、看病的费用,他就发愁。
当时我非常详细地了解了他的病情,并把问到的情况记在小本上。我说:“我能帮你治病吗?”他说,那感情太好了。我说我不能打包票,只能试试,但我肯定不会出问题。老华房说,死马当作活马医。
吃完晚饭在煤油灯下,我们五个人议了议,队里有三户五保(老地主不算),有一户工属,一户军属。我们五个知青一人包一户,要求常上门看看,帮着挑挑水、扫扫院子,做点杂事。开完会后各人干各人的事,我从箱子里拿出《赤脚医生手册》,对照洪浩的口叙判断他的病情。当时我确定他得的是肾盂肾炎,便想好了我的治疗方法。我背着挎包,打着手电筒,摸着黑去洪浩家。
说明一点,1965年毛主席说“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去”以后,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便组织学者专家编了一本《赤脚医生手册》,这本书共七百零八页,售价一块九毛钱。这本书包括了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五官科,以及常见病、传染病、计划生育等章节,浅显易懂。这本书是专门写给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看的,我实际是个小学毕业生,这本书我看得懂。我给洪浩开了两种常见的消炎药,磺胺恶唑和呋喃坦啶,我写了个条子让他们的大儿子大黑到大队卫生室去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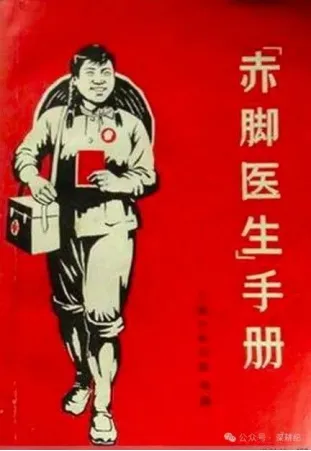
《赤脚医生手册》| 图片来源:深耕纪
我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扎针灸。关元穴扎一针,两个腿上的阴陵泉穴各扎一针。喝了药,扎了针,我便在他家堂屋里坐了一会。坐着聊天时,我宽慰老华房,我说医生给病人扎的针,都是在自己身上扎过试过,找到了感觉,找到了最佳的位置。至于用药,只要不过量,服药以后勤观察,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像我开的那两种常用的消炎药,更不会出问题。老华房说:“医得好,我们家会记住你的大恩大德;医不好,我们也不会埋怨你。总之我知道你是个好心,不求名利。”
老华房给我倒了一碗白开水,我不敢喝。因为晚上吃了两大碗红薯稀饭,再喝一碗水怕半夜起床受不了。大黑在送我回家的路上,扯着衣角问我:“洋学生,我该喊你啥?”我说:“按公社规定,喊啥我都比你长一辈。”他说:“那我是叫你叔好,还是喊你舅好?”我想了想说,“叫叔吧!”大黑亲切地叫了一声“鲁叔”,这一叫就是五十年。前年我回朱家湾,大黑的孙子叫我老太,大黑一米八高的儿子喊我爷,搞得我不好意思。其实我比大黑大不了多少,最多五六岁。
第二天晚上,我去华房家时付洪浩在院子里散步,他牢记我的话:多喝水,多走动。看他的精神状况,就知道针灸和药起了作用。我第一次给农民看病就收到最好的效果,真是个开门红!我心里非常高兴。付洪浩在床上躺着,我给他扎了针炙。我和华房在堂屋里聊天,华房问我:“兄娃,你从哪儿学的这个魔?年纪轻轻的还会扎个针灸?”
她这话把我的话匣子打开了,我说:“我哥我姐是前年上山下乡的知青,去年他们回家过年,说到贫下中农待他们怎么好,他们无以回报。当时我就想要能学会几种为人民服务的真本事就好了,只会理发这一件事太少了。我们家兄弟四个,为了省钱,都是自己在家里理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住在我们家隔壁的夏叔叔在给自己打针灸。咦!这可是门好手艺!架不住我死缠烂磨,夏叔叔收了我当徒弟。夏叔叔原来是荆门县的办公室主任,祖上几代都是中医。荆门县原来是省委书记王任重搞三自一包的试点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了修正主义路线,王任重的秘书梅白把他的工作组撤回了武汉,顺便把夏叔叔也调到了湖北日报。夏叔叔的医德很好,他要求我凡是给病人扎的针,一定要先在自己身上扎。夏叔叔的马列水平也很高,他是中央党校毕业的,他还跟毛主席照过相。夏叔叔不光教我学针灸,还教我辩证法,因为中医里充满了辩证法。可惜我只跟夏叔叔学了半年的针灸,学了点皮毛而已。”
听到这话,老华房说:“这就不得了了!你瞅娃子他爹今天比昨天强了不少,一天都没听到他哼哼唧唧的。”之后华房又说:“队里面把你们要用的农具买回来了,明天你们五个跟我们女的一等劳动力一起锄麦草。”我说:“明天我拜你为师,你教我。”她说锄麦草简单,你没听说‘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我咋做’”。说罢,心情相当高兴的她唱起了《朝阳沟》里那段“你前腿弓,你后腿蹬……”第二天锄麦草,我们五个知青是丑态百出,女一等里的一二十个老嫂子、大闺女、小媳妇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6、知青安家费的挪用与补偿
锄麦草的事就不说了,老洪浩的病情继续好转也不说了,单说那第三天晚上,我给付洪浩扎完针留针以后,聊天时老华房跟我透露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队委会开会的秘密决议。老华房的情报是她的好友、副队长李永昌的老婆张远房给她说的。队委会那天晚上的会是在她家开的。会上李永昌先发的言,他说:“前天公社韩会计把我们各队管知青的都叫到公社开会,狠狠地训了我们。韩会计说:‘据调查,不少生产队挪用了知青的安家费,不给知青盖房子,仅把仓库或者牛棚拾掇拾掇就算给了别人一个家。生产队穷,没现钱,看到白花花的千儿八百块大洋能不眼馋?这个我理解:你们要买农具,你们要给五保户添衣服,你们要给队里的耕牛看病,都得要钱,可你们没有钱。但是你们总得‘堤内损失堤外补’吧,总得给人家知识青年点补偿吧!要是铁公鸡一毛不拔,我有办法收拾你们的。知青的安家费有一半是盖房子的,我们叫人家住牛棚子是有点亏良心。大家议议看咋样补偿?”
老队长付洪章说:“这五个学生娃正在长身体,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不能跟‘男一等’一起干活。我的意见,让他们跟‘女一等’一起干,但是记‘男一等’的工分。”当时的工分是这样的,“女一等”干一天10个工分,“男一等”干一天12个工分。生产队每天每人给我们补两个工分。上一年我们队的分值是“两分五”,就是两个工分值五分钱,干一天十个工分值两毛五分钱。这是相当低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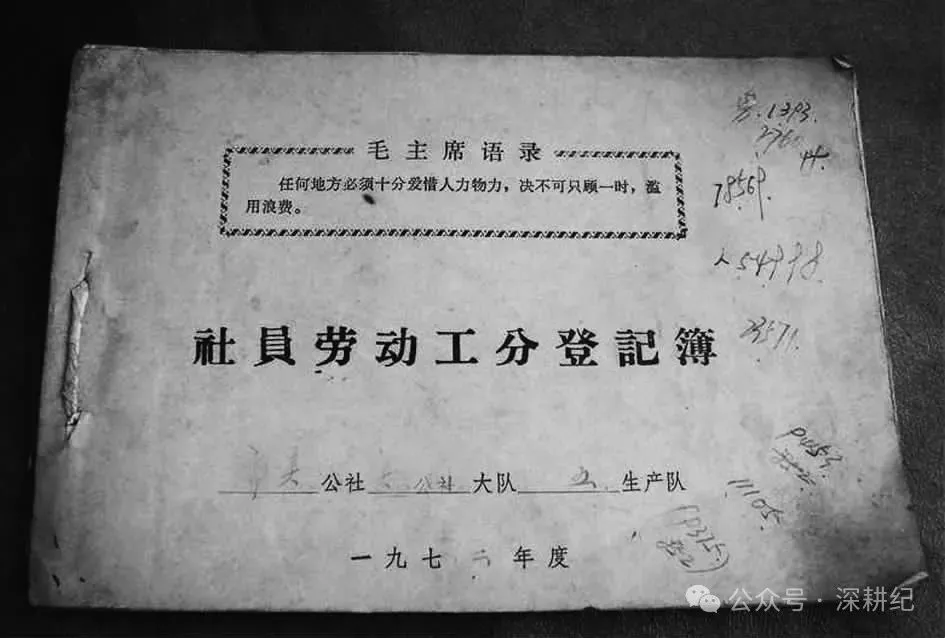
社员劳动工分登记簿 | 图片来源:深耕纪
我妈他们后来在湖北天门五七干校,那里生产队的工分高,他们干一天的工分值两块多,我们才两毛多,差十倍。因为天门是产棉区,他们主要是种棉花。李永昌说:“生产队是种庄稼的,小青年在我们这儿连饭都吃不饱,我们对不住他们的父母。”1969年生产队因干旱欠收,1970年开春也就是我们下农村的时候,生产队在吃周转粮。李永昌说:“这一季就算了,艰苦点,下一季,也就是收了麦子以后,我建议由着他们的意吃,吃多少算多少,只要不浪费。”老队长插了一句:“要不了多久60亩地水库就要开工了,到时候让他们知青去修水库。”
公社的工程,公社有补助,别的不说,一天三顿饭吃饱是没问题的。当时是这样的,如果是国家的工程,吃粮食国家有补助,县里有补助,公社有补助,生产队有补助,自己带不了多少粮食,这是国家工程。当时我们枣阳县有个国家工程,就是引唐灌溉的大岗坡。那个时候我们没上大岗坡,但是我听别人说过。修大岗坡国家补助粮食,地方政府补助粮食,公社补助粮食,生产队补助粮食,修大岗坡的干劲大得很,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一天吃五顿干饭。我们这是公社的工程,公社的工程当时是一个人每天公社补助半斤粮食,补助六七分钱的菜金。
当时有些地方农民吃粮还蛮紧张,还有吃不饱的时候。我跟别人说,有一些人不相信,说我是污蔑毛泽东时代,说毛泽东时代农村哪有吃不饱饭的?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年轻人听说过没有,就是知青上山下乡的68年,或许是69年,记不住是安徽省还是江西省,有一个叫李庆霖的老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编者注:李庆霖是福建人,给毛主席写信是1972年】,说他儿子插队落户,吃不饱饭,病了,看病也难,希望主席过问一下。当时毛主席专门给他写了一封回信,表示了歉意,并给他寄了两三百块钱,这是真实的事情。后来整造反派的时候,李庆霖还因此受到了牵连。关于农民“吃饭”的问题毛主席还有个指示,意思是,忙时吃干点,闲时吃稀点,粮食不够瓜菜代。
生产队的民兵排长说:“知青不会种菜,吃菜难。听说前两年下放的老知青有的还偷农民的菜。既然粮食能由着他们随意吃,我看菜也由着他们吃。他的种的菜不够吃的时候,让他们到队上的菜地去薅几棵菜,到队上的豆腐坊去端几块豆腐,我看也行。”
妇女队长万青说(妇女队长是那个姓朱的老婆):“等他们从水库回来,叫我们当家的(指老朱)帮他们买一只壳郎猪(指半大的猪)过年杀了,每人提十几斤肉回家孝敬父母。再买几只鸡,每天生几个蛋,改善一下生活。”会计郑秀理也出了个点子:“生产队分东西一家算一户,小青年五个人五个姓,当然算五户。这样干社员们没有话说”。
这就是生产队队委会给我们知识青年的补偿,因为他们挪用了我们的安家费。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情报!给老洪浩取完扎在他身上的针以后,我跑步回家去给几个同学汇报。
7、听取知青意见整顿党支部
锄麦草的那几天还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这件事情我记忆蛮深的。当时在搞整党,毛主席对整党活动有个指示,毛主席说,一个党像人一样,要吸进新鲜氧气,要呼出二氧化碳,要吐故纳新。还说每个党支部都要放到群众里头去整顿。公社革命委员会派了几个人到我们大队来听取群众意见,主要是想听一下对李永昌同志入党的意见。前面说过了,本公社的宗族问题很严重,本大队也是如此。我们朱家湾大队的书记姓付,大队长必然姓郑。大队的会计姓付,大队的民兵连长非姓郑不可。基层的权力是均分的,是互相制约的。但本小队有个例外,副队长李永昌的爹是土改时的积极分子,建人民公社时就是队长。后来年纪大了,干不动了,大家推他的儿子李永昌当了副队长。李永昌办事公平公正,从不卷入宗派之争,他的所作所为深得民心。当时女一等里头绝大多数人支持李永昌入党。公社的领导征求我们知青的意见时,我说,不光要入党,还要“双纳新”。
这里解释一下,文革前和文革后新党员都有一年的预备期,在这一年的预备期里,新党员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恰恰是文革中、1970年前后,我们插队落户的那两年例外:新党员没有预备期,一入党就能提干。那时起了个新名词,叫做“双纳新”。
当时我提议李永昌入党后担任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我认为这样对解决宗派问题很有益处。公社革委会很重视我们知识青年的意见,一个月以后,李永昌不光入了党,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同时还兼任一小队正队长。
8、修水库
没过几天水库上马了,我们五个知青踏上了新的征程。公社武装部的部长,当时是建水库的总指挥,他在动员会上讲话,说得很透彻,他说:“天上都是美国的间谍卫星,每发现我们祖国大地上出现了一座新的水库,他们都感到惊讶。一个水库每年能增产多少斤粮食,一斤粮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他们算得精确的很。我们每修一个水库他们都感到害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修水库就是在跟帝修反作斗争。”他上纲上线,修水库的巨大的现实意义、深远的历史意义,他谈得很深很透。
当时修水库或者出民工上面都有补偿,我们修60亩地水库,公社每天每人补半斤粮,补六七分钱的菜金。每天每人自带一斤粮食就够了,关键是吃菜的问题。那个时候出民工有个习惯:先用公社补的菜金去买一只半大的猪,一二十个人或二三十个人的剩饭剩汤喂几个月的猪,水库修完时,猪也长大了,就把猪杀了大家分点肉。菜金被挪用了,吃菜怎么办?有时到生产队拿一点,有时从自己家带一点,凑合着过。但那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地里的菜没长起来,社员们只能吃自己家带的咸菜。最艰苦的时候,伙上把堰塘里的水草捞起来,用开水烫烫,拌上辣椒面下饭。

知青和社员一同兴修建水库
图片来源:那些珍贵老照片
我们村带队的民兵排长会抓枪杆子,也会抓笔杆子,除了生产任务完成得好以外,他还要求我们知青每天写一份通讯稿,交到工地广播站。等到工程完工的时候,公社武装部部长将唯一的一面“文武双全民兵排”的奖旗,授给了我们民兵排。
那天天黑以前,排长交给我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连夜赶回生产队,把这面奖旗交给刚上任的大队书记兼一队的队长李永昌。接到任务时我有点胆寒,十几里的山路,一边是堰塘,堰塘边上长着一人高的茅草丛,一边是一溜烟的坟堆,让人产生很多联想。老歪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不咋地!毛主席的红卫兵走到哪都有六丁六甲护身,把这个家伙三带着,有谁挡道给他狗日的来一下。”说罢老歪递给我一把锋利的砍镰。有了它我的胆气壮了一截,我一路高歌地往生产队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国际歌》不知唱了多少遍。
李永昌看到我带回来的这面奖旗,便知道了排长的意图:就是我们为队里争光了,队里该奖励奖励我们。李永昌当时批了个条,要我明天早晨到队里羊圈牵一只羊,到菜地里去薅点菜,原来的老队长付洪章说:“水库上的基干民兵们也是队里的生产骨干,马上开始双抢,这一仗还指望着他们。给他们搞点奖励是应该的。”
第二天天还没大亮,我就到队里的羊圈牵了一只七八十斤重的大绵羊,然后到菜地里拔了两颗七八斤的大白菜,两个一尺长的大萝卜。用带铁牙的钎担一头扎两个大白菜,一头扎两个大萝卜,手里牵着羊,紧走慢跑地往水库赶。赶到水库时,猪已经杀好了,每个人分了五斤肉,接着把羊也宰了。下午二十几个人好好地会了一餐,十几个人坐在地上围个圈,然后端起装着酒的大搪瓷碗,一个人喝一口,转着喝。那是我第一次喝醉酒,怎么走回生产队的我不知道。
9、“双抢”生活
第二天,生产队给我们指定的生活老师金房,我们叫她老金,也就是老歪的老婆,帮我们处理那25斤猪肉。老金说,肥的割下来炼点油,瘦的腌腌,马上就要“双抢”了。有年轻人可能不大清楚,城里人可能也不大清楚,“双抢”就是抢割麦子,抢种稻谷。因为农时不等人,特别是插秧,早一天插跟晚一天插大不一样。“双抢”一共二十天,这二十天决定着一年的收成。老金说双抢特别累,不吃饱不吃好绝对不行。
那年搞双抢的时候农民还在吃周转粮,公社照顾我们知青,我们男生按学校的34斤指标吃。就那肯定还是不够吃。老金说,双抢不能喝稀米汤,喝稀米汤是要闹出病的,要吃干的。我们知青的管家计小平说,烙饼粮食不够吃,专门吃干的,哪有那么多粮食?老金说,白面里头加一碗麸子,凑合着吃吧。当时生产队分粮食,大米算是净粮,稻谷算是毛粮。因为稻谷的谷糠不能吃,所以是毛粮;但麦子算净粮,因为麦麸子能吃。一般的年成,人是不吃麸子的,麸子是喂猪的。
现在想起来,当年农民交公粮,给国家做出多大的贡献啊!当今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从哪来的?主要靠农民交公粮!如今国家有钱了,却不给当年交公粮的老农民发养老金,狗日的亏了良心!当年交公粮多难啦:一年的粮食收到手,不管收成咋样,先把公粮交了再说。剩下的粮食不够吃,再吃周转粮。周转粮还不是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国家有定量,好像是不论大人小孩,每人每月25斤。“双抢”那繁重的劳动不吃饱不吃好肯定不行。那时不说麸子,好多人家煮的稀米汤、稀面汤,里面放了不少的瓜菜。有一条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说,忙时吃干点,闲时吃稀点,粮食不够瓜菜代。可见毛主席是非常了解“三农”问题的。现在一想起不给老农民发退休金,我就想骂人。那时候割麦摘秧没有任何机械,全靠弯着腰干,最难受的是腰,酸疼得简直无法形容。
1970年的双抢是很有意义的,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件事情。简冲是我们队主要的产粮冲,但简冲离我们住的庄子较远,走过去干不了一会活,歇次坡,就得赶回家吃中午饭,很大一部分时间花在走路上去了。以往插简冲的秧要三天,1970年李永昌当队长后我们采取了一种新的方式:发扬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吃了一天大锅饭。具体的方法是:一大早社员在各自的家里吃完早饭,就到简冲去插秧;党团员发挥带头作用,劳动的中间不歇坡;中午不回家。中饭由几个老妈妈在保管室里做,蒸几笼馍,煮几大锅稀饭,烧两盆子黄瓜,做好后用牛车拉着去简冲。全村男女老少都在地头吃,那个大场面真是开人眼界。

社员在田间开展“双抢”工作 | 图片来源:深耕纪
吃完就干活,本来三天的活,硬是一天把它干完了。这里还得说一下我们每人分的那五斤肉,肥肉炼油以后就没五斤了,瘦肉把它腌一下,双抢没过几天就吃完了。原来计划是每人每天切两片,塞个牙齿缝。肉吃完了,这活还是那么重,咋办?没有足够的营养肯定是不行的。说心里话,老金、老歪对我们是真关心!
那时生产队里只有老金养了两只鸭子,老金是河南人,能干得很。她把鸭蛋腌起来,自己从来不吃,双抢时隔两天她就给我们五个人每人送一个。现在想起来天下最好吃的东西就是老金腌的鸭蛋。老金作为队里指派给知青的生活辅导员,对我们的关照真是胜过亲姐。
当然,老歪不是亲哥也胜过亲哥。这里插一件小事,我们修水库回来以后,每个人不光瘦了,衣服破了,鞋子也磨穿底了,那个地方属沙质地,特别费鞋。我们从水库回来以后跟女一等一起干活,老陈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老陈对老华房、老金,还有老远房、老绣房几个老嫂子说了一声,要她们每个人给知青做一双鞋。后来某一天,我们五个知青都穿着新鞋上工,中间休息的时候社员问:“小张,你这鞋是谁做的?”“是我张姐做的。”问小徐:“你这鞋是谁做的?”“远房做的。”最后问我:“小鲁,你这鞋子谁做的?”“那还用问?肯定是我姐做的”。人家都以为我说的是老华房,她们就问:“老华房,是你做的吗?”我说不是华房做的。问,“哪是谁做的”?我说是我陈大姐做的。
当时凡是姓付的都对我瞪着眼,好像我占了他们好大个便宜。因为老陈是他们老太,我把老陈叫大姐那还得了?虽然他们知道公社有这个规定,40岁以下的都是平辈,但是我公开地对她们这样说“陈大姐”还是第一次,他们感到很吃惊。老陈出来证实,“是我给我兄娃做的。谁要乱嚼牙巴骨瞅我决她(骂她)祖宗”。当时姓付的几个大姑娘,小媳妇瞪着眼不做声了。这事给我印象很深。
10、五块钱的分红
搞完双抢,一天都没歇,就开始挖渠。我们那儿的山,基本上都是花岗石,即使表面风化了,䦆头也挖不动。咋办?得打眼放炮,一米远得放一炮,你算算得多少炮?炸了40里路,抡大锤、打钢钎、安炸药、点导火索,我们都干过。修水库、挖渠是全公社基干民兵无偿干的,受益的是我们朱家湾大队和骆庄大队,这就是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1970年下半年,我们养的鸡也开始生蛋了,老朱帮我们买的那头半大的猪也长大了,长到200多斤后,它也变野了,獠牙长出来了,有一天整晚上不回家。
我们那山上有狼,它不怕,满山遍野地跑。过年杀的时候估计有300多斤,杀了一辈子猪的老朱不敢杀,他要我们去三队请个杀猪的,并嘱咐我们说有人要问起他,就说他病了。请来杀猪的,在七八个基干民兵的帮助下,终于把猪杀了。收拾完以后,屠夫对我说,我造孽了,我杀的是头五爪猪,是人投胎的猪,这是农村的传说。老朱买这头五爪猪的时候,卖家养了一年,只长了二三十斤,因为卖家对这个猪不好,所以猪不长肉,老有病。等老朱把它买回来之后,我们对这个猪好,心细得不得了,为了报答,它猛长肉。
到年底了,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终于到了分红的时候,我们五个人每人分了五块钱。五块钱是个啥概念?当时从枣阳坐火车到武汉车票得四块钱,再加上从我们区到枣阳县城几毛钱的汽车票,五块钱就是我们回武汉的路费钱。
五个知青都感到很沮丧,垂头丧气的。老歪看到我们这样,便请大队党支部书记李永昌来给我们做思想工作。李永昌把小队的会计带来了,小队会计翻着账本,拿着算盘,一五一十地对我们说:“上半年你们吃粮食用的是安家费,队里不跟你们算账。麦收的时候,你们每个人每月平均吃了60斤粮食,值多少钱?全年你们在保管室抱了多少斤烧柴,值多少钱?队里分这分那,你们五人按五户算,一年算下来你们得掏多少钱?一年中你们的生活所需生产队全部给你们包了,算下来你们每人还能分五块钱。你们不算超支户就不错了。”
年底决算以前,李永昌跟会计定了个原则,不管你咋算,小青年不能当超支户。要当了超支户,干一年还得倒给生产队交钱,说不过去,不能当超支户,要适当的照顾。但照顾过头了也不对,照顾过头了,相当于剥削别的社员。看着这五块钱有账可查,我们几个知青都低头不语。没话说了。
看到这个状况,李永昌说:“五块钱是少了点,但是你们要看到成绩。这一年你们政治思想上的收获是非常非常大的,今年你们五个人都被评为‘五好社员’了。公社团委今年发展了六个团员,你们五个都入了团。再说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你们也增加了不少,刚来时除牛粪,怕脏了裤子,现在脱了鞋,光着脚丫子往上踩,你们连眉头都不皱一下。这一年,你们每个人的变化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特别是小鲁的针灸,社员牙疼,他一扎就好;尿床,他一扎就好;肚子疼,他一扎就好。说到他,贫下中农个个敲大拇指,说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老歪插了句话,老歪说:“物质收获也不是没有,有。猪杀了,一人带20斤猪肉回家,剩下的腌腌,明年吃。老母鸡一人也带一只回家。‘五好社员’的奖状,共青团的团徽,这些都是辛勤劳动换来的啊。”最后老歪感叹地说:“一个十六七岁的娃就出门挣钱养活自己,不容易”。
11、跟贫下中农
一起过革命化的春节
1970年年底,全公社的知青都骚动了,因为68年插队的老三届的知青开始招工了。我们湖北的三线工厂很多,需要大量的知识青年。既然老三届都开始招工了,我们69届离招工也不远了。我跟我的好友计小平商量:既然在农村待不长了,我们就跟农村的贫下中农一起过个春节,行不行?他说可以。其他的三个同学回武汉过年去了,他们帮我们把鸡和肉带回去了。我和计小平留下来,跟贫下中农一起过个革命化的春节。过年以前还发生了一件大事,这里也得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生产队每年是腊月二十五放假,过了正月十五上工。放假后农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山砍柴然后挑到集市卖。青壮年劳动力的一挑柴,能卖四五块钱,买点烟酒、糖果过年。那些高中生的一挑柴,能卖两三块钱,交一年的书本费学费够了。
二十五号那天,除了我和计小平外,全队没有一个成年男人。我和计小平在家做卫生,准备年货,忽然听到斜对门的付世美家传来救命的呼喊。我们两个人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他的大儿子,躺在床上牙关咬得紧紧的,脸惨白,晕过去了。我问怎么回事,世美的老婆说,估计是偷着喝酒喝多了。我们也闻到他身上的黄酒味大得很。
世美的儿子只有六七岁,当时我吓得不得了,束手无策。我说这种喝醉酒的事情我没处理过,大队的赤脚医生也处理不了。咋办?到公社要赶个牛车,路上有很大一截弯路,牛车走得慢,即便送去,可能人也不行了。当时我和计小平决定,我们把他背着到公社,十几里路我们俩换着背,硬是把他背到公社去了。经过抢救,把他救过来了。晚上砍柴的男的都回来了,听说这个事大家都跑来问。
世美当时拉着他的儿子功成,要功成给我跪着,认我们当干爹,我们没答应他,因为我们有点看不中那个世美:世美的老婆有公心,蛮能干,跟李双双一样;世美跟那个喜旺一样,人蛮能,但私心重得很。所以我对世美有点看不中。我跟世美说,我说你要真的想感谢我的话,你就教我学炒炸药。我那个时候迷上了炸药,因为开渠的时候,除了军用的黄色炸药以外,就是用化肥炒黑色的炸药。世美是被公社专门派到县城里去学炒炸药的,我想学这个手艺,他始终不教,他垄断了这门技术。我跟他说过,但他始终不教。我救了他的儿子,他没法感谢我,我说你把炒炸药教给我行吗?他还是不愿意教。他找了个理由,他说以后再开渠,再用炸药的时候我再教你。他说的也是个实话,不用的时候咋教?特别是看火候蛮重要,你得在实践当中学。他光用嘴说,还真教不会。
救功成的事公社也知道了,也表扬我们了,韩会计专门写了一个通讯报道表扬我们。韩会计知道全公社就我们两个知青没回武汉,在农村跟贫下中农一起过个革命化的春节。
往年过年都是过了十五才上工,我们那一年是初二就上山种树去了,林场有好多松树苗。过年以前我们还给每家每户写对联。在农村过了一个年,确实很不错,印象蛮深,这是1971年年头的事。1971年,干农活还是重复的,双抢、割麦子、栽秧,这一套都是重复的,但是1971年我们又修了个水库,那就是我们大队的油坊河水库。我们还参加了一个枣阳县投资的从鹿头到新市之间的战备桥工程。我下乡一年零八个月,差不多有一半时间是在搞工程:修水库、开渠、修战备桥。一直到1971年9月底,我被招工进了襄阳轴承厂。
我在朱家湾待了一年八个月,在这里我学会了坚强,学会了勇敢,学会了谦虚,学会了礼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毛主席说的那句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确实,这一年零八个月学到的东西我受益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