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中国黑为什么喜欢方方日记?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司马南频道。今天是2020年4月7号,现在太阳快落山了,我在北京的书房里跟各位说说关于方方的事。
方方是个女作家,比我大一点,差不多65岁左右,现在已经退休了。她写过很多作品,有的还获了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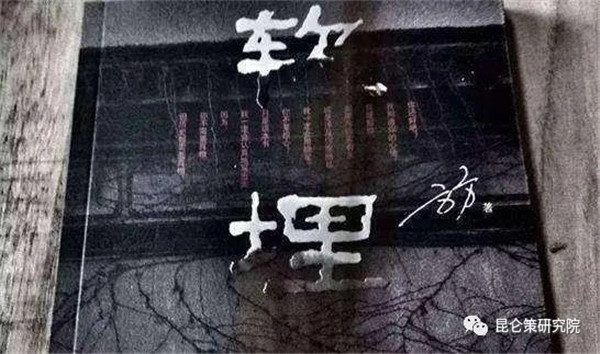
说实话,过去我对这个作家了解不多,但是去年,有一本书叫《软埋》,写土地改革的。我认真读了这本书,读了不止一遍。这本书给我的印象 ,用天津话说“不老好”,还是有点问题的。因为这本书把土地改革写得不像样子,用我们这个年纪理解的语言就是她在否定土改,用写小说的方式表达强烈的政治信念。否定土改对1949年建政的共和国来说,要的是抽取积木底下吃劲儿的那一块。
最近方方日记火了。
疫情期间,生活在武汉的方方出不来,她就把身边的一些事儿,包括听到的、看到的、朋友的、同事的,点点滴滴记下写成文章,然后在网上贴出来,取名叫作方方日记。
大家知道,日记其实是私人化的东西,是不公开的。把日记公开来,只能说她托日记之名,其实写的不是日记,而是关于疫情的纪实。
可是作为疫情的纪实,她又没有亲历一线,也没有采访,只是家长里短,把道听途说的事情记载下来。勉强说,这是非常独特的文学题材:道听途说的、家长里短的、身边发生的,甚至是传言联袂成篇,变成了一本有60篇之多的笔记。
从文学角度来看这本所谓日记,它成为一种新的文学现象,引发别人的关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不仅仅是个文学问题。之所以引发争论,也不是什么文学争论,不是观察问题的视角大与小的争论,也不是写光明写黑暗的争论。之所以引发争议,不是因为她写得好,也不是由于文学题材新,更不是因为日记满足一些人对日记窥视的愿望,而是因为这个日记成为一种独特的、传播学意义上的典型。
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如果她自己写日记,哪怕是在朋友的一些公众号或微博上转载也没事儿,写日记的人成千上万,她之所以显得那么独特,缘始于一种聚焦效应。聚焦就是大家扎堆来看,人群不是自然形成的扎堆,而是推手推波助澜的结果。根据我们在网上十几年的经验,大约二十年的经验,网络上面一件事情如果爆火、爆款,突然一下子,所有的人都在传,甚至越传越邪乎,说后边没有推手,我是不相信的。
那么谁是方方日记的推手呢?
国内有资本控制的媒体,国外有中国黑全媒体机构,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出版社,一体化的。

方方日记的推手怎么有那么大的能量,把日记推至全网、推至海内外?人们又在争论什么?争论的人为什么平静不下来?这些问题都是内涵很丰富的。
问题的实质是政治立场。简单说,就是大家坐的板凳不一样。坐在不同的板凳上,屁股所坐的位置不同,因此说话就不一样,大家所处的位置不同,人们对其所说的那些话,嗅出来的意味就不一样。
什么人说什么话,各种思想无不打上其所从属的、阶层的、阶级的、板凳的、立场的烙印。老话说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虽然说的都是关于武汉疫情的事儿,带着什么样的眼镜,持有什么样的立场,使用什么样的调子,投射什么样的背景,写出来的东西,人们解读自然是不同的。
方方日记里所讲的,有些家长里短,挺细腻的,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也有一些挺耸人听闻的,添油加醋的,故意在紧要处遮掩了一下或者突出了一下的。
很多人不能理解的是:就中国而言,一个一千多万人口的城市突然间踩了一脚急刹车,整个城市,连同整个城市群都封住了,涉及衣食住行,保证1000多万人口的基本的衣食住行,政府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全中国四万多医护人员奔赴武汉湖北,在一线冒着死亡的危险救助那些患者,还有数不尽数的志愿者,平凡的英雄,如此之多可歌可泣的事情,在方方的日记中鲜有反映,而比较多的却是方方黑色墨镜视角下的阴森聚焦,包括扭曲变形。
这件事情究竟怎么样?那是一回事。你看到了什么?又传递出来了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方方日记中最遭人诟病的是,她看到“殡葬馆满地都是无主的手机”,以此来描绘殡葬馆里的凄惨。还有就是,为了营造悲悲切切,凄凄惨惨,怨怨恨恨的情绪,把一个还没有去世的护士写死了,这就近乎瞪眼说胡话了。
类似这样的描写很遭人诟病。方方说她有根据,但是直到今天,面对质问,方方还没有拿出根据来。比方说她说护士已经死了,那个护士明明还在抢救当中。她说朋友给她传的照片,殡葬馆满地都是无主的手机。可是很多人去问,说请您把照片拿出来吧!她顾左右而言它,但到今天为止,也没有拿出照片来。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龄的缘故,这位女作家气儿比较冲,跟胡同里的□□大妈一样比较横,话都是横着出来的,凡事不忍,方方对待那些批评、质疑,一概视为极左。
质疑方方的,不仅有我这个年纪的人,还有年轻人,比我年轻一点,还有好多90后、80后的一些孩子。文革对这些孩子来说是一个遥远的记忆,是历史事件,但是方方概斥之为极左,指控这是一种有组织的行为,这就比较霸道了,不肯虚心接受别人批评的态度,于是遭致了更多的诟病。
一方面是很多人对方方日记对阴暗凄冷,含沙射影,渲泄仇恨提出批评,另外一方面是一些诋毁中国的媒体却为方方的日记欢呼。
比方说我的“老朋友”——那些朋友说起司马南就咬牙切齿,夜里不睡觉,血压上升,尿糖增加加号。那些人声称自己肚子上有个盘子能转圈圈儿、生了病不用上医院、与中国势不两立、与中华文化势不两立的势力。在网上,人们一般把这种人叫做轮子。轮子各级各类媒体对方方日记大加赞许,还有一些诋毁中国的政治媒体也大赞方方的日记。今天的消息是方方日记已经出了英文版,方方的日记被一些人极端反华的势力拿来,作为证据,敲诈中国,勒索中国,要中国索赔。他们说中国人带来了病毒,中国人祸乱了世界。那些人之所以喜欢方方日记,是把方方日记当做榔头抛回来,他们一口咬死了,你们的作家方方说的,是方方提供了详实的“证据”。

这本日记,以最快的速度在美国出版销售,这速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他们太需要这本书了。
有业内人士分析到,美国现在对于自身疫情严重的统一甩锅说法,就是污蔑造谣我们中国对美国隐瞒了关于疫情的信息。这一点和某人的这本日记的核心内涵是一致的。有了这本中国国籍的某人的日记,美国污蔑造谣是不是就有了“佐证”?这样美国民众在购买阅读了这本日记之后,会这么想?美国对外的目的就更简单了,有了中国国籍的某人的这本日记在美国上市销售,那就看我们中国该怎么办?如果中国无作为无反应,那美国就可以宣传,你看这日记里说的都是真的。如果我们追究某人造谣的法律责任,那美国也可以宣传,可以继续造谣中国对某人展开了什么政治迫害。
为什么方方的日记能够受到如此欢迎?欢迎的动机是什么?欢迎中所表达的利益诉求是什么?这里说的如果还不够清楚,美国出版商迅雷不及掩耳速度已经补充得足够充分了。
不仅仅是美国,包括澳大利亚,包括印度,包括当年八国联军中挑头儿在中国崛起到最大利益的那个日不落帝国。英国智库杰克逊协会刚又抛出报告,将世界经济受疫情蒙受的损失“甩锅”给中国,呼吁英国应向中国损失索赔3510亿英镑。方方日记与这3510亿英镑存在着某种逻辑上的勾连。

方方的主观动机怎么样且不做讨论,重要的是客观上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成语为虎作伥用在这里恰当与否值得深入探讨。
有一个词,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一般不用,但是在网上经常使用,叫意识形态话语权或者叫网络话语权。也就是说,在网上谁说了算、在网上谁嘴大,村里的喇叭归谁控制,谁说话的嗓子最大谁霸占的喇叭时间最长。目前世界上,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拥有更强大的话语权。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常常是较为被动的,话语权在人家手里。方方日记所提供的那些,其实未必经得住检验的证据,帮助了村口村长家的“大喇叭”,给他续添了不少恶心中国的材料。
在意识形态舆论场,方方日记里凄惨、灰暗、看不到光明的、看不到希望的调子正是西方“大喇叭”所需要所欢迎的。大凡文学作品,总有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无论你主观动机如何,作品的功效在那里摆着呢。
面对方方日记,人们有不同的评论,不同的看法,我看这事儿很正常。方方大概刻意要追求这么一个效果,以期引起人们的议论。只有议论的多了,褒贬都是买家,书才能卖得好。前面说到的那本否定新中国成立之初土改的那本书,就是在一片质疑声当中不断获奖,在争议当中获得更大的知名度。
对方方提出批评的人中,很多都是咱们眼里的孩子,80后、90后甚至更年轻的小孩子,他们看不惯方方一副苦大仇深咬牙切齿样子。可能你婚姻不幸,过去经历了坎坷,也可能爷爷父辈遭遇了一些自己说起来不太愉快的经历,但把这些投射到今天——大疫当前、全民战役的背景中是不合适的,极左的大概念大帽子扣在这些年轻的孩子上更不合适。
年轻人站起来批评方方阿姨,这种现象说明什么?说明这时代变了。30多年前,有人写伤痕文学,30多年前有一种仇恨教育,还有一种河殇式的启蒙教育。这种仇恨和启蒙核心都指向中国不行,中国什么都不行,中国搞砸了,中国演坏了,中国5000年的黄土文明是愚昧的,恶毒的,堕落的,中国应当接受西方的启蒙,中国应当给西方再当300年殖民地……我们都是在这种启蒙的氛围和河殇的文化氛围之下成长起来的。到了我这个年纪,头发都白了,横着比较,竖着比较,仔细看一看身前身后,国内国外,生活常识告诉我们,尽管中国的过往有很多需要总结的地方,但也不是一无是处,更不是没有资格平等地与其他民族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文化不比别人输一截儿,我们的政治制度也有自己的优势。因此,渐渐地变得冷静起来了,心肠是热的,头脑是冷的,不再被这些启蒙者所忽悠。
今天这些80后、90后的孩子,他们没有接受过这种启蒙,没有接受过河殇所给予的仇恨教育和文化反思。他们睁眼来到这个世界,中国GDP巳是世界前列,继之世界第二。他们年纪轻轻到海外一看,发现海外所谓的发达国家也不过如此。这些孩子没经过文革,方方一骂人家文革余孽,把这些孩子骂冤了,孩子们不怕骂,他们没有这种心理负担。什么左呀右呀伤痕呀,往事并不如烟呀,孩子们脑子里没这些概念。
方方日记现象说明什么?
说明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咿咿呀呀磨磨唧唧的一个老太太,数落着自己心灵的伤痕,患有经年不遇的文革后遗症,跟阳光灿烂的年轻一代过招儿,以为自己一骂体制就能赢得青年,非但没有赢得青年,反倒被青年人打得落花流水。

说明方方拿着文革余孽大帽子横扫千军的战术今天已经不灵了,年轻人根本就不怕这种扣帽子战术,拿在方方手上的那样高高的一摞帽子,酷似代表着自己心灵世界的招魂幡。
极左一类大帽子扣到司马南脑子上,本来就白头发,老杂毛,再戴一个文革余孽极左大帽子,我还真有些忌惮呢,同样的帽子戴给今天的80后90后,年轻人不屑,年轻人看到的是一个更真实的、更客观的世界,他们的眼里绽放着中国的自信,他们对建设这个国家管理这个国家,有着不同于上一辈的自信。
中国的希望在年轻人。
年轻人对方方阿姨有意见,我看这是方方现象最值得思考的地方。
好了,今天就说这么多。
又想起个事儿,这两天怎么突然间都在传方方的别墅。本来说卖书,后边怎么卖房子了?
据说别墅大house几百块钱一平米,官商勾结打通各种关节,原来说是艺术创作室,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方方名下的私产。有点酷似老电影的桥段,向高家庄赵庄马家河一带进军的途中,回头一看,老窝炮楼被点了……
方方扬言要打官司,可以打官司,法律是解决问题的最后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汹涌澎湃的网民关切,方方似也应回应一下。除了见官以外,有关方面是不是也有必要介入调查一下?方方一再声明她不是共产党员、不是高干,但省作协主席、前省作协主席是省管干部,她的个人情况,监察部依照其法定职责是应该管的。有人举报了,有人过问,那是应当的。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过问的信息,倒是举报方方的那篇文章被删了。
就说到这儿,打住吧。
——此文为2020年4月7日下午,录制司马南频道节目文字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