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洋货运动与明治维新(奴性与狼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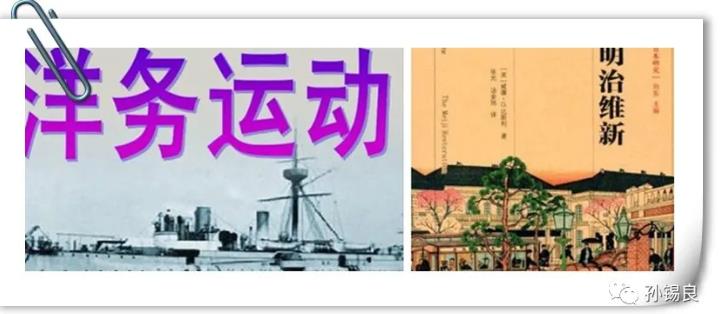
洋货运动与明治维新(奴性与狼性)
1895年正月,日本海军司令官伊东祐亨中将用一篇可载入教材的“劝降书”为中日战争作结,文情并茂,软硬兼施,引经据典,至威至感。伊东有曰:大厦之将倾,岂一人所能支。
丁汝昌的投降书,自然不能出彩,败军之将,有何心思行文立意?且摘几句:……今因欲保生灵,愿停战事,将在岛现有之船及刘公岛并炮台军械献与贵国,只求勿伤害水陆中西官员兵勇民人等命,并许其出岛归乡,是所切望……
惊天一战,既宣告了中国洋务运动的破产,又宣告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
如果我们仅仅只看战争的结局,当然也不全合理,因为日本也为自己的成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如果再把视野扩展到一百年的观察期,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为失败所付出的代价冠绝古今,其负面影响之持久无法估量,一战,二战,都不是结束,未来还将延续。
一百年的被欺凌,列强在中国人脸上刻下了一个烙印——华人可辱。
中国学者研究了一百多年的洋务运动,越研究,越出“奇迹”,过去还能反省些不足,如今尽剩下美化言辞,好像今日中国的现状乃洋务运动所结果,一百年的将亡之痛,在某些洋奴的眼中,那都只是历史的“故事”。
撇开微观的历史细节,我对洋务运动失败的最直接总结是:洋务运动的本质是“洋货运动”,它没有带来真正的洋务和洋技,只带来了洋人,只带来了洋货,“洋务”的内涵是“洋人来务”,不是中国人的任务。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推动因素
1856年-1860年间,英法两国在美国的帮助及参与下,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进一步扩大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取得的权利。此时的清朝,集中力量镇压太平天国,遭遇外战失败是历史必然,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不得不继续卖国求和。
除条约的权利之外,侵略者取得的最大成就是:驯服了清朝统治阶层。
就清朝而言,除对外失败之外,也获得了自己想要的“利益”:满清统治者与洋人化敌为友,利用洋枪洋炮镇压了农民起义军。用满人的话讲,农民起义是“心腹之害”,而洋人的侵略不过是“肘腋之扰”,两害相较取其轻,“以毒攻毒”便是洋务运动的政治首选。(摘自《洋务运动》第9页)
●★●洋务运动的始点
1861年,清政府决定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称总署或译署。
1862年,又在总理衙门下面设立了同文馆,挑选八旗十三四岁儿童进馆学习外文,英国人赫德是帝国海关和中国政府依托顾问,乃同文馆的鼓动者,他从海关拿钱,并任命美国传教士丁韦良做校长,同文馆在丁韦良控制下前后达30年之久。随后,两广总督瑞麟在广东设同文馆,江苏巡抚李鸿章在上海设广方言馆,宏闳等30人成为首批留美学生。(摘自维纳克《远东近代史》第68页和《洋务运动》第13页)
●★●师夷智以造炮制船
所谓师夷智,就是请洋人来帮助推动洋务运动,主要方式有以下几种:
其一,直接武装干涉。英国的常胜军,法国的洋枪队,运用新武器,在争城夺地的战斗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宁波,常熟,昆山,富阳,等,都是在洋军直接援助下打败太平军。(摘自《洋务运动》第14页)
其二,洋军帮助清政府训练军队。执枪,用炮,战术练兵,阵式排练,都由英法教官担当,1865年用半年时间训练了1200多名清军,这批清军后来都成了李鸿章淮军的精锐。
其三,出售洋枪洋炮和船只。直接给清军洋枪洋炮,用船只帮助清军运送队伍,1861年,英国派出8艘轮船帮助淮军运送7000多人到上海,然后高价向淮军贩卖枪炮,由赫德安排,清军向英国购买炮船,还聘英海军大尉阿思本作司令。(摘自《筹办夷务始末》第四卷第25页)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军队,在洋人的帮助下,于1864年打败了坚持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革命军。这次胜利,给了洋务派极大的信心和资本,他们敢于喊出:资夷力以济运,得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三位清末重臣的分歧也随胜利而公开化,李鸿章讽刺曾国荃(曾国藩之弟)劫掠南京:无屋无人无钱,管葛居此,亦当束手,沅翁(曾国荃)百战坚苦而得此地,乃至妇孺怨诅。而左宗棠讽刺李鸿章则是:李瀚章(李鸿章之兄)一门,遭际圣时,以功名显,其亲党交游,能自树立,文员监司以上,武职自提镇以下,实不乏人,惟勋伐既高,依附者众,当时随从立功,身致富贵者又各有其亲友,展转依附,实繁有徒。(摘自《李文正公全集》第6卷第34页)
●★●洋务派的对外政策
洋务运动的主动权掌握在奕訢和李鸿章手上,对外政策权也掌握在他们二人手上。在对待洋人的问题上,主要有几种主导性的思想认知:李鸿章认为“中国无法战胜洋军”(不是短期,是长期);光绪的本生父亲奕環认为“我国之兵,为防家贼,非为御外侮”;军机大臣刚毅认为“我家之产业,宁可赠之于朋友,而必不畀家奴”。(摘自《洋务运动》第32页)
三个人的对外政策思想逻辑都是“宁卖不战”,比如说日本侵占琉球一事,李鸿章对朝廷的建言是:琉球是孤悬海外的黑子弹丸之地,与国家安危无关,不惜把它含糊送掉。在这之前,美国调停人曾劝清政府与日本瓜分琉球,清政府未曾答应。(摘自摩尔斯《远东国际关系史》第334页)
洋务运动的对外政策中,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洋员”两个字,凡涉洋制造、洋贸易和洋合作,无论是清政府事业,还是合办事业,都必须有“洋员”主导,所有的“洋员”都具有双重人格,一方面是洋人,背后都是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是清朝雇请的办事人员,可以直接参与中国政治,在任用督抚问题上,清政府还无耻地去征求赫德的意见。(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43页)
在控制军事方面,资本主义列强利用中国的洋务运动,实现了“让清朝军事力量只能镇压中国人民、不能抵抗外国侵略的水平上面”。它们的手段主要有两个:一是向中国出售过时的武器弹药,一是控制由洋人主导的中国办军火炮船制造业。
英国历史学家季南曾写道:“对英国来说,最为重要的事情在于支配中国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它的舰队。”1880年,李鸿章授权赫德,中国海军聘请英国军官一事可由赫德代办,但赫德并不满足,他接着劝告李鸿章:这种方式应当同时运用于陆军。(摘自季南《1880-1885年间英国在华的外交》第213-215页)
总而言之,满清洋务运动的一个鲜明特色是:洋人主导,洋人控制,以洋货为洋人获利,内政,外交,海关,军事,均是洋人世界。1884年,英法德美等国在中国有451个商行,银行业主要有汇丰、麦加利、丽如和德华等,其中汇丰银行势力最大,掌管着中国海关收入特权,由部税务司赫德定夺。
●★●外国军火厂的甜蜜时期
洋务运动,它的始点就是购买洋枪洋炮和洋船,英法德是三大卖主。阿摩士庄和克虏伯等军火厂是阔绰主顾。清政府突出一个“买”字。李鸿章向德国定购的定远和镇远两舰即花掉300万两白银,而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五年经费也才300万两白银。
因为不懂技术和规则,买的过程浪费巨大,不仅陈旧货多,而且坏货也多,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大沽炮台,第一次试炮时,李鸿章现场观演,结果炮台爆炸,李被吓个半死,第二次试炮演习,他拒绝再到现场。(摘自包尔格《马格里传》第241页)
●★●洋务运动的主要阶段
三个主要阶段:军事工业阶段;围绕军工业配套的其它工业阶段;北洋海军成军和重工业阶段。
企业的四种类型:官办;官督民办;官商合办;商办。
◎第一阶段:军工企业
购买机器。曾国藩购买美国机器,左宗棠依赖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都是请洋人代造。李鸿章的苏州炮局主要依赖英国人马格里。
左宗棠办了福州船政局,李鸿章办了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和天津机器局。
江南制造局。招募的是英法兵匠,最初计划以造船为主,后来由于清政府需要镇压人民,就改造枪炮,造英、法、美式兵枪、马枪等。从1868年始,江南制造局城南分厂可以造小船,都是外国人按照外国的图纸生产,部分是出钱购买英国的图纸,除船壳外,船内的机器多是外国的旧机器,与其说是生产,倒不如说是仿制。光是仿制还不行,还必须附带购买洋枪洋炮的任务。
金陵机器局。李鸿章任命英国人马格里主办的一个军工厂,前身就是苏州炮局。这个兵工厂主要任务是生产火药和大炮,因为马格里是一个帝国主义阴谋家,金陵机器局为大沽炮台制造的炮很多是废炮,1875年,因为多次试炮无用,李鸿章不得不撤去马格里职务。(摘自包耳格《马格里传》第250页)
福州船政局。主要依赖法国洋枪队将领德克碑和税务司法人日意格,他们建议轮机向西洋购买,用法国图纸造船,由法国人代为监制。为了更好地利用洋技术,还开设了洋学堂,有洋文学洋师,主要教英法两国语言。在五年中,该局制造了大轮船11只,小轮船5只,大轮船150匹马力,小轮船80匹马力,均照洋兵船式样。
后来,福州船政局造的船被李鸿章查出用的是旧轮机,于是指责左宗棠造船失败,要求直接购买洋舰,并且只能由朝廷包办,实质上当然是由他包办。
天津机器局。先是由清朝贵族崇厚创办,后由李鸿章接管。该机器局的总管是美国驻津领事英人密妥士,购买机器制造火药。李鸿章接手后,募来香港等地洋工匠,大肆整顿,扩大规模,制造洋火药、洋枪炮、洋水雷和各种制式洋子弹。如同江南制造局一样,天津机器局除制造弹药以外,还有购买洋枪洋炮的任务。
综合看来,四大军事工业,表面上是中国人创办,实际上是洋人主导,任用洋匠过多,几乎所有原料都来自外洋,炮船子弹制式效仿洋式,实事求是地说,它们都只能算是装配厂,或者说是外国军工厂的附庸。
洋务运动中诞生的企业有三个特点:规模上还算大,实际上是空中楼阁,只要外国侵略者一天不支持,武器都造不出来;二是落后的产品只能用于内部镇压,而不能抵御外寇;三是无法维修自己所造船舶,只能送到洋厂维修。(摘自《洋务运动》第82页-85页)
◎第二阶段:与军事工业配套的工业。
轮船招商局。1872年,轮船招商局成立,5年中添置轮船9只,1877年,又花222万两白银收买了美商洋行的破旧轮船18只,旧轮愈增,耗费愈增,在与洋船行竞争时每每落败,尤其是外洋运输中,曾派船到日本、吕宋、新加坡等地,但不久即告停顿。招商局本身没办好,但招商局的官僚们都发了财,公款日亏,私囊日充。
开平矿务局。这是一家开采煤矿的企业。帝国主义列强不愿意中国自己采铁矿,但不反对中国开采煤矿,因为它们觉得把煤矿从外国运过来资费不少,不如在中国取,而铁则是重要制造机器的资源,必须控制。煤矿聘任的矿师是英人哈德森,购买机器,英人巴顿主持钻探。中国其它地方还有聘请日本工程师试行新法开采,但这些日本工程师并不是真正的采煤工程师,开办极不顺利。后来,赫德又从英国请来矿师哥师登及洋匠3名来华办厂,用西法探测阮家山、窝子沟等四十余座煤矿,勘测大冶、武昌等铁矿。
天津电报总局。创办电报的意见,最初系由沈葆桢提出,后由光绪批准,指定李鸿章在天津试设,试设成功后,再在各地设分局。建设电报,必须架设电线和大量器材,全部购自外洋,主要由英国大东电报公司和丹麦大北电报公司两家垄断,中国的电报事业完全被它们掌握,所有筹办商军要事,调兵机密消息,都完全泄露,清朝的一举一动,都被洋人了如指掌。(摘自《洋务运动》第102-103页)
兰州机器制呢局。这是由左宗堂开办的一家制造毛制品的工业,主持者是德国人石德洛末、李德、满德、米海利和福克等人。后因成本太高而倒闭。
上海机器制布局。1878年,上海候补道彭某禀请李鸿章、沈葆桢,准备购买英国机器和聘请英国匠人,在上海成立机器棉纺制厂,获批。1880年,由美国技师单科负责主持选订机器和规划厂房,先订200台,以后再补充。该机器局最初由彭某筹办,但李鸿章派来郑观应经手,从此便将“彭某”隐去,机器局便为李鸿章所控制。1883年后,郑观应离去,李又派龚寿国兄弟、盛宣怀和经元善等人经营。1893年,清花厂起火,适值狂风,厂货俱焚,全厂房屋及货具大部分烧成灰烬。
这个阶段,仍然是官僚办企业,不懂业务,更不愿意设法培植中国人才,一切依赖外人,船主司机都是洋人,洋人在华,非赌博嫖娼,即酗酒躲懒。中国开矿,未尝不请矿师,惜来者多是南郭先生,名为矿师,实无本领,夸张诡作,愚弄华人。电报业,完全掌握在洋人手里,凡各地密电至京,无不消息外布。即使如此,洋务派官僚仍然强调“综理一切,统用西人,绝不思教养华人。”如此经营企业,还妄图自强求富,无异于痴人说梦。(摘自陈炽《庸书》外编卷下第247页)
◎第三阶段:北洋海军与冶炼厂
前两个阶段经历了25年,清朝有志之士批评洋务派粉饰太平,苟且偷安,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1885年,中法战争的失败使洋务运动遭到了声讨(其实,中国并未失败,是李鸿章主动认败),投降卖国政策已经破产。海军方面,福州船政局的十几艘船完全沉毁,陆军方面,淮军都是配有洋枪洋炮的部队,自强,最后变成了投降。购买和仿制洋炮洋船,而不修明内政,直是“全无心肝”。
此时,李鸿章强调,水师还未练成,船舰尚须添置,不得不“含忍议款”。李鸿章下定决心全力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技,要向外国侵略者购买更多的船只大炮,要购来一支强大的海军,不再打算自己造炮制船。此时的湖北,张之洞开始建设湖北炼铁厂和湖北织布局。
天津铁路公司。李鸿章主导,由他任命伍廷芳主持其事,负责财务,以金达为技师,官督商办。(摘自肯特《中国铁路企业》第30页)
洋务运动时期中,洋务派建筑的铁路总计里程接近400公里。建筑技师差不多都是英国人,所要重要器材也差不多都是从英国输入。1884年,英国国会议员约翰奔德致英国外交部的信中说:“对英国说来,中国修建铁路具有最大的重要性,对我们的钢铁业来说,对我们的机器制造业来说,都给予了出路。”(摘自季南《1880-1885年间英国在华的外交》第266-267页)
北洋海军成军。1888年,北洋舰队建成,在整个洋务运动中,建设这支舰队是为时最久用钱最多的,它的船只几乎都是向外国购买得来的,而船只的价格比起枪炮来却要贵得多,在赫德推荐下,1879年,从英国购买的8只蚊船性能低劣,完全是一个骗局。后陆续改从德国购买铁甲船。国内修建船坞,李鸿章介绍法国人德威尼包办。
北洋海军的阵容如下:
主战舰队:定远,镇远,经远,来远。
防守舰队:致远,靖远,济远,平远,超勇,扬威,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
练习舰队:康济,威远。
补助舰:泰安,镇海,操江,湄云。
上述22只舰,17只全部外购,5只来源于德国,12只来源于英国,另5只为外购构件国内拼凑而成。在这22只舰中,有9只为铁甲快船。
船舰为外国所买,北洋海军不得不延出洋教练,也就是说,洋教练实际上掌握了中国海军的全权(在甲午海战中,每条舰上都有三名左右的洋人指导)。外国侵略者为了控制中国海军,首先从争夺教练的席位着手,赫德一方面揽炮船的购买,一面又企图控制中国海军。李鸿章认为:不免揽权,而欲令其办事,似不能不稍假以权。最后,清政府重臣均认为,赫德既控利权,又执兵柄,其结果是总理衙门和南北洋都将为他牵制,赫德没有达到目的。(摘自《洋务运动》第143页)
北洋海军在英德势力的控制下,各种教习均任用两国洋员,琅威理任北洋海军副统领和总教习达四年多之久。1891年,李鸿章第一次检阅海军,他在《巡阅海军竣事折》中写道:“…..海军频年训练,远涉重洋,并能经受风涛,熟精技艺,陆路各军,勤苦工操,经久不懈…..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可摇之势。”
1894年5月,李鸿章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检阅海军,规模比上一次更大,一路之上,要塞,学校,铁路,船坞,军舰,礼炮齐呜,龙旗招展,向他致敬。他觉得自己的舰队已经可以“先声夺人”和“聊壮声威”了,于是向朝廷申请嘉奖北洋海军。(摘自《洋务运动》第145页)
湖北炼铁厂。张之洞创立,既可以炼铁,还可以铸造山炮。熔铁炉购于英国,枪炮厂的机器自德国购得,其它设备多从英国购得。该炼铁厂也是雇用大批洋匠为指导,主要的有英国人亨纳利贺伯生及比利时人白乃富等。洋教习,矿师,工师各匠,择其不可少者招募28人,托欧洲著名之郭格里大铁厂代雇。张之洞最后还吸收淮系盛宣怀,同他兼办铁路。
洋务运动的第三阶段,既是高潮阶段,也是破产阶段。赫德曾说:“我为英国控制中国海军而奋斗了25年。”
●★●洋务运动的结果
新开办企业数。从1872年始,到1894年,共开办企业厂矿数为54家。
进出口变化。1871年,清朝的进出口数为:出口66853千海关两,进口70103千海关两。1894年,出口为128105千海关两,进口为162103千海关两。
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近代工业开始出现,但这时的工业机器自主性极差,绝大多数掌握在洋人手上。
标志性失败——甲午战争。
北洋陆军自牙山开始溃败,再失平壤,让战火烧至中国境内,九连城再溃败,放弃大连湾,跟着牛庄、营口相继失守,一发而不可收拾,东北和胶东半岛尽被日本蹂躏。
海军方面,9月8日,大东沟之战,失船4艘,北洋海军只是比日本损失稍大,并非大败。但李鸿章此时命令北洋海军停在刘公岛藏匿不出,被动挨打,导致主力战舰被水陆夹攻而毁,丁汝昌被迫投降并服药自杀,残余军舰全送给了日军。李鸿章及其同僚,即使到了将亡时刻,还在坚信“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战,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切记勿忘,汝勿性急。”有如此愚昧迂腐的重臣,何人能救中华?
李鸿章对甲午战争的责任主要有:一误于望和,二误于待和,三误于求和。(摘自洪弃父《中东战纪》第1页)
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中讲: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政府认为“鸿章夙望,边事悉以委之”,甲午之战,用叶志超、丁汝昌诸人,辱国丧师,为诸夷笑。由是谈洋务者,渐为世人所诟病。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不论在军事、经济、政治各方面,都在全国人民面前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
洋务运动的破产,甲午战争的赔款割地,影响只是第一阶段,其后几十年,中国工业和军工产业继续是延着这个错误的道路前进,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所有的大国中,有且仅有中国不能依靠自己保护自己,中国民生工业不能为战争提供援助,中国军工企业不能为战争提供可与敌人抗衡的武器,直至二战结束,中国所有的先进武器和机器制造业都来源于外国。
综合性总结:直接买洋货,请洋人造洋货,洋人决定中国洋货水准,中国军队被洋人训练,军火和舰船由洋货所控制,无一洋事,中国有独立自主能力,与其说是“洋务运动”,不如说是“洋货运动”。
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的起点和终点,日本国内并没有统一说法,有人以“黑船来航”为起点,有人以资本制造为起点,有人以开国为起点,比较多的说法是1868年为起点。终点的分歧就更大,有人以中日甲午战争为终点,因为那标志着日本的霸权时代来临,有人以日俄战争为终点,认为那才是日本成为世界强国的标志。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实现了民族自立。
1842年,日本得知英国对中国取得最后胜利,政府立即撤销了1825年公布的驱逐外国船的指令,避免与外国发生冲突,同时加强军事准备,以便抵制外夷。
1844年,美国两军舰来到浦贺,要求通商,幕府拒绝。1852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再次出现在日本海面,要求日本开国。1854年,日美亲善条约《神奈川条约》正式签订,这是日本开国的第一步。随后,日本与英、荷、俄、法都缔结了通商条约。在日本看来,通商条约是治外法权、关税缺乏自主的不平等条约,基调都是以武力相威胁。幕府政权逐渐解体。(摘自大石嘉一郎《日本近代史纲要》第107页-126页)
开国以后,日本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幕府被推翻,二是富国强兵成为主流意识。
为了实现目标,日本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化”,与近代化政策并行的是向世界宣扬“国威”,对朝鲜和中国表示侵略意图。西乡隆盛,大隈重信,大久保利通,山县有朋等日本精英均把目标指向中朝,山县有朋友著《邻邦兵备略》确立了对中国进行战争的宣言,一大批“国权扩张论者”主导维新思想。顺利将琉球设县是标志性成果,日本不只是对琉球实现废藩置县成功,中国还为此支付了50万两白银。(摘自《日本近代史》第119页)
注:这与中国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重臣的“投降洋务运动”是截然相反的定位,日本精英在受辱中变得顽强且具有侵略性,而中国精英则在受辱中把自己变成任人宰割的小绵羊。
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日本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和皇室典范,天皇被确定为国民应该绝对服从的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权威,从而建立了天皇制国家。甲午战争的胜利,鼓舞了日本成为“亚洲宪兵”和“东洋盟主”的信心,鼓舞了日本搭上世界列强“最后一席”的信心,它让日本下定决心参与到瓜分世界利益的进程中。(摘自大石嘉一郎《日本近代史纲要》第128页-132页,第187页)
对外扩张,在日本维新人士看来,还有“失之欧洲,取之亚洲”的思想,不敢报复欧洲,只能从亚洲邻国身上试刀,以转移国内封建反动政府的视线。(摘自《日本近代史》第117页)
◎明治维新过程资本主义的确定(“自立化”是关键词)
日本的工业革命,首先是军事工业的革命,它的基调是:军事生产自立化。到日俄战争以后,日本陆海军工厂的水平大致达到了世界技术水平。(摘自大石嘉一郎《日本近代史纲要》第133页)
其它工业方面,为解决军需问题,日本创立了八幡制铁所,逐年提高钢铁自给率,钢铁业的发展,又促进了造船业和机器业的发展,还加强了军需工业和军事工业的结合,制造军舰也达到了自立化的目标。(摘自大石嘉一郎《日本近代史纲要》第134页)
◎日本重臣对欧洲的考察有别于满清腐臣
特命全权大使,右大臣岩仓具视率领的使节团,经历一年又十个月,考察了欧洲十二个国家,为日本明治维新做了几个导向:所谓实力,只能是军事实力;必须用实力打破亚洲的野蛮,从而统治亚洲;弃亚从欧。换一个角度看,明治维新的最大特点就是构建“对外侵略性”和“对内专制性”的近代天皇制国家。(摘自大石嘉一郎《日本近代史纲要》第153-154页)
注:李鸿章也周游过欧洲,但他只得出了“中国无法战胜洋军”的结论。
◎明治维新中自由民权的开展。
尽管日本天皇制有对内专政的特点,但日本的明治维新过程始终伴随着自由民权的扩散。主要有三个特点:爱国社派系政治结社的潮流;城市民权派潮流;在乡民权派潮流。自由党建立,并且可以严厉批评政府。
◎明治维新中的日本工业革命概述
为了排除列强的干涉,迅速地完成工业革命,必须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需要国家强有力的介入。(摘自大石嘉一郎《日本近代史纲要》第187页)
纤维工业,迅速达到了国际化水平,岩崎,三井,住友,等财阀实力强劲。
重工业,尤其是军火工业,在较短时间内达到了欧美的技术水平,1880年,枪支大炮大体能自给,1905年时,军舰建造技术已经达到世界水平,“武器自给”是至高无上的使命。摘自大石嘉一郎《日本近代史纲要》第193页
矿业方面,三菱,三井,住友,等财阀,已经在矿山中基本实现了机械化运输,研制精炼炉和理工化学,慢慢可以自建熔炉。
工业革命的结果是诞生了一大批极具独立性的财阀,主要有三井,三菱,住友,安田,浅野,藤田,久原,古河,大仓,川崎,石川,田中,铃木,等等。这些有超强实力的企业,开始从欧洲进口,到后来可以自制机床,再到后来可以独立制造各类工业商品。
1870年始,明治政府一面聘请外国技术人员,另一方面抓紧时间自己的高级技术人才,发放大量“创业基金”和“劝业基金”,殖兴产业发展资本主义。另外,日本政府也创办国营企业,例如东京炮兵工厂,成立横须贺海军工厂,1880年的时候,就可以完全无需外籍技术人员而独立建造军舰。大阪炮兵厂,不但生产武器,还可以独立的生产机床、齿轮和其它机械用具,还能生产发动机,还能生产农业机械和桥梁机械。这些国营工厂,最后都以极低的价格送给了财阀。(摘自《日本近代史》第151-153页)
两条道路的对比
长期封建下的中国和日本,都曾是现代科技的盲区,“闭关锁国”这个词也并不只是适用于中国,是适用于几乎全亚洲。不过,当列强来航后,中日两强的统治者和精英阶层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应,尤其是从思想层面做出了不同的定位。
综合分析,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主要存在以下不同之处:
1,面对列强,日本从害怕走向冷静,再走向直接面对,最后走向勇敢地与列强合流。而中国则不同,面对列强,先是自大,后是恐惧,再后就是投降,缺乏自强的勇气和决心。
2,日本精英阶层能正确评估欧洲列强的实力,并找到了日本与列强的差距之所在,坚定地选择了“自立性”这个根本性要点,哪里不足补哪里,想尽办法靠自己的能力实现达到并超越列强的目标。反观中国,精英阶层坚定地认为,中国短期甚至是中期都不可能学会列强的科技和经济,消极地依赖列强“帮助”自己,在几十年的洋务运动中,没有构建一个可以独立自主的产业,连决定国家命运的军队也掌握在洋人手里。
3,侵略并不光荣,但被侵略也不光彩。日本以狼性和侵略性来展示明治维新的成功,从法理和人性上看,当然并不光荣。但是,被人持续侵略一百年,被动挨打一百年,很光彩吗?我看也不光彩。
一艘“黑船来航”就能将日本打醒,至少证明日本人自强的道路选择正确。
两次鸦片战争,一次台湾战争,一次甲午战争,一次八国联军战争,都未能将中国打醒,这就必然导致后面持续几十的被动挨打。在丛林世界,对错并没有绝对标尺,挨一次打不算可悲,挨几年打也还能狡辩,挨一百年打,那就是精神和躯体都出问题了。
我反反复复地强调日本的“自立性选择”,无非是想强调一个核心问题——洋务运动错就错在卖身于洋人。清朝的洋务运动,本质上讲,绝对应该称为“洋货运动”,因为它的结果不只是战争的失败,而是它的所谓洋务产业一直到二战结束时都未能给中华民族撑腰,中国人,不是被洋货打,就是依靠洋货打,一切货都离不开个“洋”字。
历史不远,现实很近,未来就来,谁是什么货,谁需要什么货,全世界都是清楚的。
货,不是侵略的资本,但没有货,就会成为被侵略的对象。
一个大国,未必样样自主,确须核心自主。
写于2020年10月11日星期日
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 孙锡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