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小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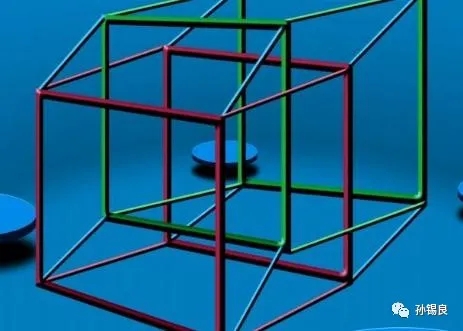
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编撰工作一度非常紧张,普通编修夜夜加班,纪晓岚亦不例外。不过,满清虽专制,乾隆不糊涂,他对纪大才子是别有政策,只要看到纪某眼里有红丝,必定放他回家会妻,第二天早朝,皇帝会发现纪大臣容光焕发,精神抖擞。
乾隆英明在哪里?知人,给空间。纪大臣身体非同寻常,三日不会妻,眼睛必冒血丝。乾隆本就性情中人,懂生活,懂得给重臣生活空间,他也深信,帝恩一尺,奴报一丈,与贤臣方便,贤臣必加倍效忠。
唐太宗,本性好强争胜,并不是真的很想听谏言,但坐在皇帝位置上,又以明主自居,“求谏”必是其赢取民心的形式。时间久了,便对魏征这样直言不讳的诤谏者感到很反感,因为长乐公主的事,他曾愤怒地对魏征讲:“你管了国事,还要管我的家事,是不是管得太多?”长孙皇后知道这事后,赶忙对太宗讲:“这要祝贺皇上啊!皇上英明,臣下才能直言,魏征之所以敢直谏,正是因为陛下英明。”唐太宗听这么一说,就转怒为喜,继续允许给魏征直言诤谏的机会。
清末,甲午战争失败后,一个皇帝,一个太后,假装都爱纳谏,因为再不纳,江山就亡了。然后就出现了康梁等维心人士的涌动。不过,好景不长,1898年,慈禧狭窄的胸口还是装不下良言,她杀了六君子。人,死在菜市口,血却溅在全国有识之士的脸上,真的清醒者对纳谏这事再也不感兴趣了,大家都学会用“违心”替代“维新”,冷眼看着那批遗老腐朽说闲话。不想进谏,不能进谏,不敢进谏,那他们都在干嘛?都躲着在底下搞革命嘛!
乾隆给点小空间,太宗给个大空间,慈禧是不给一点空间。
是物,便要占用空间,一草一木如此,一猪一狗如此,一民一官岂不是如此?
人,是个怪物,不同于常物,生要占空间,死了还要占一小块。为啥呢?因为人除了有肉体,据说还有个所谓的灵魂。就是这个灵魂,活着附体,死了不离,你愿不愿意,都得给它留些位置,否则它就变着法子要干点正义的“坏事”。与之相对应,那些被斥为“没有灵魂”的人反倒是为社会所唾弃。在现实中,如果往高一点拔,灵魂也可以解读为理想和信仰。
说到空间,我又不得不提到被骂正在衰落的美国,也是我跟很多网友的重大分歧所在。我赞成并设法跟美国继续斗争甚至是战争,但不赞成“美国正在衰落和美国民主失败”的结论,扩展到西方其它国家身上,也类似于我对美国的看法,一个言论空间较大的地区,你必须用较长远的视野去观察它,人民智慧的释放与空间自由度正相关。
法国的黄背心运动搞了几年,艾菲尔铁塔都被放过火,香榭大街也曾把轮胎烧得火光冲天,至今也没看见把法国闹散架。美国人因为大选闹得很凶,国会大厦陷落了,议长的办公室物品也被拿走了,国内很多人都说美国要完蛋了。然而,不知不觉,它又平静了,小打小闹,大吵大闹,暴露的问题在另一个过程中会慢慢被消化,新的问题也会在大大小小的“闹事”中不断得到消化。
不停地闹,仍不改变全世界年轻人往那里跑的热情,到底因为什么?
空间,空间,空间。
无论肉体还是灵魂,哪里更易容纳,哪里便更有吸引力。
活着的灵魂真可以上升为思想的话,那么也可以说,某处预留的思想空间大,其产生的创新成果也必将越大,某处的思想空间压缩得越小,其可见的成果必定越小,这不是可能性问题,是必然性问题。一边呼吁同美国战斗,一边认可美国的空间政策,这决不是冲突的观点,而是保持思想上的一致性。人类之间的斗争,早已经脱离了原始的肉搏战,头脑力量远大于肉体力量,用长期竞争力作为评价指标,头脑被束缚的人决不可能战胜思想开放的人。
你获得的空间越大,你为这个空间拓展的热情就越大。相反,你获得的空间越小,你为这个空间奉献的意愿也越小。经常有人问我:“新中国前几十年,生活不好,经常搞运动,思想也被束缚,那么多的成果是如何搞出来了?”我会以纠正的态度回答:“那个时代,看起来要学习红色思想,但其实人的思想更开放,干任何事,只定目标,至于怎么干,全靠集大家智慧,搞“两弹一星”,目标定了,没有谁考核你每年发多少篇论文,没有人让你天天搞没完没了的改革,做成了,大家庆功,失败了,重新再来。那个时候,运动是不少,但运动始终围绕着生产转,根本不用花大量心思去搞庸俗的人际关系,科学家也不需要陪着处长喝茶吃饭,更不用应对没完没了的形式主义评估。”时间可以决定空间,你把宝贵的时间用在了“关系”和“钱”上面,必然没有时间沉下心去干正事,杂事超越主体,你为自己所服务的空间奉献的意愿和价值必定越来越小。
思想空间,何谓大?何谓小?
有人认为,我想干嘛就干嘛,那就是思想空间大,反之,就是思想空间小。
错,想干嘛就干嘛,是自由主义,是把人与动物等同考量,动物随意,人有自制,有规则约束,如果人人都选择“随己意”,人类世界就变成了动物世界。
自由主义错在哪里?错在把“随意”误等于“思想”。
随意,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和自私性,思想则是文明概念,它的根本目标是把自己的智慧奉献于人类有益的正当事业和正当权利。随意干坏事,随意耍小聪明,在最近几十年被解读为“思想解放”,它导致全社会视“假,恶,丑,黄,赌,毒,坑,蒙,拐,骗”为合理化存在,它导致全体国人在相当长时间内对拥有腐败机会表示“羡慕”,它导致各行各业都视“拿来主义”为开放指示灯。所有人都“随意”久了,这个民族的思想就慢慢也会枯竭,决不是空间更大。
本人特意把思想空间进行限制,并非主动缩小自由空间,恰恰相反,限制正是为了拥有,自由主义泛滥的结果必定是你只能获得伪自由空间,或者导致制度和法律的双重打压。合理合法空间的有效释放,对每一个人而言都至关重要。朋友圈,除了废话,除了微商,除了卖货卖保险,你几乎什么也看不到,沉默是精。微信群,不管什么类型,除了偶尔的相互吹捧,也是一片死寂。私聊?不,除了“祝节日快乐”,私下的空间也清空了。
你,我,他,十几亿的你我他,相互视对方为不安全因素,又相互以沉默表示对对方安全的最大关怀。沉默,又被误读成“默认”,你们都不说,那我就代表了真理,最后,我所有的决定都是胜利。沉默,又代表一种死心,过去,单位定个框框,大家可以争争吵吵,对框框的修改有很大影响,现在,大家都不吵了,因为吵也没用,孙悟空都没办法跳出这个框框。
在前两篇文章中,有网友批判我只唱赞歌,实在有些不公。自我公开写文章以来,就没有写过一篇以歌功颂德为导向的文章,更没有写过对现世人的赞美文章,何来的只唱赞歌?爱国,从来都不需要以赞美来体现,因为我真没有看到值得赞美的优越感。承认局部成功,但也一直在呼吁朋友们不要做井底动物,只给你一口井,你的世界就只在井里,也许舒适,也许灿烂,但谁听说过历史上曾留下伟大的井?
灵魂真的寻不着灵动空间,那就让它冬眠,留一副狗皮肉活着也是可以接受的。100条杠线划出来,你就是背下来都相当困难,如何可以做到不触碰?最好办法是装死,死人自然不会说话。说鬼而不知是精是魄,说梦而不知为想为因,苟且刻画,纸上黄梁,浩气尽失。三家村老学究们,不惭不愧,嘴通千古,无知绝倒。
要窥得精神世界之伟大光辉,必先给精神以空间。
聪明的家长,请给予你孩子以合适的空间,一点也行。
附言:
1,有人让谈谈“小马云”一事。答:国人只认嘴巴两张皮,赚钱的时候不批,说是人尽其“材”,榨尽之后全是狠批,有意义吗?在乔治二世时期,英国也有把残疾或流浪幼儿按定式生长并用来赚钱的事例,但英国人说这是从中国学到的办法,并且手段不如中国人那么丰富。古中国有,现今又有了,拿肉体和特殊形体赚钱已经流行了几十年,不新鲜,不奇怪,奇怪的是大家都习惯了。
2,有人问我杨雨教授在央视讲评讲得如何?答:拒绝评论,给自己留点空间。
写于2021年2月26日星期五
【孙锡良,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 “孙锡良”,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