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博士苦难童年刷屏,该感恩还是反思
近日,一位北大博士2009年的论文后记被各大媒体炒作了一番,有人这样点评:“这篇后记比博士论文本身还要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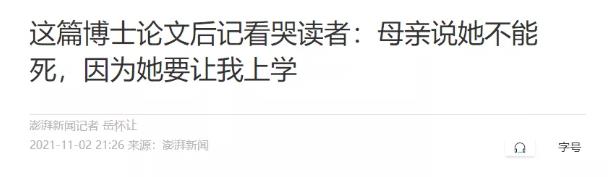
这究竟是怎样一篇后记呢?
作者的名字叫肖清和,1980年出生于安徽潜山,1999年考入北大,文章记述了他苦难的童年。

7岁时,上一年级交不起钱,只好先上幼儿园,荒废了宝贵的一年时间。
8岁时,爷爷病逝,家中无一分积蓄,多亏一位医生资助了20块钱,才最终办了丧事。
母亲四处做生意,穿着连衣裙带异性朋友回村,被村民带到村公所审问。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没有吹散这里浓厚的封建气息。
11岁时,父母离婚。母亲走了,留下孤零零的他,还有6岁的弟弟。
12岁时,家里勉强让他上到五年级。差一点因为交不起考试费用,而失去参加小升初考试的资格。班主任老师来家里做工作,可是,实在没钱。结果,班主任老师代他交了钱,自己考了全乡第二名。这一年冬天离家几十公里去打工,历经千辛万苦挣了75元钱,终于可以上初中了。
上大学之前,常常为学费发愁,靠人救济资助才没有辍学。
初中时遭遇校园霸凌,被打踹两个多小时。
住校时带的干粮没吃完,拿回家喂猪,没想到被饿极了的大叔吃掉。因为粮食发霉,和他相依为命、疼他爱他的大叔中毒身亡。
…………
媒体的论调大家也能猜出来,无非感慨、感动和感恩,外加一点“心灵鸡汤——这可是寒门出贵子的典范,只要努力,就没有跨不过去的槛儿……
这看起来确实挺惨的,尤其是如今我们已经全面脱贫了,很难想象中国的农村还过过这种穷日子。但从国家和社会发展角度来讲,借此鼓吹感恩和个人奋斗而无视背后巨大的社会问题,无异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肖博士在文中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家会这么穷?
但他没有给出答案,或者觉得这是由出身决定的。对于一个北大的文科博士来说,这似乎有点说不过去。这个关键的问题不应该被忽视。
以往我们听说过“大锅饭养懒汉”,把农村搞得不像样,怎么都“B产到户”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幅度提高了,还是这样艰难呢?捌玖十年代的农村,不是都和小岗村一样起飞了吗?同属安徽省,这位博士的家乡为什么就这么穷呢?我都有点怀疑他是不是在编故事了。
农村人这种吃不饱饭、上不起学、死不起人的情况在当时是否普遍呢?2000年李昌平上书总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或许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吧。
三农问题究竟如何?
2000年10月1日两位报告文学作家在农村改革的发祥地安徽进行了一次地毯式的调查,用两年的时间跑遍了安徽50多个市县的农村,又尽可能走访了一大批从事“三农”工作的学者和政要,写了一本名为《中国农民调查》的书。该书揭露了“大包干”之后安徽乃至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其中就包括肖博士的老家潜山。
在笔者看来,肖博士应该看看仔细看看这本《中国农民调查》,或许他就会明白他家为什么穷了。
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两位作家的调查结果吧。
一次,为了了解淮河污染的事,我们曾路过安徽淮北平原上的一个村庄,竟发现那里的许多农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这使我们感到震惊。有一家,全家人竟然用卖菜得来的五元钱就过了一个春节,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刚解放那几年。有位农民掰着指头给我们算了一笔帐,他说刨去种子、化肥、灌溉、用机械种收和这税那费,假如小麦亩产上不到九百斤,这一年就等于白干。而淮北农村能够达到亩产九百斤小麦的,显然并不多见,可以收到八百斤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一般也只有六百斤,就是说,如今农民靠种地已难以为继,但他们仍然要承担多如牛毛的各种税费。
农民们含着泪说:“大包干留给我们的好处早就一点一点被掏光了!”
…………
农村实行了“大包干”的经济体制的改革之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体制也进行了改革。在历时三年的“撤社建乡”的工作中,全国五万六千个公社改制为九万二千个乡镇。国家允许乡镇政府可将乡镇企业上交的利润和管理费、各种集资和捐款收入及各种罚款收入,都作为乡镇财政的自筹收入,这就为乡镇任意增设机构与人员,乱征收、乱集资、乱罚款的“三乱”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以后,随着一系列“分权让利”趋向很强的改革措施,以及“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政策的相继出台,各级政府和部门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泾渭分明的利益关系,于是那些拥有国家权力又“分兵把守”农村经济发展各个领域的部门,便迅速成为既垄断权力又追求利益的行为主体。我们的干部一旦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阶层,与民争利的事就将不可避免了。
截止到一九九〇年,仅由国WY各部委下达文件可以向农民征收的各种项目就高达一百四十九项之多!于是,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利益开始膨胀,收费项目越来越多,收费范围越来越广,收费标准越来越高。
…………
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身上摊派的费用急剧上升,成为不可承受之重。似乎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之后,农村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不再需要国家的投资帮扶,而是要比计划经济时代更多的支援国家。
再加上一些基层干部借机捞钱,一些地区农民抗税抗费的案件层出不穷。一些正直的敢于斗争的农民兄弟遭到残酷的打击报复,乃至被夺去了生命,例如该书记载的“丁作明案件”、“小张庄惨案”等等。
从这些记录中我们可以对捌玖十年代的农村了解一二,也可以对“为什么穷”这个问题有个简单的判断。
肖博士的遭遇不是个别情况!当我们在随着他的回忆感恩一路上的好心人帮助的时候,是否想过还有多少人已经永远失去了像肖博士这样咸鱼翻身的机会呢?
那原因,绝不是他们自己不努力。
我们社会的发展,一个人的出人头地,难道能寄希望于别人偶然性的善意帮助吗?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幸运呢?然而就是有人一直在乐此不疲地鼓吹这样的神话。
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就会明白,肖博士有多幸运,整个时代和农村就有多艰难。
一位老同志在她的教育经历中这样写道:
“1970年代,建立在农村集体(人民公社)基础之上,村村有小学、社社有高中,到1977年全国在校高中生达到近2000万人,此后几年由于包产到户很多农村学生辍学种地、及撤销公社高中,在校人数大幅度下降,直到2000年左右才恢复到1977年的水平。”
的确如此。中国普通高中的招生人数在1978年到1985年锐减,此后就一直在低迷中徘徊,再次翻身则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了。

虽然高中生人数受到出生率的影响,但简单推算一下,可知在这个时间段入学的高中生应该绝大部分出生于1962年到1970年之间,那是中国人口出生率最高的年份。

多少人的教育梦想在1978年戛然而止!其中又有多少是肖博士这样的农村娃?肖博士的故事,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应该鼓吹还是反思?
这正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