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28份“性萧条”调查:年轻人和中产消失的性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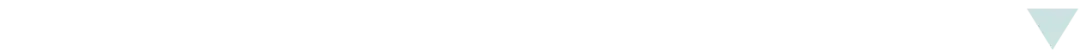

性在中国年轻人中的存在感正在减弱。
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一同发起的“中国人私生活质量调查”中,6828份有效问卷显示:年轻一代的性活跃度在下降。只有大约一半的95后(1995年-2003年间出生)每周有不少于1-2次性生活,频率低于80后和90初。
最年轻群体不是性生活最活跃的人群——这不符合人们的传统印象。另一个数字揭示了更加“冷淡”的现状:在最年轻一代中,14.6%男性和10.1%女性(注意:他们均有伴侣)表示,过去一年没有性生活,这个比例高于70后、80后、90初。
“相当大比例的中国年轻人处于无性婚姻/关系中。”调查发起人之一、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於嘉说。於嘉回忆,她读大学时最火的电视剧是《奋斗》,李小璐饰演的都市女孩偷户口本去结婚。在当年,“为爱奋不顾身”是浪漫爱的典范,可放到今天,恐怕要被观众“骂醒恋爱脑”。
变化从更年轻的00后中得到预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茅倬彦等人2022年调查了全国32282个大学生的恋爱状况:25%的大学生不仅没有恋爱经历,也没有恋爱意愿;46.14%的大学生没有恋爱经历;有恋爱经历的那一半中,发生性行为的不到六分之一。按照一位日本学者的说法,年轻人进入了“恋爱(嫌)麻烦时代”。
这让我想到凤凰网关心过的年轻人选题:这一届年轻人忙着保研、就业(而非创业)、被大厂反复面试19遍、相亲400次无果、等待被裁员或主动当全职儿女、富养猫狗、买黄金、考察鹤岗化的“白菜房”、苦攒定期靠利息生活、忧心晚年预存养老金……要操心的实在太多了,哪有余力谈恋爱?
再来对比一下95前群体。“中国人私生活质量调查”发现,有固定伴侣的国人中,性生活最活跃的分别是80后男性和90初女性。67.9%的80后男性和64.6%的90初女性表示每周至少有1-2次性生活。但超出研究者预料的是:中产的性生活也被剥夺了。
性社会学专家潘绥铭曾指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男性拥有更活跃的性生活。这观念深入人心,但这次调研显示,80后、90后男性里,教育程度和性生活频率的关系发生倒挂。
80后男性中,近三分之一(31.4%)高中以下学历男性每周有3-6次性生活,远高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同龄人;而90后和00初(1990年-2002年出生)研究生以上学历男性中,超过半数月均性生活不到1次。
“我们认为应该特别关注新兴的年轻中产阶级,尽管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但相对而言性生活匮乏。”报告提示道。

事实上,在性萧条趋势上,环球同此凉热。2018年,美国大西洋月刊率先刊登文章《性爱降级》指出这一现象:不过才一代人之隔,高中生性经历就从大多数人都有过变成了大多数人都没有过,美国青少年怀孕率掉到了当代峰值的三分之一。研究爱与性的人类学家海伦·费希尔(Helen Fisher)指导了某调查公司连续8年的美国单身人口调查,“每年整个公司对美国人性生活的贫瘠——这包括千禧一代——都非常惊讶”。
作为“低欲望社会”代表,日本同样难逃“爱的萧条”。日本作家牛窪惠在纪实文学《不谈恋爱的年轻人》中回忆她的大学生活——浪漫爱神剧《东京爱情故事》《悠长假期》诞生的90年代,和男朋友约会可比上课、研讨会、社团活动重要多了。在日本泡沫经济最旺盛的80年代,六七成18岁-34岁男女有交往对象;到2015年,数据发生翻转,20岁群体中超七成女性、近八成男性没有对象。
《性爱降级》作者列举了一连串当代困境,试图理解美国年轻人的转变:“巨大的经济压力,飙升的焦虑人群比例,脆弱的心理健康,抗抑郁药物的广泛使用,流媒体电视,环境中塑化剂泄漏出的雌激素,睾丸激素水平的下降,网上的小黄片,按摩棒的流行,交友软件,选择无力,无所不在无所不管的父母,立业当先的态度,智能手机,新闻周期,信息超载,缺觉,肥胖……不胜枚举。”
悲伤的是,几乎每一条(或多或少)都正在中国年轻人身上发生。於嘉指出,所谓的性萧条更多是一种“被动剥夺”——“原本理应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却在更大程度上被工作、孩子、教育等占据了。全球的经济情况(下滑)阻碍了年轻人形成亲密关系。”

怀着调查数字引发的好奇(和怀疑),我和四对90后情侣聊了聊。他们分别生活在一、二、三线城市,有的已婚已育,有的新婚不久,有的刚结束单身。我想知道他们此刻(2024年秋冬)的情感生活,真的“萧条”“降级”了吗?
30岁的刘也和先生赵睿的生活节奏与许多职场夫妻一致。赵睿每晚加班到11点,到家后需要坐在窗前发会儿呆。为保证第二天的工作状态,他们要在12点入睡。刘也在外企工作,早晨7点40起床、准备通勤一小时时,先生已经坐上去往公司的顺风车了。
赵睿每周单休,刘也有时在周末做副业。他们向我做了一道算术题:两人每月只有三四天能彻底摆脱工作、享受生活——还要排除女性生理期。这道算术题冷酷验证了哲学家韩炳哲在《爱欲之死》里的论断:“绩效原则已经统御了当今社会的所有生活领域,包括爱和性。”
“大家都在996,过什么性生活?”刘也说,答案显而易见,“性的本质是生命力。如果工作把你的生命力给榨干了,就没有空间去发展。”

方冰仪和陈昊已婚已育,他们生活在一座二线城市。下班后,这对夫妻的大部分时间留给了孩子。陈昊认为性萧条总体上是“一个不够普遍的伪概念”,因为在他周边,人们的生活依然“活色生香”,但他同时认为妻子就是一位性萧条人士——这位保持着旺盛精力的男士所期望的周期是每天,这令方冰仪头痛甚至崩溃。“你每天下班、当完妈,你只想拥有刷会儿手机,想睡就睡的时间。”方冰仪说。
恋爱半年的杨晓茜和小胡正处热恋期。两人分别住在某一线城市的东、西两头,每次见面坐地铁就要花1个小时。他们的见面频率保持在每月五六次,性生活频率则斩半。这是双方理智友好协商后的结果——两人都希望把难得的约会放在爬山、攀岩、去公园晒太阳这些事上。在他们看来,所谓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始于“假期过于珍贵了”。“看看蓝天、呼吸新鲜空气也是身体需求的一部分,这可能是打工人更需要的释放。”
林萌和男友吴飞过着室友般的同居生活。在林萌眼中,吴飞是她精神和生活上的最佳伴侣,而不是身体上的。“我经历过(身体)更合适的伴侣。”林萌说,她希望理解并尊重自己身体的感受。而吴飞的态度是:“一直对这事没啥欲望。”林萌听过一个说法,如果结婚第一年每做爱一次打个红色对勾,以后每年换个颜色打勾,人生最后可能还是红色最多。这对情侣的“错位”,最终以林萌的退让告终,她选择自己解决。
2024年1月,韩国播出了一部关于当代人爱欲困境的电视剧,《好久没做》(Long Time No Sex)。一条豆瓣热评写道:“虽然都是冲着性喜剧来的,但是看完四集之后,还做啥呀,穷人光是搞钱就已经掉了半条命了。”
“东亚人都非常累,中国人很紧绷,”於嘉说,“紧绷背后的原因是,我们不是传统的福利国家,非常强调家庭和个人的作用,这导致社会的安全网是不够的。如果我们稍有松弛,就可能跌落到一个非常低的社会位置。”在生存受到威胁时,爱情和性被“合理牺牲”了。
《不恋爱的年轻人》里解释了泡沫经济崩坏如何作用在日本年轻人爱欲消退上:在经济安全感破灭后,“失去1万日元的痛苦感远比获得1万日元的满足感大得多,因此,人们会为了避免失去而过度保护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与之对应的生活态度是:“似乎已经看透了任何事情‘反正不过如此’,这背后溢满了对国家及企业的心灰意冷,‘反正国家和企业都不会保护我’‘反正日本也就这样了’”。由此,这些年轻人带着不符合年纪的“透彻”终于打开“简单活活”的低欲望模式。
而这正是我的单身朋友李念的生活缩影。她自称“70分低欲望践行者”:33岁,在一座三线城市事业单位工作,独自生活,上六休一,朝八晚六,经常加班。这是一份听起来安稳,实则枯燥的工作。李念每天要花费大量脑细胞揣摩领导意图、搞好办公室政治、解决群众投诉。
李念说自己过的是“仓鼠跑轮”式的单调生活,“除了疲惫,没有别的感受”。不仅如此,她对很多世俗意义上的消费——房、车、旅游、买买买——失去兴趣。到了宝贵的休息日,她只想自己待着,更别提发展亲密关系了。“如果我家里再来一个人,可能会让我(已经快被榨干)的生活无限地挤到一个墙角里。”

当聊到我们的主题“性欲望”时,李念打趣自己“英年早衰”。“我对生理需求的欲念很低,它对我来说真的是吸引力不大。”
“你经过一天无意义的工作消耗之后,你会觉得你的生存质量特别低。你说你缺吃的吗?不缺。你的基础生存需求没有满足吗?不,你都满足了。但你就是勉强地活着。”李念说。接受访谈这天,是她连续上班的第9天。她用略带夸张的语气补充道,“我每天恨不得爬到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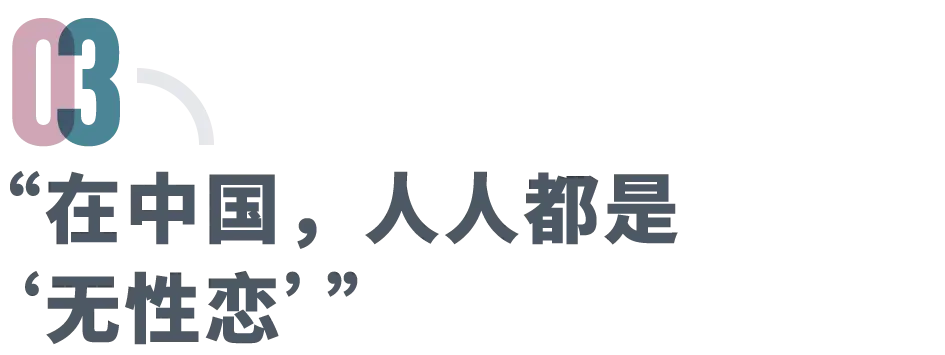
当我们谈论性萧条时,是否应当首先关心什么是性繁荣,或者性正常?
2011年,美国学者曾根据年龄因素对性能力的影响规律,得出了“性爱频率公式”。即用年龄的十位数乘以9,得到数字的十位数代表一个性爱周期的天数,个位数代表应有的性爱频率。比如30岁乘以9是27,代表20天内性生活频率为7次。
李念曾看到有文章写,每周和伴侣发生肢体接触达到多少分钟才是健康的。下面有人留言:“果然不爱了”。李念不认同所谓的“科学依据”,她说:“身体是自己的,你想怎么用它,你就怎么用它。为什么要被这些数字裹挟?”
色阿是性教育团队“莓辣”的创始人。这个她在高中毕业后创立的团队曾把她送进福布斯中国30岁以下精英榜单。“性是普通人为数不多的可以掌握的权利,我们还能掌控自己的身体。”色阿说。但她否定了所谓“正常数字”的观念:“大家总是希望有一个正常值,其实是没有的。尽管有统计意义上的平均值,对每个个体的参考意义非常低。”
刘也有性别领域学术研究背景,她认为,“正常数字”只与伴侣双方的性需求有关——伴侣一起商量出两个人都可以接受的频率,这就是正常数字。

在美国一档亲密关系播客里,一名女性指出自己一直为性生活频率“不达标”感到不安,直到意识到这种焦虑是被大众文化塑造的。媒体和影视作品(包括“小黄片”)持续宣传着并不真实的频率、方式、快感标准,却构成了真实生活的参照系。大西洋月刊通过大量访谈印证了这一观点,“大多数人仍然认为其他人总是有很多性生活,然而事实远非如此。”
相比之下,在中国大众文化中,性耻感仍然强烈地存在着。尽管和日韩共享相似的东亚困境,国内少见《好久没做》这类直白分析情欲问题的影视作品,甚至反向追起了“双洁”设定(原指网络小说中男女主均是处子之身)。即便是大热综艺《再见爱人》——这档火了四季的婚姻纪实真人秀邀请了那些徘徊在离婚边缘的娱乐圈真实夫妻——也十分纯洁。
於嘉是《再见爱人》的观众,在我们见面前,她还在手机上追了一会儿。她从一些嘉宾的隐晦讲述中察觉他们可能存在性生活问题。比如,曾有一位男嘉宾暗示这件事很重要,他妻子却是回避态度。但在节目里,这些内容无法得到严肃讨论。
刘也曾做过无性恋人群的学术研究,并从中观察到一个吊诡的现象:“无性恋在人群占比约3%。(因为)性在国内不能够被摆在台面上,所有人都在呈现自己是‘无性’的状态。这个时候你就看不出来中国人里谁是真正的无性恋。”
“在中国,人人都是‘无性恋’。”刘也说。
一个被讨论过很多遍,但依然值得再次陈述的事实是:我交流过的每位女性都经历过性羞耻阶段。刘也上大学前,对表姐说,结婚前绝对不会发生性关系(她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笃定,并收获了表姐意味深长的目光)。
方冰仪回忆大学毕业后,她和陈昊约会只能“偷偷的”,并对父母谎称是去见女性朋友。家庭禁忌在她婚礼那天突然被打碎了,奶奶当着众人的面交待她,睡在你丈夫的哪一边,就能生儿子。说完,在场亲友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中国人私生活质量调查”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年轻女性的性观念比以往开放,与此同时,年轻男性有向保守回归的趋势。
在“女性在性生活中的角色”问题下,总体上,不同性别、年龄受访者都认为女性可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但其中年轻男性的态度出现了回流——这张图表呈“倒U型”:80后男性更主张性别平等,随后90后男性又回归保守。
而女性版本的图表几乎是一条向上直线:越年轻的女性越重视自己在性生活中的权益。
不仅如此,在关于“性行为目的”的问题下,大多数人不认同“为了生育”——调查强调,“这种转变被视为性革命的意识形态基础”。在女性受访者中,“性行为是为了履行配偶义务”的回答也急剧下降,只有4%的90后女性选择了这个答案。与男性相比,更多的女性认为性行为的目的是表达感情。

当我向方冰仪陈昊夫妻提问“中国人私生活质量调查”问卷里的问题,比如性生活频率以及对这个频率是否满意时,方冰仪坦率回答,她不满意——她认可的频率是“一周1-2次”而不是“每天”。她说她曾向丈夫分享同事的情况,借此旁敲侧击,但丈夫“除了觉得自己厉害以外,没有任何改观”。“我觉得理想的状态是互相取悦,但我现在更多是为了取悦他。”
一直安静旁听的陈昊在此时加入了讨论。这位高校教师礼貌地指出,妻子的冷淡叫作“结构性冷淡”,“所谓的萧条/正常/繁荣是相对的,坐标系是以每个人的情况为原点”。
我对他的说法不置可否。我问他,听到方冰仪的感受后,会做出来改变吗?
“我觉得需要改变的是她。”他答道。
色阿和同事在工作中会收到大量网友的咨询。她发现,男女两性关心的事情不一样:男性更担心身体机能是否正常;女性更担心欲望是否正常——无论觉得欲望太高(频率为每天/次),还是太低(频率为每月或更久/次),她们都会产生羞耻感,害怕自己“不是一个好女孩”。
我问刘也,男性和女性作为主体讨论性时有什么不同。她想了想告诉我,女性更归咎于个人感受/体验,而男性更引向权力。
“男性在谈论性时,本质上是一种对权力的使用。比如讲黄段子,本质上他觉得我凌驾于你,我有权力这样讨论你。”她说,“男性很少勇于暴露性方面的不和谐,希望呈现男性气概。但这也是一种禁锢,他们很难启齿告诉别人自己的困境。”
而女性在聊这个问题时,“更像是女性之间平等、亲密地寻求理解和帮助”。
在“中国人私生活质量调查”的婚姻部分,约 81% 的已婚受访者(76% 的已婚男性和 84% 的已婚女性)认为,婚外性行为是错误的。不过,与20年前其他学者的调研相比,已婚国人对出轨的反对比例下降了14%。
从离婚率来看,一个或许能让关心中国婚育现状的保守人士们安心的观点是,“中国的婚姻其实挺稳定的”。尽管中国的粗离婚率数字一路走高,但是於嘉提到,如果横向对比美国、韩国、日本等国,中国婚姻整体还处于非常稳定状态。重要原因是:中国家庭是“子女中心主义”——孩子在家庭中的角色占据主导。
这意味着,在中国,或者说在东亚,性、爱、婚、育往往是一体的。学者伊庆春曾提出中国人“婚育套餐”的说法,就像买汉堡必须搭配薯条,谈恋爱是为了结婚,结婚是为了生子,生子意味着买房、教育等一连串任务——於嘉提到一组统计数据,2010-2015年结婚的中国家庭里,56%在婚后一年生了孩子,77%在婚后两年完成生育。
於嘉说,也许不是人们对性失去了兴趣,而是被那一系列附带、捆绑的东西吓住了——“性萧条只是一个表象,根本原因是人们想从传统家庭对于个体的规范、约束中逃离。”

牛窪惠也在书中强调了“婚育套餐”的高昂成本。她认为,“在巨大恋爱风险与不良债权已然暴露的现代社会,告诉年轻人‘不要害怕’‘要勇敢地去爱’”是不负责任的。想向年轻人推销婚育套餐,那“大人们”理应“创造出一个能够重获失去之物,即使置身底层也可以逆袭翻身的社会”。
访谈结束后几天,刘也特意发来几条语音。她补充道,这个私密话题有一个时常被隐去的背景:我们的国家、社会希望人们拥有性生活吗?
最近,电影《好东西》里出现了单亲妈妈和女性好友“结伴带娃”的叙事,“离异抱团养娃”“单身互助养老”等话题也被一再讨论。“人们开始探索传统之外的生活方式,它只要能够适应你的生活,能完成婚姻提供的部分功能就足够,因为有的人不需要婚姻的全部功能。”於嘉说。
所以个体视角下的性萧条未必是坏事——如果它符合关系中被忽视一方的需求,比如方冰仪,如果它体现了跳出婚育套餐的勇气,比如李念,那它就是积极的,甚至是自由的。
正如美国性学研究专家黛比·赫本尼克(Debby Herbenick)提醒我们的:性萧条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对坏的性行为的健康反应,“人们比以往更敢于说出‘我不要,谢谢’了”。
应受访者要求,李念、刘也、赵睿、方冰仪
陈昊、杨晓茜、小胡、林萌、吴飞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