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节 | 钟雪萍:“女性”为何不待见“妇女”
导 语
伴随着“女神”“女王”等称谓的新鲜出炉,“妇女”一词正与我们渐行渐远。在一些人看来,用“妇女”形容一名女性似乎暗含了对这名女性的诋毁与中伤。相较于“女性”,“妇女”甚至会招致许多女性主义者的不满。那么,曾经预示着荣光的、能顶“半边天”的“妇女”一词,缘何在当下频频遇冷呢?
今日,食物君特别推出钟雪萍老师2022年11月30日在杜克大学“女性主义理论与帝国主义”会议上的发言。钟老师从阶级视角对“妇女”的起源与衰落,“女性”的崛起与回归进行了解释。钟老师认为,称谓的变迁有其政治语境和历史意义。“妇女”一词的运用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息息相关,因此,对其阶级与性别意涵的判断不应脱离中国革命的性质。而作为后革命时代的必然结果,“女性”的回归背后则隐喻着去政治化的文化转向。
作者|钟雪萍(塔夫茨大学国际文学与文化研究系)
译者 | 王斐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责编|东格 侯Q
后台编辑|童话

图片来源:360网图
在过去四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尤其自90年代初“性别”这一概念引入中国以来,中国学者(多数为女性,但也有男性学者)一直在直接或间接地讨论,应该如何理解西方女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在中国参加的不少与此有关的会议、工作坊和各种形式的活动中,总有这方面的讨论,其中不乏激辩。
比如,2010年在北京举行的题为“社会主义妇女解放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讨论会、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与《妇女研究论丛》杂志联合举办的“革命与妇女解放”研讨会、2018年上海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国妇女解放:文化想象与社会实践”会议,以及2019年夏天,十多位学者(包括若干男性)就美国女性主义中国历史学者白露(Tani Barlow)的著作《中国女性主义中的妇女问题》(2004),在上海师范大学进行讨论交流,对“妇女”(woman/women)这一概念(我下文会讨论这个术语)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发表各自的看法。[1]疫情期间,继续参与了一些网络会议。在那些会议上,讨论和争论仍在继续。

《妇女研究论丛》创办于1992年,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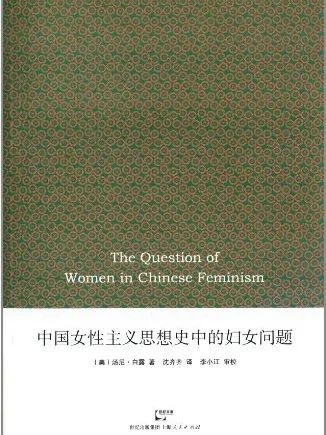
汤尼•白露著,沈齐齐译《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中文版,2012| 图片来源:百度网图
就像其他众多西方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一样,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经由各种活跃的学术交流,中国译介了不少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和主要论述。与此同时,这些理论和论述在中国也遭遇质疑,而且大都来自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颇为了解的学者。
当代中国的这些背景,与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有诸多联系,我将在下文中作一些简短的讨论。

老宣传画:妇女电工 | 图片来源:163网图
我今天发言的标题看上去有点宽泛,但它的副标题“一个与中国有关的阶级视角”旨在把讨论变得具体。确切而言,我将再次回到并分析两个不同的中文用词“妇女”(woman/women)和“女性”(female),反思它们背后的阶级意涵和内部张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这些意涵和张力与(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遭遇的“性别麻烦”有关,如何思考其中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历史层面上的政治原因。
事实上,任何一个了解那些围绕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女性主义争论的人,都知道,在中文里,这两个词语之间一直存在着张力。原因在于跟英语中的“女人”(woman/women)和“女性”(female)相比,中文的“妇女”和“女性”包含更多与历史相关的政治含义。论争也主要与怎样理解这些含义有关,尤其与怎样理解中国革命及其政治语境和历史意义有关。也就是说,虽然这两个词语都可被视为“现代”的“语言事件”,但与对应的英文词语相比,内在于二者的历史和张力更为丰富。这一特征与颇为复杂的中国现代历史和政治斗争直接有关。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我讨论这两个词之间的张力与阶级问题的关系。[2]今天,我将继续这一思路,但着重着眼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的阶级性质,与内在于“妇女/女性”的阶级含义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在很多方面,这两个用词一直或隐或现地反映着20至21世纪中国的革命、反革命和“去革命”之间的矛盾、辩证及其特有的“阶级话语”。如果这两个中文用词都有(尽管是不同的)阶级内涵,为什么相较于“女性”,“妇女”这个词会招致更多女性主义者的不满?而对“女性”一词,大多数女性主义者则少有同样程度的关注和不满?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可以在“女性主义理论和帝国主义”这一主题下来再一次思考并讨论这个问题。
我将通过以下三点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讨论:(1)在阶级意义上思考妇女解放和中国民族解放的关系;(2)简单回顾“妇女”一词的革命性起源;(3)改革开放时代,“去政治”文化转向与“女性”一词的崛起或回归。考虑到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我最后会提出几个问题,并以那些问题来结束这个发言。
一
在阶级意义上思考妇女解放和
中国民族解放的关系
白露教授在她那本颇受关注的专著《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里使用“误用”(catachresis)这一概念,来探讨现代中国的“妇女话语及其运作方式”如何帮助生产“现代”妇女主体。她的研究重点放在若干跟中国历史相关的“运作方式”上,探讨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现代”中国妇女主体的构建及其未完成性。在这个意义上,“误用”这一概念凸显了现代中国妇女主体形成过程中的辩证以及发生轨迹,怎样与历史相勾连。
在题为“理论化‘妇女’”(“Theorizing ‘Women’”)的一章中,白露教授首先提及“妇”这个字的“历史性误用”,然后将其与现代中国“妇女”一词的演变联系起来。她特别指出,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个词被纳入“国家话语”范畴。白露教授的这一论点,与很多女性主义学者倾向于把中共领导的妇女解放定义为“国家女权主义”(state feminism)相呼应。
确实,“国家女权主义”这一提法可以追溯到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之际,并很快成为(尤其是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和评论者习惯采用的提法。[3]

2016年5月25日,作为我国主办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首场配套活动——二十国集团妇女会议(W20)在陕西西安开幕 |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网
有趣的是,在这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意义上的“国家”和“妇女”之间相联系的关注中,经常被忽略的是中国作为一个曾经的被压迫民族(oppressed nation)和“妇女”之间的关联。[4]如果我们把“妇女”与“民族(国家)”放在一起思考,并在“阶级性”的大前提下强调两者之间的联系,会有怎样的发现?
在西方学界,有一个流行但值得商榷的论点,即马克思的“阶级”概念被发错地址,寄到“民族”,被“民族主义”取代并占上风。这个论点也被不少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西方学者接受。[5]但是,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妇女问题和妇女解放引入这一讨论,便可发现这类讨论基本无视妇女问题及其重要的历史和理论内涵,暴露出其自身的“男性中心”以及思考中的盲点。
我在此希望强调一个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殖民统治和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同时以最终建设社会主义为目标。在这一斗争中开展的“妇女解放运动”,包括“妇女”一词,从头开始,就既是阶级的同时也是性别的。正如林春对本发言稿回应中指出的,中国革命中的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贯穿始终,而妇女解放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不可能独立于民族和阶级的解放而完成。这不仅仅由于妇女参与在革命中,并成为不可或缺的力量,更是因为具有双重性的共产主义革命,归根到底同时就是“女权主义”的。
让我进一步展开一下。
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Mao’s China and After: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一书中,作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以第一章“西方帝国主义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软弱性”作为该书的开头。[6]这一章虽然简短,但基本上把中国革命置于中国和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阶级历史关系,以及中国内部的阶级社会状况的背景之下。
迈斯纳呼应马克思的一个观点,认为西方帝国主义是为中国社会革命创造条件的“无意识历史工具”。[7]他指出:“在一个近代经济部门被帝国主义所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几乎不能指望羽翼未丰的中国资产阶级除了充当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属品之外还能干点别的什么事情,不管这个阶级中的个别成员可能对外来统治滋生多么强烈的民族主义愤恨。”[8]
迈斯纳继续说:“现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以现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软弱性为标志:一个弱小的资产阶级和一个更为弱小的无产阶级。但是,并非只有这两个现代阶级是弱小的;现代中国历史状况的基本特征是中国社会所有阶级的软弱性。”[9]
因此,迈斯纳认为,上述条件使得“独立的政治力量”——包括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中国现代政党——的运作成为可能,与其说它们各自代表社会阶级的不同利益,不如说是它们作为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占有者,决定了社会各阶级的命运。[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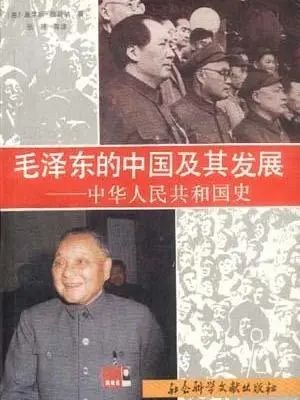
莫里斯·迈斯纳 著,张瑛等 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 图片来源:百度网图
作为西方少数持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中国历史学家之一,迈斯纳在认识到中国现代政治角力与社会阶级之间关系的同时,把中国共产党视为一个缺乏自身阶级认同的“独立政治力量”,实在显得有点简单化(reductive)。简单化的原因在于,在迈斯纳的理论视野里,“阶级”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被清晰地理解为既是“结构的”(structure)也是“形成的”(formation)。而这一观点,恰恰在中共对中国革命的解释框架里得到更确切的表述。所谓弱小的工人阶级相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而言是一个成长中的、强大的阶级力量。而中国与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也渗透着超越国界的阶级内容。
在研究思考中国革命,社会主义时代和后社会主义时期以及各种相关的历史和理论问题时,林春始终坚持首先从阶级角度来理解现代中国和世界。[11]她的新著《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讨论到女权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其中,“阶级与民族: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与不平衡发展”一节呼应了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和历史状况的思考和批评。她用“重叠式不平衡发展”(compressed uneven development)取代通常的“结合式发展”,因为前者更强调“共时性的动态过程,包括被压缩的时间中空间发展的不均衡”。[12]
林春认为,在这个“被压缩的时空运动”中,国内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的结构性阶级性质相连。“全球资本主义及其霸权无情推进的过程,造成一个曾经拥有无与伦比财富的中华文明的陷落”;而“外国侵略和由此产生的半殖民地中国,是产生后者社会政治危机的直接原因”。同时,作为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最薄弱环节”的一部分,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的推动进程”恰恰决定了中国的反抗斗争及其阶级性质。
她进一步指出:
逐渐衰落的清朝沦为资本主义丛林的牺牲品,民族反抗斗争亦随之兴起,中国在其所处的全球局势中成为一个“阶级的民族”(class nation)。……在敌对帝国主义势力的围攻下,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显而易见的“阶级地位”使其抵抗具有民族和阶级解放一以贯之的特征……正是这种历史条件,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具有社会主义前瞻性的创新型工人阶级先锋组织。这个形成中的民族国家被剥削与压迫的历史地位,为形成一种革命民族主义的集体自我意识提供了支撑。[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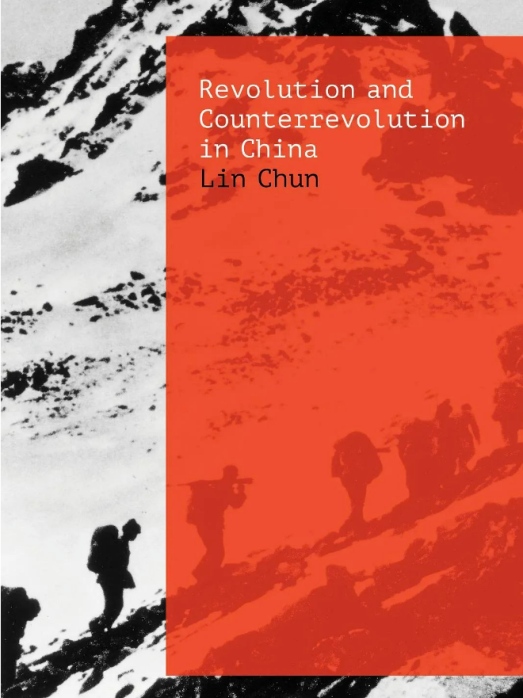
Lin Chun,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The Paradoxes of Chinese Struggle,Verso,2021 | 图片来源:豆瓣网图
因此,本质上呈现一种对抗关系的“阶级民族”(class nation),必须置于资本主义在其初始地区的发展及其全球化扩张的进程和产生的影响,以及与之相对的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各种斗争,努力寻找替代方案以求建立一个资本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和在这些斗争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过渡形式等历史背景下,加以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林春指出必须反对“自由主义、修正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都有”的“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轻视”,这种轻视“忽略了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大背景。而正是这些危机,让中国爆发了全面革命”。[14]
我顺便提一句,也正是由于这场革命的阶级属性及其果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让新中国“荣获”了西方帝国主义对她的仇视。
二
简单回顾“妇女”一词的革命性起源
“中国爆发的全面革命”的阶级性质,同时界定了中国妇女解放的阶级属性。也就是说“妇女/女性”之间的张力及其辩证,存在于上述提到的“被压缩的时间”之中,与革命领导的妇女解放(以及对其的不满)的阶级属性密切相关。

妇女也能当英雄,劳动妇女是伟大的革命力量
图片来源:163网图
“妇女”是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布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中选择的用词。决议特别指出,没有妇女解放的目标,整个革命纲领就不完整。它还规定“中国共产党认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15]明确了“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通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保护女工及童工的利益”“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三项任务后,决议进一步规定,“这些运动,不过为达到完全解放目的必须经过的站驿,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妇女真正的解放是不可能的”。
由此,“妇女”一词作为阶级话语被明确政治化,日后成为中国革命话语中的一个关键词。关于其含义的论争仍在持续。
当然,并不只有中共领导的革命最先开始呼吁妇女解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中国改良派或革命派的男女知识分子,都从各自的立场和角度表达了改变妇女境况的观点。不论直白还是隐晦,他们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和辩论,以及他们对革命的呼吁,都与中国正作为为独立和解放而斗争的阶级民族,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
首先,被有些女性主义学者视为中国第一位女权主义者的何震(何殷震)。她在20世纪初写下《女子解放问题》《论女子劳动问题》《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等多篇文章。除了关注传统文化如何控制和约束妇女之外,何震还敏锐地觉察到社会经济结构与妇女(“女子”)之间的关系,并同时质疑现代欧洲妇女“自由”背后的经济和阶级问题。
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何震坚持认为,妇女必须在不依赖男人的情况下寻求自身解放。她指出妇女必须打破传统性别关系的重要性,这个传统性别关系是一个女性依赖男性的系统,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引入一个坚实的社会维度。她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对上层妇女与下层妇女之间同样存在的阶级压迫的认识,以及对欧洲妇女的“虚假自由”的质疑,都标志着“中国的女性主义”,从一开始就在社会—阶级意识中孕育而生,并且以在理论上持有一种不妥协姿态为特征。[16]

何殷震 | 图片来源:新浪网图
第二个例子是与20世纪初何震的论点相呼应的鲁迅。他在谈到“妇女问题”时更加不遗余力地呼吁需要一场革命。确实,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的鲁迅,始终支持妇女解放,并坚持认为只有在中国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妇女解放。
很多中国人熟悉的例子之一,就是鲁迅1923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的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关于为什么这个问题比关注易卜生戏剧里的中产阶级妻子下决心离家出走更为重要,鲁迅进行了切中肯綮的讨论。
“走了以后怎样?”鲁迅问道,“伊孛生并无解答”,他用他标志性的讽刺语气指出,“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孛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17]“娜拉走后怎样?”鲁迅的问题超出了原著小资产阶级的个人选择范畴。对于娜拉来说,尽管她已经觉醒,但她“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鲁迅说:“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18]
在此,鲁迅间接响应了何震的观点,继续发问:“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19]
通过将妇女解放与反对现有经济制度联系起来,鲁迅认为我们需要一场真正的革命——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尽管他承认自己也不知道这场革命“从那里来,怎么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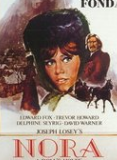
1973年英国约瑟夫·罗西导演《傀儡家庭》电影海报

鲁迅先生 | 图片来源:百度网图
这些一百多年前提出召唤革命的“妇女问题”讨论,在中国革命及其妇女解放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几十年以后的今天,仍然没有过时,对讨论妇女解放以及性别与阶级之间关系的问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可是,“妇女”这一用词本身却似乎未能同样保持新鲜。这就引出下面第三点。
三
改革开放时代,“去政治”转向
与“女性”一词的崛起或回归
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伊始,中共领导的妇女解放,以及“妇女”一词,就开始遭遇各种女性主义者的批评。这些批评和后来的“性别”转向,同时又都伴随着“国家”(state)从性别平等宣传教育的公共领域中撤退,以及在同样的领域里出现的(用Danial Vukovich的话来说)“自由主义的报复”,(或隐或显地)谴责整个中国革命,并把质疑延伸到革命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妇女解放。[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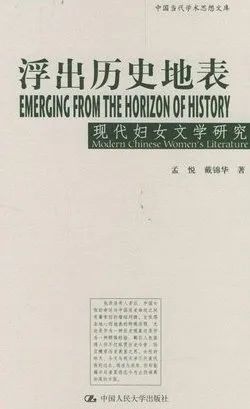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图片来源:百度网图
与此同时“浮出历史地表”的“新”批判视角,质疑“妇女”的所谓中性/雄性化,呼唤找/招回“女性”及其被遮蔽的“女性特质”。[21]在这些“新”走向和“新”视点下,“妇女”这个字眼,随同对“妇女解放”的被质疑,遭遇到“性别麻烦”:被视为“革命男权主义”的产物,在男性为坐标的基础上提倡男女平等,缺乏对“女性特质”的充分认可和认识……等等。
西方女性主义认为真正的妇女解放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对此观点的接受也很快成为评估和判断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妇女”一词的“自然”标准。延续这一标准,除上述的没有充分认可“女性特质”以外,还认为妇女主要受制于“国家利益”,缺乏从自身出发的“自我”意识等等。在文化层面上,“妇女”这个被认为不够“女性化”的形象也成为公众嘲笑的对象。内涵于“妇女”的阶级和女权双重意义及其政治性,则在这样的“去革命”“去政治”的语境下被消解。
可以说,在“后妇女解放时期”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反向的“妇女”性别歧视。取而代之的“女性”一词,象征着被压抑的“女性气质”的回归,把妇女问题从革命领域重新归类到“女性”“个人”“身体”“唤起性欲的存在”以及与男性二元对立的思考层面里。
可以说,在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自身面临的“历史的狡计”(cunning of history,Nancy Fraser语)的全球影响力“协助”下,我们遇到了中国版的“历史的狡计”。[22]
一方面,就“男女平等”而言,面对国家从明确维护性别平等的话语和政策中撤退,“性别”概念的兴起,有可能为增强性别平等政策和社会文化实践提供必要的理念和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它也确实如此。
然而,另一方面,如果不同时维护和坚持妇女解放的遗产和实践,“去革命”的“女性”和“性别”概念容易陷入个体的单薄,成为小资理念的收容品。改革开放以来,对女性和女性气质的强调,在出现脱离历史语境的“女性本质化”走向的同时,在市场化的大潮下,“女性特征”迅速被消费主义的欲望及其逻辑所吸纳所界定,向乐于站在资本一边而非劳动一边的小资产阶级性别主体倾斜,其“性别意识觉醒”的思维方式往往以简单的“男/女二元对立”为前提。
换句话说,在“后革命”的阶级转型中,“妇女”的衰落伴随着“女性”的兴起/回归,伴随着城市小资产阶级文化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以及后者愈发彰显的其自身阶级和性别诉求的某种结合。
不过,中国革命的深厚性以及内在其中的妇女解放和阶级解放的直接关系,在转型后仍然被继续不断书写和认识,无论是在历史层面,还是当下现实层面,譬如打工文学,尤其是来自皮村的女工文学,等等。

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记录了改革开放后,当代打工群体的文化历史变迁 | 图片来源:搜狐网
必须指出的是,与此同时,在中国这个“后妇女解放”的历史语境里,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也遭遇了自己的“性别麻烦”。正如我在发言一开始提到的,面对上述的各种矛盾,许多中国女学者通过对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的历史和遗产的重新强调和思考,质疑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局限性和话语霸权。我们也许可以问,这一在中国面临的“性别麻烦”是不是在本质上也反映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自身的一种“阶级麻烦”?
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我以为可以进一步提出和讨论其它相关问题。由于时间关系,无法进一步展开,但我想以下面三个问题来结束我的发言:
1. 帝国主义发展的历史中是否存在性别维度,后者又如何与阶级(和种族)的维度产生联系?与马克思主义的“离婚”(divorce)是否以及怎样阻碍了(西方)女性主义在这方面的思考和理论化?
2. 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如何不再继续躲在非西方世界的反帝斗争背后,走到前台直接面对和处理“帝国主义”这个问题,并与之斗争?
3.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有可能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做出贡献吗?如果有可能,应该怎么做?如果没有,那又是为什么?
谢谢大家!
参考文献
[1] Tani Barlow,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有一个翻译备受批评的中译本,汤尼·白露《中国女性主义思想中的妇女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2] Xueping Zhong, “The Class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Women’s Liberation and Twentieth-First-Century Feminism”, Feminism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ing Zhu and Hui Faye Xiao, eds.,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76-102.
[3] 关于中国的“国家女权主义”,已有相当数量的英文出版物。以最新相关论著为例,可参阅Wang Zheng,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A Socialist Feminist Revol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4] “nation/民族(国家)”跟 “nation-state/民族—国家”含义不同。
[5]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83.Gellner对民族主义的讨论引发讨论和质疑。1997年,作者在《新左翼评论》上发表题为“对批评的回应”(“Reply to Critics”)。Gellner 的这一观点也影响了一些西方的中国研究学者。如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6][7][8][9][10]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李玉玲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页;第5页;第6页;第7页;第11页。
[11] 参见Lin Chu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China and Global Capitalism: Reflections on Marxism,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s,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12] Lin Chun,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 ,Verso, 2021, p.8.
[13] Lin Chun,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p.10-12.
[14] Lin Chun,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 p.37
[15] 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编:《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1918—1949(第1册)》,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年,第50页。
[16] He-Yin Zhen, “On the Question of Women’s Liberation.”, Lydia H.Liu, Rebecca E.Karl, and Dorothy Ko eds., 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Essential Texts in Transnational Theo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53-72.
[17][18][19]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6页;第168页;第170页。
[20] Danial Vukovich, China and Orientalism: Western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he PRC, Routledge, 2012.
[21] 对于这种与冷战有关的 “性别转向”的批判,详见Lingzhen Wang, “Wang Ping and Women’s Cinema in Socialist China”, Signs 2015 vol.40, no.3, p.589-622.
[22] Fraser, Nancy, “Feminism, Capitalism, and the Cunning of History”, Cahiers du Genre, vol.50, no.1, 2011, p.165-192.
文章来源:转载自公众号“现代中文学刊杂志”,2023-08-18,原文刊于《现代中文学刊》2023年第3期。
原标题:现代中文学刊 | 钟雪萍:女性主义理论与帝国主义:一个与中国有关的阶级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