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文科的学问要怎么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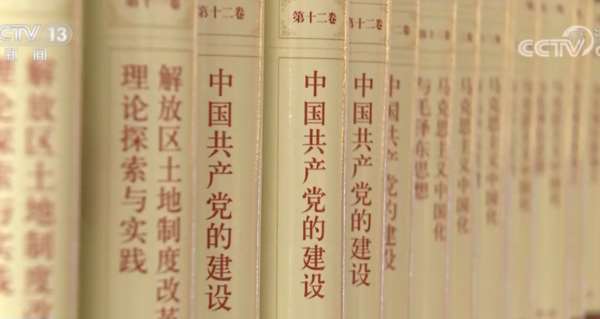
一般说来,在中国,说到所谓文人,多指研究文科类学问的人。似乎研究理工科学问的人,除了特殊情况之外,很少在文献中花费太多的时间。而所谓文人,似乎主要的工作都是在钻研文献。无论是古典文献,还是国外的文献,这些文献就是文人们主要的工作对象。
当然,也有一些文人不太钻研这些文献,而这些文人主要是写文、作文、行文。简单说来,就是以写为主。当然,他们也会读书,也有的人读过不少的书。然而他们的日常工作都是在写,或者为了在写而做各类准备或者其他工作。一般说来,写文的人,大多都会与现实相联系,无论他的观点是对是错,他们写文的时候,不太可能离开他所生活的现实。即使是那些创作历史小说的人,他们也无法脱离现实。
而那些以文献为工作对象的文人,似乎有一种另外的感觉,在其中某些文人心里,研究学问就是要脱离现实,至少要与现实保持相当的距离。在他们看来,如果要做学问,但还总惦记着现实,那么这个学问是做不好的,也是做不深、做不透的。在他们看来,只有专心一致去做学问,才能算作真正的文人,才能算作学问家。
我对这样的现象总是不太理解。有时候,看到介绍这种学问书的文章,例如在某些似乎专门给文人看的报章里,论述某些学问著作的时候,我总觉得是在看天书,总是弄不懂他们想要表达什么。他们可能太热爱自己的学问了,他们完全不需要考虑非专业以外的人是不是能看得懂。而那些所谓的专业,在我看来,也是非常狭窄的。这个狭窄专业之外的,即使是属于同一大类专业的人士,也未必看得懂,也未必有兴趣。我不知道,这样的现象算不算自娱自乐。
在我读到的会引起我兴趣的学术文章中,还是那些既讲学理,也没有离开现实的文章。读这样的文章,总感觉能得到一种启发,能够有所收获,甚至会有某种领悟。例如,原北京大学哲学系朱德生教授所写的学术文章或者学术著作,我每当读到这些文章或者著作时,都感觉到一种津津有味,有一种乐趣,会产生某种愉悦。
朱德生教授是研究西方哲学史的。这门学科在今天一些文人当中,也是他们研究的对象。但是当我读到他们中的有些人所写的学术文章或者学术著作时,除了感觉枯燥无味以外,更有一种有意卖弄,以示自己学问高深,而旁人无人能懂的那种洋洋自得。而朱德生教授的文章或者著作里,就没有这种令人生厌的气息。只是,像朱德生教授这样做学问的人确实不是太多。
在朱德生教授的文字里,总会感受到他的研究与现实的人们,或者与现实的世界,以及人们对现实的感受,存在着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并不是那么直截了当,有的时候似乎若隐若现。他并不是刻意要表现出这样的思考,但是在无意之间却形成了一种非常自然的启示。
张文木教授说,做学问要有生死感。或许,像对于朱德生教授所研究的西方哲学史领域里,这样的生死感未必有那么鲜明,但绝对不会没有。而在其他人文学科或者社会科学中,有的领域确实需要那种鲜明的生死感。所谓生死感,就是人文学科,或者社会科学,在当代都是有着鲜明阶级性和斗争性的。很多领域中的斗争就是生死斗争。哲学同样也是如此。因此,哲学领域研究的生死感,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没有那么鲜明,但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至于其他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史学以及文学,都免不了这样的生死感。这些学科在历史上,在今天,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着各种阶级关系,以及相互斗争过程中的,的思想意识。而这些思想意识反映的都是有阶级性和斗争性的思想产物,这些思想意识同样也都是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在上述学科中,你不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就必然要为敌对阶级的利益服务,两者没有调和的余地。任何离开所谓阶级意识和斗争性来做学问,不可能触及到问题的实质,也不可能真正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张文木教授研究的国际战略领域,就是这样具有强烈生死感的学科。在今天的世界上,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美国的霸权主义,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矛盾,至少是剥削与反剥、压迫与反压迫之间的矛盾。而中国的崛起,对于霸权主义国家一直得以剪羊毛的剥削,就形成了一种反制。这是霸权主义绝对无法容忍的。因此,张文木教授的国际战略研究,就不可能不针对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的种种行径,要找出与其针锋相对斗争的方略。这种针锋相对,就是鲜明的生死感的体现。
今天中国的崛起,以及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为今天世界上的霸权主义,以及霸权主义的跟班们所不容。所以无论是哪个学术领域,生死感与斗争性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近几十年来,西方意识形态的侵入已经相当严重了。这些意识形态的渗透,已经严重危及我们的崛起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所以,我们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中的研究,不可能回避这场斗争,不可能回避斗争中所涉及到的具体问题。
说到底,讲生死感可能会让某些人不太舒服,感觉火药味太浓了。但是,我们做学问,一定不能脱离实际,这一点应该不会有问题吧?要接触实际,目的就是要解决实际问题。只是纸上谈兵,不解决实际问题,这样的学问不做也罢。当然,解决实际问题,不一定要提出特别具体的方案和具体方法,但至少要提出一种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与方法论意义上的思考。无论我们研究什么领域,研究什么问题,这些领域与问题一定与当下的现实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如果能抓到这样的现实联系,我们的学问做起来就有广阔的天地。如果看不到这种现实联系,只是在纸堆里乱翻乱挖,固然也可能出一些学术成果,但这样的成果毕竟还是有点肤浅,原因就在于它过于脱离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