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上一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主席对全党干部发出号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毫无疑问,这个时间点非常特殊,正是在我们三年自然灾害进入到最困难的关头。毛泽东主席在此时发出这种号召,自然颇有深意。毛主席这次号召中指出:
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
发那么多表格,报上来说粮食增加了,猪也增加了,经济作物也增加了,而实际上没有增加。我看不要看那些表格,报表我是不看的,实在没有味道。河南要求下边报六类干部情况,今天通知明天就要,这只能是假报告。

就在这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有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
有了好的方针、政策,你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没有。郑州会议的方针政策是对的,只有一条不对,就是不要算账。郑州会议是三月初开完的。有浙江的经验,有麻城的经验,到了四月上海会议就搞了十八条,决定旧账坚决要算。我写的那个批语还早嘛。那两个月我动笔批的文字有两万字以上。打笔墨官司没有多少用,两万字也好,再加一倍也好,不起作用。底下县、社、队封锁,你有什么办法。
这些会议是什么会议?是反对浮夸风、放卫星、虚报占产量、强征粮的会议,主席自己说了,他写的相关内容就有两万多字,想打笔墨官司我都能给你翻出来。但是呢——不起作用。底下县、社、队封锁,你有什么办法。
可以看出来,老人家已经非常生气了。半年之后还有一段吐槽,他用“等于放屁”来形容自己当时的重要批示,还说出了“不懂社会主义”这种重话:
我在北京召集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1961年6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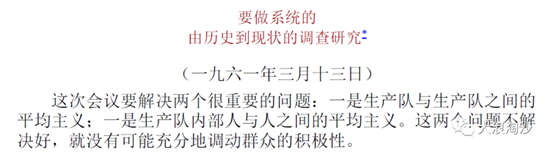
为了解决先锋队出现的问题,除了大规模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领袖还做出了两项重要呼吁,一是不要压制群众反映意见:
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
第二,是鼓励干部去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
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人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毫无疑问,这一系列组合拳,是与引发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有着直接关系。
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58。
“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毛泽东,1959年3月5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讲话的背景是反对弥漫全国的“浮夸风”、“共产风”,他老人家发了这么大的火、说了这么极端的话,一方面因为全国这一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另一方面因为官僚集团沆瀣一气、欺上瞒下,他屡次强调这个问题,依然遏制不住这股歪风。他老人家气愤之下只能说出“我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反对亩产万斤的浮夸风,被某些人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像小孩子斗嘴一样说“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在1958年11月9日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讲话中,毛主席就指出了现在全国盛行的“浮夸风”,并强调:“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
并强调:“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最诡异的地方在这里,派人去调查了一番,调查结果是——产量没有虚报,共产主义实现形势一片大好。
毛主席是正儿八经身经百战的人,怎么会不知道一亩地产量多少。在随后的武昌会议上,又强调了这个问题:“听说有几个姑娘说,不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我看她们是想独身主义的,把这个作挡箭牌。据伯达调查,她们还是想结婚的,八万斤是不行的。”
还有钢产量的问题:“西北去年只有一万四千吨,比蒋介石(的钢铁产量)少一点,今年五万吨,超过蒋介石,明年七十万吨,增加了十三倍,这里头有机会主义吗?华南去年两千吨,今年六万吨,增加三十倍,马克思主义越到南方越高,明年六十万吨,增长十倍。”
可以看到,这时候主席的话还是比较轻松的,用“她们是想独身主义”“马克思主义越到南方越高”这种又诙谐又讽刺的话敲打他们。但是问题必须还是要解决的,做出了如下强调:
“这些数字,还要核实一下,要各有根据,请富春同志核实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声。”
“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从反面考虑一下,翻一番可以,翻几十番,就要考虑。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到?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虽然你们说要搞基点(钢、煤),但要几个月才能搞成?河北说半年,这还要包括炼铁、煤炭、运输、轧钢等等。这要议一议。今年有两个侧面,中国有几个六千万人,几百万吨土铁,土钢,只有四成是好的。我看还是稳一点。水利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搞他十年,不就是五千亿了吗?我说还是留一点儿给儿子去做,我们还能都搞完哪?”
与此同时,还以事实为论据,批评了基层中出现的种种魔幻现象:
“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战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欺骗不了的。”
“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
最后,毛主席总结说:“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要进行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能做到就好。”(1958年11月21日)
结果呢?“这TM8岁?”“这就是8岁!”


人家一口咬定这就是八岁,你能有什么办法?要是斯大林,早就命令手枪队上子弹了。然而毛主席还是宅心仁厚、菩萨心肠,还是想着拯救同志、改造干部、整顿风气。
某些地方盲目追求产粮,或者说为了宣传效果,盲目推进庄稼密植,有的甚至要在庄稼上面站个人,来证明自己种得够密、产粮够高。这个小问题毛主席都注意到了,他苦口婆心地在《致六级干部公开信》(六级为: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里写到:
“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1959年4月29日)

小孩好说,大人难办。大人后面还有大大人,这不是打大人的屁股,是打大大人的脸啊!
强调了半天有用吗?没有用。事态开始越来越严重,因为有些地方卫星放得过高,农民开始出现自发的瞒产情况。对于这一问题,毛主席批示说:
“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
“有个下放干部写信回来说,他所在的那个公社规定要拔掉三百亩包谷,改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当时包谷已经长到人头那么高了,群众觉得可惜,只拔了三十亩,但上报说拔了三百亩。这种造假是好的。”
“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以多报少。以多报少危险不大,以少报多就很危险,一百斤报五十斤,不怕,本来是五十斤报一百斤就危险。”——可以看到,毛主席永远是站在劳动人民这一边的。
很明显,毛主席心里是门清的,上面说大炼钢铁好钢率只有四成,农村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可见他早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但是他提,有人反对——或者说当时大多数人都反对,说这是打击积极性、说这是机会主义。在八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就与这一派人马进行激烈的交锋:
“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开始搞八亿土石方。以后翻了一番,变成十六亿。八亿是机会主义,十六亿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几天又搞了三十二亿,十六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后来提高到六十四亿了。我们把改变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马克思赏识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评我。”

“其实今年好钢只有九百万吨,轧成钢材要打七折。只有六百多万吨。不要自己骗自己,粮食是不少。各地打了折扣以后是八千六百亿斤,我们讲七千三百亿斤,即翻一番多点,那一千一百亿斤不算,真有而不算,也不吃亏。东西还存在。我们只怕没有,有没有,没有查过,在座诸公都没有查过。
就算有八千六百亿斤,四分之一是薯类。要估计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讲清楚,把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县开个会,吹一吹,有什么不可以,别人讲不爱听,我就到处讲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脱离群众,被美国占领,国家灭掉,打游击。”(1958年12月9日)
主席这些话是论辩的最高境界——有数据支撑、事实打脸、调研为基石,又诙谐幽默、讽刺爆表——然而依然没有什么卵用。于是就有了上文中那段话“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不是代表你们官僚;“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就是旗帜鲜明的反对浮夸风、共产风;“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为什么浮夸风难以遏制呢?归根结底还是官僚主义的问题。譬如说吧,官员考核肯定是看KPI的,我说今年我们乡亩产一万斤、密植三千亩,这就是我的政绩。我汇报到县里,县里一看不错,作为我们县先进乡的样本申报到省里;省里一看很不错,作为我省人民积极推进“多快好省”实践的典范汇报到中央,建议全国推广,咱们是省的日报先给宣传一波,先号召别的县乡学习一下。
结果报道中央,毛主席一看不可能,我们都是种过地的,怎么可能你这说一万斤就一万斤了,批示建议核实,不要吹牛。但是你这样不是打下面一串人的脸么,下面人的政绩怎么算?然后一层一层核实下去,县里向省里汇报,木有问题我们调研过了就是亩产万斤;省里向中央汇报亩产万斤真真切切,主席你别这样,这不打击我们干部积极性么?就是上文中毛主席讲话说的“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
那么问题来了,是谁在“扛着红旗反红旗”呢?是谁在主席三令五申之下,依然顶风作案不思悔改,甚至还想颠倒黑白呢?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传》的作者之一李捷在讲座时说过:有些材料不能公布“不是因为说出来以后有损于毛泽东,而是说对现在有些人不利”,所以只能采用“著而不述”的春秋笔法。大家自己体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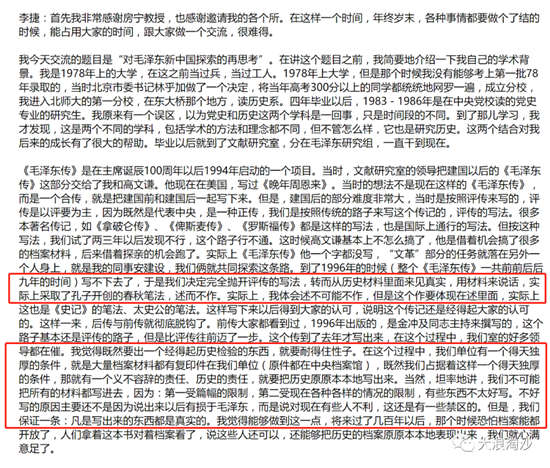
去年建国七十周年的纪录片《我们走在大路上》,其中一段话擦了一点边,但没有明说,这就叫春秋笔法,可以与本文互为照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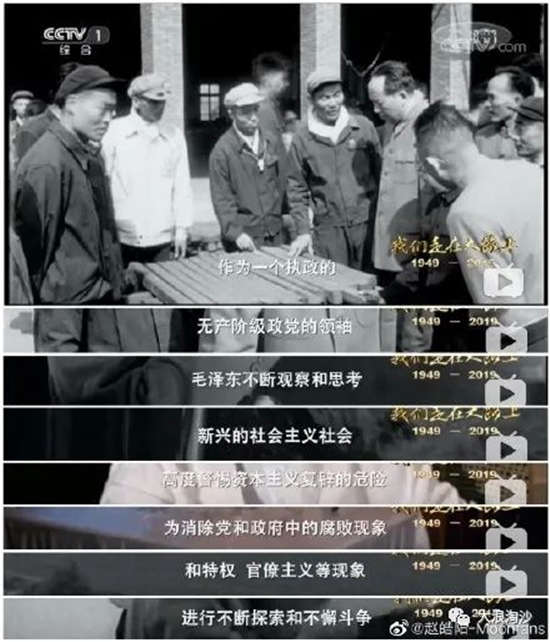
这一问题在“共产风”中体现的更加典型。“共产风”虽然跟“浮夸风”一直相提并论,但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先来看一看毛主席批评“共产风”的言论: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
“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的历史吧。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末,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1959年2月27日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一周之后,毛主席又开火了:“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如不愿不等价交换,就叫没有共产主义风格。这叫什么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现在什么公?猪、鸭、鸡、萝卜、白菜都归公了,这样调人都跑了。河北定县一个公社有七、八万人,二、三万个劳动力,跑掉一万多。这样的共产主义政策,人都走光了。劳动力走掉根本原因是什么,要研究。”
还是那句话,无论是浮夸风还是共产风,毛主席心里是门清的。他至少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基层事实:“甚至征购粮款也被公社拿走,国家出了钱,公社拦腰就抢。这些人为什么这样不聪明呢?他们的政治水平哪里去了。问题是省、地、县委没有教育他们。”(3月1日、3月5日的讲话)
共产风的本质与浮夸风相同——都是官僚主义,但是表现逻辑是不同的。生产队是以村为单位的,生产队长是村民公选推出的、德行和能力足以担任的农民,一个村可以有好几个生产队;而人民公社是相当多个生产队与村庄的联合体,领导就不是农民了,而是干部,通常是副县级或县级的领导。那么他们把生产队的粮食全部收集上来,还要把猪、羊、鸡甚至茶几、剃头刀都要收缴上来,为什么?赵本山回答过这个问题——腐败啊。
腐败是一方面,彼时共和国从上到下还是非常清廉的;更多的则是官僚的权力,天然就处在一个集中的趋势,这是官僚的本性决定的。把生产队的生产资料、粮食甚至农副产品都集中起来,越集中权力就越大。英国讽刺喜剧《是,大臣》中,常务秘书汉弗莱为什么这个活也要揽过来、那个职务也要兼任,而且天天想着扩大预算和编制,这就体现了官僚的本性——他们渴求权力就像鱼类之于水。
权力集中了就怎么样呢,比如说就会有脱产的文工团,选一些适龄少女唱歌跳舞——我们领导操劳一个大公社这么累,连农民家的剃头刀都要管,需要劳逸结合适时放松,这很合理吧?毛主席批评过这个现象:“劳动分配,现在极为不合理,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分配太少,而工业,行政人员和服务行业的人员太多(有的多到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必须坚决的减下来。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
但是批评没有用,你不可能指望官僚被你骂了几句就良心发现,欺上瞒下是他们最擅长的技能。毛主席不止一次对这个问题发过火:
“六中全会公社决议的一套制度,二个半月来根本没有实行。问题不这样提,共产风会继续发展。为什么六中全会的决议没有阻止这股风的发展?是不是只有冀、鲁、豫三省?是不是南方各省道德特别高尚,马克思主义多?我就不相信。”
“整社三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在武昌会议时,不感到这个问题,回到北京感到了,睡不着觉,九月就充分暴露了。”
“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未执行,等于放屁。”(三月五日的讲话)
但凡下面这些官僚有毛主席百分之一的良心,他们也会睡不着觉。就比如说文工团这个事,三番五次强调,并在1959年2月28日专门下发了一个文件,题目就叫做《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但是正如上文所说“根本没有实行”。
毛主席点名批评了一些“扛着红旗反红旗”的省份,看看他们找的是什么借口:“河南说‘虽有本位主义情有可原,不予处分,不再上调’,安徽说‘错是错了,但不算错’。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上级犯了冒险主义,翻箱倒柜,‘一平、二调、三收款’,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这是什么主义?”
——后面这半段是毛主席在嘲讽,因为地方督抚(尤以五大金刚为首)吹出来这种风:我的小弟们虽然做错了,但是初衷是好的,所以就不处分啦;反倒是你毛主席,今天让我们干这个,明天让我们干那个,做出了工作还不表扬,实在是打消干部积极性啊。他老人家就直接指出本质——不要把锅甩给基层,就是你们这些督抚的错,你们搞这种强盗式的征调,算什么主义?
还是那句话,毛主席永远是站在劳动人民这一边的,对于欺上瞒下的官僚与苦苦应付的人民,他老人家做出了如下定调:“劳动力到处流动,磨洋工,对这点我甚为欣赏,放一炮,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
如何解决现在的问题,主席提出了两点措施,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政治的。经济的是:“现在银行不投资农业,我建议每年增加十亿,十年搞一百亿无利长期贷款,主要支援贫队,一部购买大型农具,十年之后国有化了,就变为国家投资了。”
政治的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适当积累,合理调剂,收入分配,由社决定,多劳多得,承认差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跃进就没有了。我这篇话不讲,就不足以掀起议论,这几个月许多地方实际上破坏了价值法则。去年郑州会议,就吵这个问题,拉死人来压活人。”
“拉死人来压活人”就是某些集团,认为主席指出浮夸风、共产风的问题属于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这个回应我们上文说了,主席表示:“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马克思赏识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评我。”
上上下下这么多问题,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主观主义,怎么办?怎么解决?毛主席走了两条路,一条常规的一条非常规的。常规的就是“整风”的老套路,他老人家力主推进了“干部下放、军官当兵、五项并举、蚂蚁啃骨头”——包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干部参加劳动”。
还有一条非常规的路,烈度就比较高了,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用的“天魔解体大法”。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