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羽亮:法律界“大神”的翻车,大反攻信号强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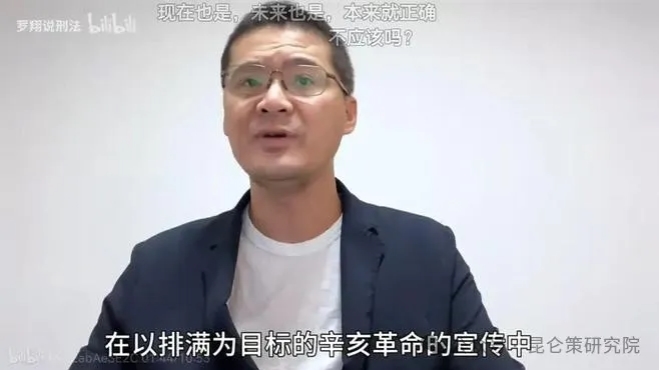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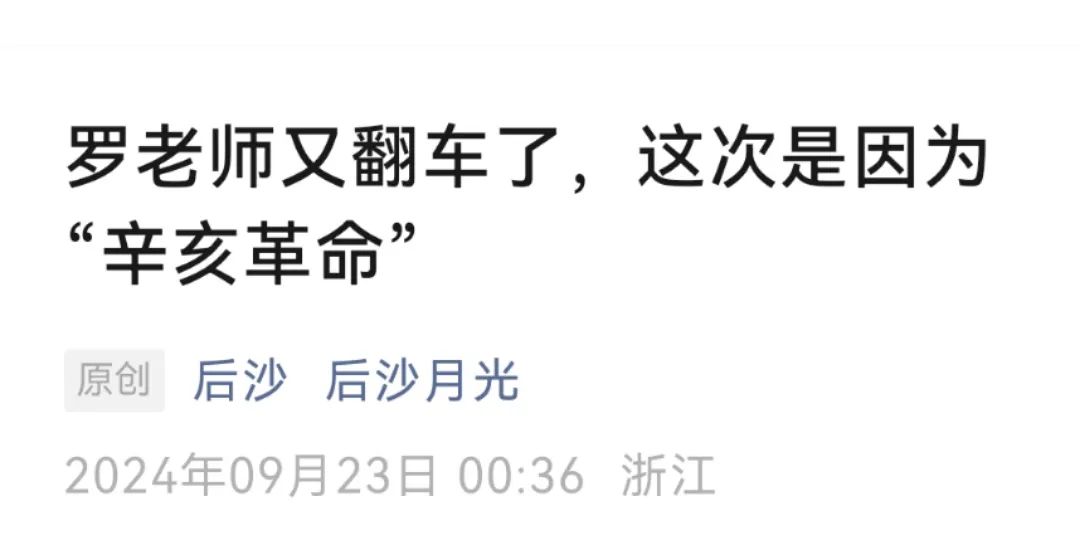
近日,法律界顶流公知、千万粉丝头牌“罗圣”大翻车。该网红长期霸占舆论潮头,背后的推动势力耐人寻味。借助这一网络事件,作为一个曾经头铁无比的西方法学学习者,让我们一起层层剥笋,揭开西方法学背后的隐秘。
一、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法学
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宪法第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从1999年开始,法制机构普遍设立,法学院系遍地开花,法学专业门庭若市。政法大学最时髦的词汇,就是宪政、民主、法治、自由。同学们普遍受到的教育是,应该减少政治对法律的干预,政治应该放在法律之下,政法大学应该改成法政大学,政治人物不应塑立在法学校园。像律师一样思考,这个想法,就像野草一样,在脑海里扎了根。
当时的教授,主流都是学习西方,反对中国例外论,都认为中华法系是死法系,中国法制史是老古董,“中国法治的进化”就是西方化,言下之意中国的法治还很原始。法学教授中最吃香的是比较法学,龙宗智的《相对合理主义》被认为是向现实妥协,梁治平贺某方的《新波斯人札记》被认为是法学启蒙,整个法学界弥漫着向西方学习的声音。
那个时候,研究中国法文化的教授,就像过了气的宫女一样不受待见。中国法制史被归为前现代法律体系,在话语权上被设定在卑贱地位,连报考博士都少到可怜。法学教授都以认识贺某方、与体制对抗为荣。从事公检法司和公证工作的法律人,几乎清一色的认为现代法治的方向就是英国和美国的方向。
甚至民国时代也被热烈歌颂。比如,民国东吴大学“养天地之正气,法古今之完人”的校训,就被广泛赞扬。大学校园里流行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如果没有读过,感觉就有点跟不上节奏。
凡是西方有,而中国没有的东西,都被大量的介绍和移植过来。比如表达自由、废除死刑、违宪审查、司法独立、一人一票,等等。教授们为了介绍这些观点,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些闻所未闻的情况:比如说到表达自由,介绍的例子就是国外的裸体游行;比如说到共产主义社会有没有法庭监狱警察,举出的例子就是发生了性暴力犯罪怎么办?这些有争议的例子,都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求知热情。
显然公序良俗应当尊重,裸体游行在中国是违法的。至于共产主义社会有没有暴力机关,毛主席早就说过一万年后还有阶级斗争。有些人故意拿机械唯物论静止的观点混淆视听,诱骗了大量的大学生,我那前后几届同学就是明证。还记得一次轰动校园的讲座当中,主张“相对合理主义”的主讲人做完主旨发言之后,被现场嘉宾毫不留情地评价“这是有史以来最庸俗的理论”“介于应然和实然之间的怪胎”,从理论到实践被批了个狗血淋头。看到主讲人有点下不来台的样子,听众从内心里反而挺有意思,大家更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
同学们听到学校里有个老师,代理一个案件挣了800万律师费,哇,第一次感受到法律人也可以成为富裕阶层。还听同学们说,那个讲诉讼法的老师,开的是豪车,每次上课没有穿过同样的裙子。才知道很多法学老师也是兼职律师,收入颇丰。
即使是多年以后回过头来看,受过系统的法学教育,仍然是深刻洞察社会的思维方式之一。然而随着社会阅历的增长,特别是跳出法学看法学,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法律阶层,就会发现法学的自我局限。
二、走出象牙塔,重新审视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越接近于学术,就越想着法律应该独立于政治。越接触于实际,就越觉得世界是一个整体,人很容易被某个局部所蒙蔽。比如,站在霸权金字塔顶端的美国,认为人权首先是政治权利和自由,你只要承认了就得带着枷锁和人家赛跑。中国主张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和发展权,所有后发国家都认为没错,你如果不承认,就去学印度,一条路修的歪歪扭扭,遇上钉子户就让路,人权比干净的水还重要,所以有人笑话印度要人权不要厕所。
其实,法学只是看问题的一种视角,并不是唯一视角,每个人所能达到的正确认识,根本上来源于自己解除认识遮蔽的程度。比如,法学解决不了地方经济发展问题,解决不了贫困地区脱贫问题,解决不了公交车上的让座问题,解决不了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问题,更解决不了国际政治问题,甚至解决不了依法缺德问题。让一个法学博导去主政一个深度贫困县,一定会对其产生深刻的教育意义。
如果我们从货币角度看美国,1944年的黄金本位货币体制,到1973年就被挤兑崩盘了,这已经是历史的事实。那么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美元再次因为货币贬值而被挤兑崩盘,这完全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是现在如果有人说,美国的法治和民主也会崩溃,可能会有很多人还不相信。
如果不管不顾我们所处的时代和阶段,再一次拿起西方的本本和经验,我们就一定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而主观主义盛行是我们事业失败的思想根源。思想上的幼稚必然导致行动上的盲从。而我们很多同学在思想上抵触政治,远离政治,奚落政治甚至以反主流政治为荣。这到底是无知还是个性?到底是对人民有利益,还是对人民有害处?
那么,我们是明知美国给中国设置了进入发达国家的陷阱,我们还要往进跳吗?还是既然看到了的陷阱,一定要设法避开?要不要区别一下,到底是因为傻,而不知道存在陷阱;还是因为坏,明知道有陷阱,还要故意往陷阱里带?这是法学教育者应当要引以为戒,并且要教育广大同学和人民的课题。
所以我们说,在法学上也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是为人民服务的法学,一条是为资本服务的法学。我们是要走一条立足国情、实事求是的法学发展道路,还是要走一条照搬照抄、鹦鹉学舌的法学发展道路?从我们的历史看,我们要学习一切文明成果,走出一条真正能够富国强兵、长治久安、人民幸福的道路。
嘴上说誓死捍卫别人表达的权利,实际上却从思想深处把中国历史、中国政治贴上异类的标签,戴上“东方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的帽子,一边倒地贬低排斥抹黑推墙砸锅,这到底是一种话语暴力,还是一种学术自由呢?毛泽东同志讲“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只要不是恶意解读,我想都会为这句话扎起大拇指!
港澳台是我们最好的民主法治教育基地。现实最能击碎主观主义者的迷梦。湾湾的乱象,就是抢夺选票,无所不用其极。湾湾经济最高时,占到大陆的45%,目前下降到4%,跟深圳市差不多。香港的乱象,就是挟洋自重,乱港分子在英国呼吁恢复“南京条约”,无知的惊掉下巴!香港经济最高时,占到大陆的20%,但是目前连3%都不到。闹来闹去,最受苦的还是人民群众。历史不会歌颂乍起的兴盛,后人不会膜拜早夭的繁荣,站在五千年先贤肩膀上的炎黄子孙,怎能做短视的跪族?
三、驳斥几种常见的错误观点
(1)器物崇拜宗教化。崇拜飞机、汽车、手机、网络,谁说美国民主的不是,就搬出这些器物,要把器物也划清界限,目的是浑水摸鱼,制造思想混乱,掩护错误观点突围。如果按照这种观点,全世界都得给中国人民返还4大发明乃至成千上万的中国文明成果的专利费,那么后来的所有知识科技能否创造出来都还是个问题。所以显然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要么是在抬杠,要么是脑残。
(2)把美式民主宗教化。谁说美式民主的不好,就立即反唇相讥。凡是美国民主制度有的,都想移植到中国来。只要中国没有,就骂中国不民主。你说它是金钱控制的选举,政治献金是黑洞,游说公司是拉皮条,新闻媒体拿钱说话,穷人根本上不了台,它跟你死磕,反正选举就是好。
(3)对美国地理的极度无知。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美洲大陆,这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有且仅有一次,而且这一次也快岌岌可危。美国的长期政治稳定根本原因是亚欧大陆不断自残,以致于孤悬海外的美国偶然渔翁得利。恃强凌弱靠的是黑老大地位,胁迫世界喂养美国,一旦跌下神坛,欠账迟早是要还的。
(4)不区分美国内部的资本阶层和普通民众。美国财富的集中度是令人咋舌。3.3亿人当中,1%的富人占据了近40%的财富,2015年他们的平均收入是99%普通人的26.3倍。储蓄率仅7.6%,如果发生金融风险,只能裸奔了。历任总统,还没有草根。资本阶层,比如洛克菲勒等超级家族,财富传递六代以上,根本原因在于制度设计有利于资本转移。固化的资本体制下,有谁听过美国扶持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5)看不清天道酬勤这一人间至理。有的人看到美国人开挂般的自信,看到这届美国人不用多少辛勤劳动就可以获得廉价商品,但是看不到,美国人80%的都是月光族。透支消费和睡在历史的账本上,已经极度掏空了美国的国家信用。当气球吹大了之后确实很好看,但是一旦戳出一个小孔,很快就没气了。
(6)认为美国不会产生法西斯势力上台。这种观点就像印第安人天真的认为白人不不可能屠杀自己一样。可是历史证明,美国人不仅有合法的屠杀印第安人,还有合法的贩卖鸦片,还将屠灭印第安人的日子定为感恩节,将大麻泛滥美化为民主自由。短短两百多年的历史,就断言美国民主制度的完美,也是一种宗教般的偏执。
(7)认为中国误解了美国的善意。这种观点认为,美国对中国没有恶意,是中国误判了美国的企图。其错误在于不懂大国政治,顶级国家之间都是短暂的合作者,潜在的竞争者。就像俄罗斯完全拥抱美国之后,美国仍然给他一个冷屁股一样。俄罗斯的清醒正是因为伤透了尊严。
(8)把美国说得一无是处。什么都不能学美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美国在反英建国过程中还是有它的进步意义,其在传播软实力,民间组织运作,大学教育,孵化创业项目,科技成果转化,在吸引外来优秀人才方面,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看美国一定要一分为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9)看不到美国已经发动超限战。比如对港台藏疆的手段,比如对越南、缅甸、蒙古、印度的怂恿,对网络账号的选择性封号,对爱国大V的穷追猛打,对教育、文化、宗教系统的持续渗透,特别是对香港乱港分子的大力支持,对华为公司的大规模抹黑,对重要战略节点地区的煽风点火,这是国家利益的对抗,其烈度不亚于一场局部战争。
(10)以为我们没有搞过直接选举。中华民国早就搞过总统选举,要不然也就不会有“贿选总统”闹剧了。蒋氏父子还上演了你方唱罢我登场,中间选了一个傀儡“过渡”。小蒋还自称要带头终结“独裁”,明明是在中美竞争中被逼的无计可施,却粉饰为“无私无我”。试点直接选举,在我国乡村治理中早就试点过,但发现金钱力量、裙带关系、黑恶势力投机上来,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央视《新闻调查》多年前就曝光过山西某村的选举过程。我们要擦亮眼睛,理直气壮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11)认为美国会永远强大下去。很多人思想上转不过弯来的原因之一,是美国稳定并且强大了200多年,英国稳定并且强大了300多年,认为一定是西式民主法治起了作用。岂不知,这是列强洗白上岸后的一套伪辞。英国早已从日不落萎缩为跟班小弟,龟缩在小岛还能混的下去主要是利用原有优势吸引全世界富人输血苟延残喘,这套玩法已经失灵。美国的崛起是亚欧大陆不断自残的产物,离不开压迫吸血全世界掠夺式供养,这是世界历史和地缘政治的特例,已经走到击鼓传花的尾声。
(12)误以为西方民主国家对内都是很人道的。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对外野蛮一点,甚至会杀一些人,但对内是很好很好的,所以要移民,死也要死到美国去,那里是彼岸,只有那里有自由。这就很傻很天真了。我们的留学生,现在上完学回国的比率已经超过2/3了,用脚投票的结果已经说明了问题。
(13)认为法律能解决所有的社会纠纷。很多纠纷可以通过调解,化干戈为玉帛,中国自古就重视德润人心、事前教育,国史、方志、乡规民约、家规、家训、家谱、宗祠、祖坟、节日无不润物细无声,民心也是无形的审判官,基层有德高望重者居中调解的传统,谤木、鸣冤鼓等来信来访渠道,监察御史可以望风言事,我们有的干部还有点不自信,其实这正是中国文化的道义所在,也是引进西方法律制度,并不能从根本上、便民地解决问题的明证所在。
(14)认为废除“六法全书”有点可惜。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华民国在败退大陆之前把主要的六种大法都建立起来。但他们忘了,法律是保护现有秩序的,人民解放战争摧枯拉朽,不平等条约一概废除,社会主义改造,公有制的建立,为今天中国的强势崛起奠定了根本前提,给“六法全书”招魂的话,建议去湾湾看看绿色恐怖和依法分赃。
(15)认为言论自由就是西方话语自由。从话语权来说,法学界是少数几个濒临沦陷的领域。大量两面人霸占讲台,心里对新中国政法横挑鼻子竖挑眼,宣扬欧美法律就是现代法律,其他法律都是前现代法律;一人一票选举领导人就是民主政治,非一人一票选举就不是民主政治。他们对党的领导、公有制、人民军队等国之柱石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放大短期、局部、个体的不公、短板而无视人民群众人权的巨大进步。
四、剥开西方法学的表皮
在后发国家的语境里,没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就没有长期的政治稳定;没有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就没有经济金融的主权;没有国家的扶持,等着民间自我积累,黄花菜都凉了。西方大喊环保,事实上是贼喊捉贼。如果按照西方的人设,后发国家只能当手工奴、资源奴、金融奴。如果没有中国王者归来,世界真的没有后发国家的活路!
知识产权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都是西方列强欺压后发国家的隐形门槛。标准化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倾销法、反补贴法、产品质量法、对外贸易法,都是精心设置的进出口壁垒。给新兴国家套上枷锁,戴上脚镣,然后跟发达国家一起跑马拉松,公平吗?稍有反抗,就灭你,就换人,正义吗?有人要说,谁让人家发达呢?这是历史、文化和技术积累过程的无知,打不过强盗,也不想独立自强,反过来还歌颂强盗?
发达国家通过血腥积累,掌控了教育、知识、科学、技术、金融、贸易、媒体等优势资源,以保证后发国家始终处于附庸地位。你想学先进科技吗?来交学费。你想买专利吗?来交专利费。你想要著名商标吗?来交特许使用费。你想坐飞机吗?来我这买。你想投资吗?来我这开户。一旦看到快要丧失技术霸权、再也不能骑在世界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就不顾任何规则,立即撕毁合同,各种的撒泼耍赖,这种伎俩屡试不爽,直到遇上中国。
看看世界地图,很多国界都是帝国主义用直尺划出来的,你只要遵守国际法,就得遵守这个既成事实,法律在维护强权方面不仅没有主持正义,反而是在为虎作伥。在国际贸易法律关系中,强国可以一票否决从而瘫痪争端解决机制,受侵害国拿着国际贸易法实际上跟废纸一样,法学界在这个时候应该回答,法大还是权大?孟晚舟事件,比十本法学教材还顶用。
所谓的意思自治、诚信为王、契约精神,英美法系的判例法、衡平法多么多么好,多么多么法治。看看香港那些外籍法官出的洋相,警察依法抓人,他依法放人,逼的警察没办法,站在法院门口继续抓。资本集团在幕后笑得很得意,乱港分子拿了钱也挺开心。经济呢,民生呢,他才不管!这哪里还有一丝法治精神,这分明就是政治,这分明就是生意,这分明就是依法缺德!
在国际公法领域,法学界曾经赞叹,外交领域所有的规则,比如照会、斡旋、谈判、妥协等等,都是欧洲国家对近代世界的贡献,言下之意中国和其他国家在这个方面是缺席了。而随着美国掀起阿拉伯之春、出兵阿富汗,以及俄罗斯出兵叙利亚等,以往的文明之辞,反过来暴露了野蛮本质。污蔑中国没有妥协的文化,反而让人搞明白了,中国有一诺千金的信义文化。
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民选领导,表面上是选民选举,实际上是被国际大资本东家控制的“总经理”,竞选资金来源于大资本,萝莉岛黑料就是大资本拿捏台面人物的“投名状”。在这样一种分赃政治下,其当选者专门给资本集团串场子,透支国家信用,把积累多年的人设都给整没了,就是为了让背后的大老板满意,却让人民群众背负更大债务,承担资本狂欢后的一地鸡毛。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是契约精神,不是法律为王,而是要多自私有多自私,要多失信有多失信,要多滑稽有多滑稽。
敌人是最好的老师。反面是最好的教材。毛泽东同志对此洞若观火:帝国主义,能够不讲理,绝对不讲理。
五、我们可以得出几个基本的判断
第一,法律是政治的延续。我们教科书中教了我们多少年的,还不如特朗普大统领一通王八拳,对我们的教育意义更大,让我们真正的触及到了资本主义法律的政治边界。学法的同学,大可不必对政治那么抵触。
第二,法律是有阶级性的。体现的是影响力占相对强势群体的利益,具体到美国现阶段而言,更多体现的是美国本土工业资本的利益,也就是制造业为主的力量。所以美国金融资本才有了真正的危机感,躺赚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第三,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美国政客现在最捶胸顿足的,也许正是美国宪法彻底的分权体制,各地方各财团不会听统一号令,限制了短期当选者长期视野和整合国力,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抱负。而资本的本性又不是公有制,天然的自私自利,会继续上演鼓破众人捶的活剧。
第四,资本才是美国真正的统治者。无论特朗普还是拜登哈里斯,看似口无遮拦自由表达,其实他何尝不知道,绝对不能得罪大资本集团,如果真的挡了大资本的利益那就会跟安倍晋三一个下场,不显山不漏水就可以物理清除。这哪里是什么法治国家,纯粹是黑社会政治。随着美国国债高企,金融资本加快离场,本土工业资本拯救美国的计划必将失去支点,这座大厦从活体变成骷髅,很可能是一瞬间的事。
第五,中俄同盟是美国的噩梦。大国政治是世界的主流。面对中俄欧达成统一战线,美国又气又恨又无奈,打又打不过,骂又不顶用,离又离不开,封也封不住,上半场是中美联手终结苏联,下半场是中俄联手送美国一程。这是地缘政治大势。
第六,霸权转换如同走马观花。从荷兰、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苏联到美国,所有的世界级霸权,都没有超过200年,可见霸权的治理效能之差。如此推论,美国龟缩到美洲一隅,重新回归100多年前,甚至300年前的世界地位,才是一种常态。
六、我们要反思法学教育中的学阀作风
法学界充斥着西方化的思想路线,对中国化的思想路线不以为然,污称中国自古以来缺少契约精神,缺少人权,缺少人文,缺少人道,污蔑中国历史都是东方专制主义。这种学阀作风横行其道,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体现出惊人的无知。
说到底还是利益,一些利益代理人,紧紧捆绑在灯塔国的战车。留学、访学、报项目、评奖项、孩子出国也是一种变相的精神朝圣之旅。如果让他们讲法学的中国方向,一是知识储备不足,二是论文写不出来,三是讲课讲不出来,四是项目报不出来,五是名气提不上来,六是代理费收不回来,七是吹牛吹不出来。
其主张说来很简单,就是把美国、印度、湾湾省的乱象复制到中国大陆来,民选首长,审判机关独立,检察机关独立,国防力量独立,电视台卖掉,报纸电台谁有钱就能办,那么只有一个结果:地方自治了,中央削弱了,不要国企了,贫困地方彻底歇菜了,大资本为所欲为了,老百姓就跟湾湾民众一样,二十年原地踏步。
如果你让他去美国和印度移民去投票,他还以爱国的名义赖着不走。你建议他空降到俄罗斯去体验民主,他还是爱祖国爱的不愿离开。你说他双重标准,他回答不上来。你让他去主政一方试试,他可只管杀不管埋。反正搞乱祖国,只有人人投票,才能无人负责。(关于金权和政权可参考阅读《中国的国有企业为什么必须存在?》)
你告诉他,我们现在人民代表也都是选民投票选的,他死活不承认,觉得剧本不对,套路不对,背景不对,人选不对,一句话,不是资本集团推出来的。法学学者蔡某某去世后,其子在英国留学,表示祭祀父亲时,希望烧一张选票。你看他还是崖岸自高地俯视,看不上我们人民代表的选票。其实都是祖国的领土,要想给父亲尽孝,可以去港澳台烧嘛!
七、中国法学界必须走中国道路
中国法学界和世界法学界,都面临着如何认定“普世价值”,哪些属于真正的普世价值,哪些属于夹带的私货,甚至植入的木马?我们应该怎样的看待西方法学?是顶礼膜拜?还是平视西方?甚至是俯视西方?
骂人很容易,把事情干好不容易。如果明知西方民主化的结果是中断民族复兴大业,我们就绝不能掉进西方民主化的陷阱。比如前苏联,很快就可以达到自废武功乃至自行了断。更不能掉进美式债务经济陷阱,让金融资本彻底掏空整个国家信用,一两代人享福而给子孙后代埋下还不完的债务。
一个国家,只许自己放火,不许别人点灯;只许自己在技术高地上躺赚,不许别人自力更生推进产业升级;只许自己先跑出了二里地,才允许别人带上脚镣起跑,那么它本身就失去了道义,也就失去了合法性。即使它的国内法,以及被它胁迫下制定的国际法,确认了这种行为的合法,也不能掩盖其非法的本质和面目。比如,纳粹的崛起和覆灭。
同学们,同胞们,法学是一门显学。如果要想学好法律,就要能跳出法律,在多维的角度去审视,你才能够收复自己的精神主权,才能够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才能真正的觉醒起来。同学们,一定要有信心,道义在我们这边,未来在我们这边。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湖畔真邻”,修订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