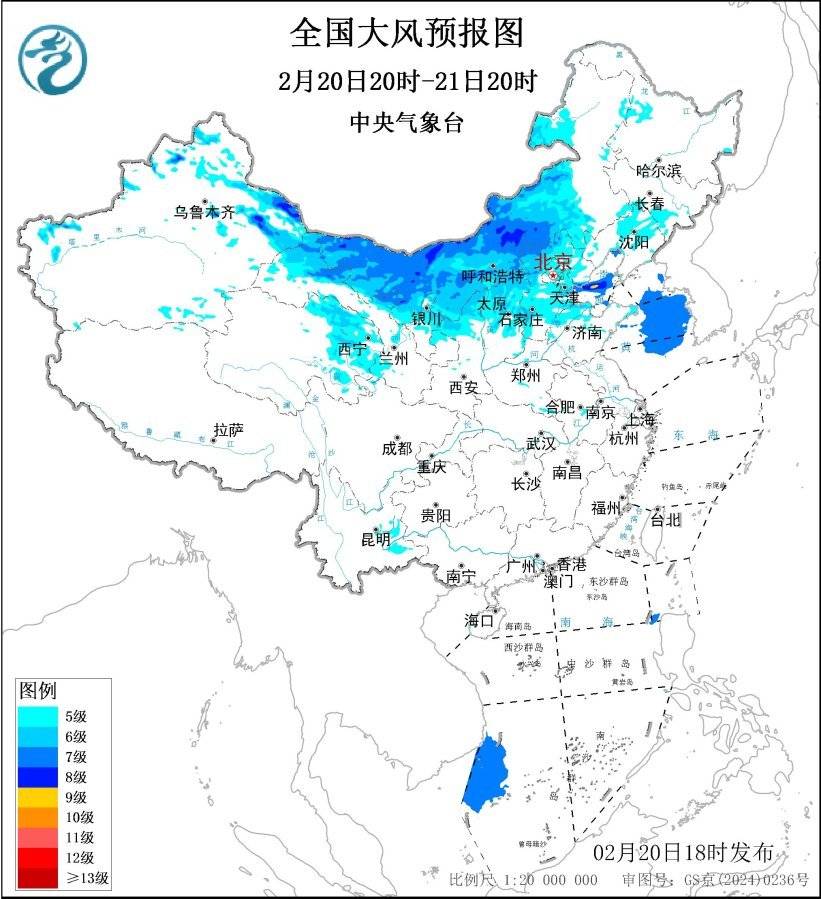煤不让烧,气用不起,河北冬季农村的取暖问题啥时候能解决?
当一种政策的推行,是以牺牲一部分人最基础的生存需求,来满足另一部分人更高层次的生活追求为代价时,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的错位。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代价的转移,还被巧妙地包装在“市场化”和“个人选择”的话语之下。

不能因为整个国家在跑步前进就忽略了那些被撞倒的人。
——贾樟柯
关注河北的取暖问题。
河北农村取暖问题最近又冲上了热搜,为什么说又呢,因为这早已不是新闻,而是河北人最近几年冬天都必须面对的现实。
只不过今年的讨论声量更高了,或许是因为在普遍感到寒意的当下,我们更能体会彼此的困境。
自己淋过雨,所以更想为别人撑把伞。
问题的根源其实并不复杂,一句话就能说清:煤不让烧了,气又用不起。
过去烧煤,一个冬天两三千元就能换来满屋暖意。
如今改用天然气,根据省人大代表杨辉素的调研,要让一间100平米的房子维持在18度的基本室温,一个取暖季的开销高达七千到一万多元。

简单算一笔账,2024年的数据,河北农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为2.2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一半。

一年近半的收入,只为换取一个不被冻僵的冬天。
这道选择题,对大多数家庭来说,答案从一开始就写好了——那就是冻着。
白天不开,晚上少开,人靠电热毯和厚被子扛过去,温暖,成了一种需要计算、需要克制、需要权衡的奢侈。
这一切,都源于一场初衷良好的变革。
大约十年前,为了治理北方的雾霾,尤其是为了守护京津地区的蓝天,一场声势浩大的“煤改气”、“煤改电”工程(即“双代工程”)自上而下地展开。

工作组下乡入户,拆掉煤炉,装上壁挂炉,雷厉风行。
到2020年,许多地方基本实现了“散煤清零”。
起初,较高的燃气补贴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矛盾。
人们以为,这只是转型期短暂的阵痛,适应一下总会过去。
然而,近十年过去,当年的阵痛非但没有消失,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尖锐。
当年的政策制定时,或许有着“海量专家”的精密计算,但他们可能算清了天然气的热值与价格,却没有算清普通人生活的韧性与脆性。
他们的精密计算,是建立在一个经济持续上行、补贴永远充足、务工收入稳定的理想模型之上。
但现实是,财政吃紧,补贴从最初的1元/立方米,大幅“退坡”到0.2元/立方米;

国际气价上涨,而许多家庭赖以为生的外出务工收入却在缩水。
更不必说,农村自建房普遍保温性能不佳,热量散失快,进一步加剧了取暖成本。
于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浮出水面:我们追求的蓝天,究竟是谁的蓝天?
同在一片天空下,我们对“蓝天”的需求并不在同一个维度上。
对于早已将温饱视为理所当然的城市居民而言,清新的空气是更高层次的“安全需求”,甚至是关乎生活品质的“精神需求”。
然而,对于那些还在为一屋温暖而挣扎的河北农民来说,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最底层的“生理需求”——不挨饿、不受冻,才是他们每天睁眼就要面对的现实。
当一种政策的推行,是以牺牲一部分人最基础的生存需求,来满足另一部分人更高层次的生活追求为代价时,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的错位。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代价的转移,还被巧妙地包装在“市场化”和“个人选择”的话语之下。
当补贴退潮,有人会轻描淡写地说:“是他们自己为了省钱,选择不开暖气的。”
这句话看似无懈可击,却恰恰忽略了这背后根本不存在真正的“自由选择”。
当温暖变得如此昂贵,当一个最基本的需求成为一种经济负担时,所谓的“自愿”,不过是别无选择的苦涩自嘲。
这让人想起多年前丁院士那句振聋发聩的追问,

其背后关乎的,是最根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最后我想说,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对故乡最深的回忆莫过于那缕炊烟。
我家门口对出去是一片田垄,再远一些是一座小山,山脚下住着几户人家。
每到深秋季节,几户人家袅袅的炊烟会汇聚成一条薄纱似的丝带,横亘在小山的腰间。
用鼻子用力一吸,那种混杂着泥土和烧秸秆的气味,我一直觉得那就是家乡的味道。
老家的地锅灶台,是用土和砖垒成的,上面架着一口大铁锅。
母亲在灶前添柴烧火,木桶里蒸出的米饭,混着柴火的香气,至今难忘。
最期待的,是寒冬时节,在灶膛的余烬里埋上几个红薯。那种焦香甜蜜,是童年最盛大的美味。
小时候的我总是很心急,为了能快点吃到烤红薯,总会忍不住用火钳去捅炉膛里的火,以为捅得越旺,红薯就熟得越快。
结果往往是,火苗被我几下捅得奄奄一息,红薯也成了外焦里生的“夹生饭”。
年幼的我不明白为什么,直到长大了我才明白一个道理:
炉火,是经不起瞎捅的。
这句话放在现实生活中,也可以理解为,
任何一项意图良好的政策,如果只是大刀阔斧地“猛捅”一刀切,而不去理解这炉火背后的经济账、民生账,不体恤烧火人的冷暖。
那么,再旺的火,也可能被一双“好心”的手给捅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