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讲环保必涉及资本主义批判?
为什么讲环保必涉及资本主义批判?
——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及地球的未来

本文摘自香港民间团体左翼21翻译的小册子,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Socialist Workers Party)于2009 年出版的,由 Martin Empson 所著的《Marxism and Ecology---Capitalism,Socialism and the Future of the Planet》,阁下阅后若觉不错,可以多分享给身边关注环保的朋友,谢谢。
译序
踏入二十一世纪,人类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已到了相当严重及临界不可逆转的地步。
经济发展是否必然地跟环境对立 ? 答案是「不一定」。关键是如何发展?為谁发展?是否可持续?虽说不一定跟环保对立,但资本主义下的经济发展,因其特殊的生產组织方式,却是必然地反生态的。资本家常唬吓我们说,不发展经济工人便失业,可是他们所谓的发展都是短视的、不可持续的,只务求用最低成本、最短时间,生產最大利润。他们计算生產成本时,只著重工厂内的成本,从来不关心排出厂外的有毒污水或废气对环境、对工人的危害,而有关代价却要社会及环境共同承担。
以香港為例,一位港大教授曾对香港的空气污染及医疗开支作出评估,指出单是空气污染所造成的额外医疗开支是每年过百亿。愈基层的工友便愈多机会需要户外工作,例如清洁街道或地盘的工人,他们每天至少要在街头吸足八小时废气。试想他们的健康会如何?又由於他们的低收入,他们根本不能负担私人医疗,唯有在公家医院排长龙。但对手停口停、工时长的基层工人来说,有几个可以负担得起排队的时间?因此不是大病起来,他们都不会求医,可这时医疗的成本更高了,而治愈的机会更低了。经济上的不平等,令工人面对环境污染时往往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要阻止环境进一步恶化,的确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也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但纯粹将焦点集中於个人,而不去挑战资本主义社会其利润至上的反生态本质,这样除了捉错用神,客观上更是将问题非政治化。
消费主义问题
消费是资本主义的中流砥柱,在上世纪 20 年代始在西方出现,至今仍支撑著整个资本制度。在一个理想的社会裡,生產应是為了人的需要,而不是為了赚钱。不幸地,商人為了增加销路,层出不穷地、过度地生產不需要的东西。结果不单是浪费能源,更造成大量垃圾。要知道,现时全世界都倚重石化能源。石油一方面是有限的 (技术性地说,石油是可以再生的,不过要能遇到合适的条件,再等上几百万年就可以了,如果人类到时仍存在的话!),另一方面使用它会释出温室气体,加速气候转变。消费主义所引申出来的问题真不少,仍未讨论垃圾问题呢 !
全球气候转变
气候转变不仅仅代表气温上升,还代表著极端气候事件 (extreme weather events) ,例如热浪、大旱、水灾、颶风、暴雪等,在次数及强度上的加剧。而这个预测在大量的数据及分析下,於「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2007 年的报告中,已得到了 2000 多位全球最顶尖科学家的确认。如果稍為留意新闻的都会发现,2010 年在中国及巴基斯坦的水灾是如此地严重和不寻常。而这些极端气候不但造成人命伤亡 ── 2010 年,日本有超过 400 多人热死,而在莫斯科死於热浪的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约 50%,接近万人──它还会导致农作物大规模失收,粮食价格暴涨。因為基层打工仔的收入本来已不高,食物开支佔了基层家庭入息一个相当的比例,粮食价格上涨只会令他们的生活更艰难。
攸关环境公义
此外,这又涉及到环境公义。低收入的人要尽力节省开始,在生活各方面都很节约。可是他们掌握的资源相对少,因此对气候转变的应变力也相对较弱。譬如说面对酷热天气,他们未必付担得起享受冷气,也未必可以减少户外劳动。富裕的人因為花费得起,对他们来说就不成问题,更有条件在各方面浪费资源。因此出现一个怪现象:在气候转变过程中,排放温室气体最少的一群人,他们的生活要比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一群人面对更多负面影响。
要阻止地球生态的进一步恶化,我们有需要指出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可惜这方面的讨论在香港几乎近於绝跡。有见及此,我们将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於 2009 年出版的,由 Martin Empson 所著的 Marxism and Ecology---Capitalism,Socialism and the Future of the Planet 小册子翻译成中文,希望藉此推动对有关议题的讨论,亦算是左翼分析常识化工作的一部份。為了让小册子更有趣味,在原文的基础上,我们特地撰写了一些人物介绍和本地议题的小格子。
最后,我们特别鸣谢 Martin Empson 给予我们翻译这个小册子的机会,还要感谢吴思敏及梁锡麟两位友好协助搜集资料及给予宝贵的意见。
前言
人类正面对前所未见的环境危机,其核心是气候转变。在大气层中的一些气体(如二氧化碳)有储热作用,会做成「温室效应」,要是缺少了它,生命将无法在地球出现。可是由於燃烧石化原料(如煤、石油及天然气)的关系,我们大量地向大气释放温室气体。大气的组成被改变,於是储热效果倍增,导致了地球暖化。这个过程已為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
气候记者弗雷德.皮尔斯(Fred Pearce)曾说:「如果你想知道气候转变第一阶段的发展,你只需要留意 1998 年之后的情况。」1998 年是二十世纪最热的一年,是「天气异常地疯狂」的一年,全球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為此吃尽苦头。
它為新几内亚带来了百年一遇的超级大旱,数以千计的人因此饿死。同时,在巴西、印尼、秘鲁、坦桑尼亚、佛罗里达州、萨丁尼亚岛发生的森林大火摧毁成千上万英亩的土地。西藏碰上了五十年一遇的大雪,数百人丧生。秘鲁的水灾让一百万人无家可归。魁北克及新英格兰的暴风雪,让 30 人死亡,数千人在停电中渡过了数星期。咖啡及棉花失收;水温变暖使太平洋的鱼获大减及珊瑚礁死亡。[1]
这只是开始。随著世界变得越来越热,环境及人类的大灾难将会越演越烈。1.5 度的气温上升,足以令额外 4 亿人面对缺水,5 百万人面对饥饿。印度洋的珊瑚礁将会灭绝。全球 18% 的植物和动物将会绝种。不幸地,这些事件都将无可避免,因為温室气体的排放已发生。据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每年有 15 万人因為气候转变而死亡。
随著气温不断上升,情况将会不断恶化。当地球大气层储存的能量越来越多,天气将会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有研究估计,颶风的强度及次数都会增加。海平面将激升,迫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放弃家园。数百万依赖饮用冰川融雪水的人,将面对水源乾涸。為保障水的供应,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将不断漫延。像疟疾等一类疾病将出现在以前从不受影响的地方。
可是气候转变并非一个稳定、逐渐的过程,情况不会随著恶化而逐渐变差。地球暖化所牵引出的一系列自然过程,将会使温室效应恶化。例如西伯利亚的冻土自上一次冰河期起已将数百万吨的温室气体锁住。可是我们看见这些冻土开始融化,释放出温室气体。覆盖地球两极的冰雪,就好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将部分太阳的能量反射回太空。但随著冰雪融化,更多的能量被储存在大气中,使地球进一步暖化,这又促成了更多的融冰。科学家们称这些过程為「反馈机制」。
為了避免气候的「临界点」──当全球暖化加速到一个不受控制的地步,威胁到人类,以至地球上其他生物的存亡──当务之急是减少温室气体的进一步排放。
可是,气候转变只是我们面对的更广泛的环境危机中,一个最尖锐的表现。世上几乎再没有一个未受人类社会触碰过的生态空间。由最深海的污染,到最高山上的冰雪融化,所有能够在地球上想像得到的生态系统,都已经被损害或摧毁。
每年有一百万或以上公顷的亚马逊雨林被砍伐及烧毁,虽然它对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人类製造的垃圾在大自然充斥,导致现时太平洋中的塑胶垃圾超过了浮游动物(牠们对海洋生命十分重要)数量的六倍。
环境危机不断恶化的征兆,促使人类重新思考其自身跟外在世界的关系。对一些人来说,这关乎个人生活对环境的影响。鼓励人的生活要跟自然更和谐,透过循环再造及再用,以及限制人类活动来减少对地球的破坏。可是个人的作用相对於跨国企业及政府政策所带来的破坏,根本是微不足道。我们需要探讨的是整个社会及其赖以為生的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
目前為止,主流政党、工会、非政府组织及政府,都在提倡通过现存社会的改革来解决危机。因此他们都有差不多的主张──寻找一些技术或经济的机制,好让我们继续以往的生活模式,当中或会有小修小补,但实质的改变相当少。有关问题被当成具体的操作问题,而非社会的本质问题。
在 2006 年出版的《史登报告:气候转变下的经济》(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Climate Change),便很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此报告受英国政府委託完成,是同类型研究中最大型及广泛的。对史登来说「气候转变為经济带来独特的挑战,是前所未见的,最大规模及最广泛的市场失败」。[3]
史登是前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及副主席,虽然被部份环保运动中人寄予期望,他却并不打算放弃其自由市场的主张。相反地,他认為市场机制仍未被赋予足够的自由力量来处理气候转变。史登方案的中心思想是自由市场机制下的「碳交易」(Carbon Trading) 。我们已知此方案对减少排放毫无帮助,但却可以為相关企业赚取巨大利润。[4]
社会主义者认為当今所见的环境破坏,其实是我们身处的独特政治及经济系统的结果 ──资本主义。正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他的毕生战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对资本主义最大的批评:资本主义是不可持续的。他们将一生都奉献於為社会带来革命性转化的斗争中,创建一个基於需要而非利润的新世界,在那裡自然世界除了会被改动和利用,同时也会受到保护和珍惜。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人类社会不能跟自然世界分割──资本主义除了剥削和毁灭人类,它同时使环境受到蹂躪。这种思想像线一样穿透在他们的书本及文章中。虽然 150 年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绝对无法预想到今天如此严峻的环境危机,但他们的思想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以了解资本主义是如何威胁人类社会的存在。
可惜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於了解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关系方面所作的贡献,已很大程度上被有心拯救地球的人遗忘及抛弃。部份是因為那些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名进行统治的人,尤其是前苏联,所犯下的罪行──包括对环境犯下的罪行。另一个原因是很多环保份子都希望在现存的社会框架下拯救世界,而不愿相信有革命性转变的需要。
我将在这小册子探讨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解释在不同的歷史阶段中,人类社会与环境的关系,以及為何资本主义对环境具如此破坏性。还有,為何要那么迫切地将马克思主义理念重新置於辩论的核心──究竟怎样的社会才能将我们从生态破坏中解救出来。
1Fred Pearce, The Last Generation: How Nature will Take her Revenge for Climate Change (Eden Project Books, 2006), p39.
2George Monbiot, Heat: How to Stop the Planet Burning (Penguin, 2006), pp9, 15.
3Nicolas Stern, Stern Review, Executive Summary (2006), p1.
4作為其中一个例子 , Larry Lohman (ed) Carbon Trading: A Critical Conversation on Climate Change, Privatization and Power (What Next Project& The Corner House, September 2006).
第一章 人类及自然世界
从一开始,马克思便提出了一个意味深远,却常常遭人忽视的基本论点 ──没有一个人类社会能够独立存在於其身处的自然世界:「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5]
自古以来,人类便会塑造工具,并在自然界中运用它们以满足基本需要。人类学家弗朗西斯.普赖尔(Francis Pryor) 告诉我们,人类早在 650,000 年以前,在后来成為了英伦三岛的地方,就会製造火石器及手斧,跟非洲发现的、有一百万年历史的工具类似。这些工具被大量生產,用以打猎来取得食物,用以砍木来製造藏身处和燃料,以及用以整理毛皮来生產衣服。[6]
如恩格斯所言:「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於自然界、存在於自然界的。」 [7]
一个社会如何去组织生產是受到两个不同的因素所限。亚历.卡利尼科斯(AlexCallinicos) 很有力地总结了马克思的论点:
生產有物质和社会这两个面向。首先,男人和女人通过行动对大自然进行改造,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意味著某程度的生產组织,以及拥有适当的工具等等。其次,生產是一个社会过程,当中人们合作生產他们需要的东西。这必然地牵涉到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至关重要的是,这关系牵涉到对生產过程及產品销售的控制。马克思称前者為物质面向,亦即是生產力 (the forces of production) ,而后者為社会面向,亦即是生產关系(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8]
过去大部份的人类社会都以小社区的形式存在,生產只够维持生存的最低需要,很少剩余。在这些马克思称之為「原始共產主义」的社会中,生產工具為大眾共同掌握。可是当社会有能力作剩餘生產,容许部份人的生活免於终日劳苦,少数人便控制了生產工具。
社会被分割成不同阶级,统治阶级剥削那些直接地生產生活所需的人。由於统治者要靠特定的方法把生產组织起来,以获得其社会地位,此利益驱使他们要维持社会现状。他们抗拒一切可能令生產关系改变或削弱他们地位的转变。历史上充斥著各种因不愿意,或无法改变社会组织方法,而终导致社会崩溃的例子。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人类社会无可避免地跟自然世界连在一起,但亦对这世界作出影响。由於人类对四周环境的影响,跟其特定的生產组织方法相关,因此其对自然世界作出改变的程度,在历史上也不断转变。
尽管只是使用古代的工具,人类已经可以永久地改变他们四周的环境。举例说,在 12,000 年前的一次气候转变中,那些被人类学家称為克洛维斯人(Clovis Hunters)的族群很有可能帮助促成了长毛猛獁象的绝种。[9]
可是若要跟后来人类社会对大自然造成的改变相比,这些都显得毫不重要。配备了石斧及木製长矛的古代人类,或许可以促使本身已因自然环境改变而弱化的物种灭亡,但他们不可能大规模地,从根本上改变生态系统的平衡。
后来的人类社会却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為他们的社会组织方法,给予了他们自由来运用各类资源於大规模的项目中和生產出更大威力的工具。不少社会都会将树林清除,以腾出耕地或获取原材料。在早期的社会,只有很少的地方需要清除,因此过了一段时间便会自然地回复原貌。
更具生產力的文明世界可令这些变化成为永久。古希腊人为了开垦耕地而砍伐树林,造成水土流失,终导致他们的港口及海湾撕裂。由于人口膨胀,欧洲大部份的森林在中世纪时代已被清除──到 15 世纪时,此过程更迅速加剧,由於欧洲列强都纷纷建设大型的木製船队以技拓展他们的殖民野心。及至 18 世纪,欧洲的林木已相当稀少,而要跑到美国来砍伐树林以提供建造奴隶交易用船支的材料。[10]
可是资本主义的降临创造了一个新的、而且很有可能是更危险的处境。在过去的一些文明世界裡,人类社会对其四周的改变,再加上气候及自然环境不时的转变,都会引致这些社会的灭亡。在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 的《崩溃》(Collapse)一书中,他说明了不同的文明世界──例如南美州的玛雅人、复活岛的岛民,以及格林兰岛的维京人 ──的消失是源於他们无法适应其赖以為生的自然世界的转变。可是在这些例子中,消失的只是一地的社会,除了一些遗址让人类学家考究外,他们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
在资本主义下,我们的文明对自然世界的改变已威胁到整个生态系统。今时今日,气候转变已令人类文明的持续存在成為疑问。
5恩格斯在马克思葬礼上的发言(1883 年)总结了马克思的观点。全文见http://www.marxits.org/achive/marx/works/1883/death/burial. htm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76 页。
6Francis Pryor, Britain and Ireland Before the Romans (Harper Perennial, 2004), p18.
7Frederick Engels, “The Part Played by Labour in the Transition from Ape to Man”, in The Dialectics of Nature (Lawrence and Wishart, 1946), p292.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73—386 页。
8Alex Callinicos, The Revolutionary Ideas of Karl Marx (Bookmarks, 1983), p83-4.
9Steven Mithen, After the Ice: A Global Human History, 20,000-5000BC (Phoenix, 2004), p246-257.
10Marcus Rediker, The Slave Ship: A Human History (John Murray, 2008), p53.
第一章 人类及自然世界香港废物处理
特区政府一直扬言,香港处理垃圾的做法不是堆填,就是焚化。虽然堆填或焚化都是外国处理垃圾的方法,但这并不是处理垃圾的唯一办法。其实台湾早在十年前已经走出了焚化、堆填以外的第三条道路。
依据台湾的经验,政策上推行生產者责任制,要求生產商补助回收所生產的商品(废物);另一方面推行垃圾分类政策,推动市民去进行垃圾分类。具体操作上实施垃圾收费计划,鼓励市民减少產物垃圾;此外,政府亦鼓励地方组织卫生纠察队,防范有人非法弃置垃圾,被捉拿者的罚款亦会全数归入地方民用基金中,藉此推动市民参与。台湾这些政策及做法的推行,单是台北市家用户垃圾弃置量就已经由 2000 年的每人每日 1.12 公斤,减至 0.39 公斤。回收率亦由以往的2.4%,增加至见前的 44%。市民的垃圾费负担亦由 144 元新台币减至 51 元新台币,成效十分显著。
「将可回收的资源尽可能回收」是台湾处理垃圾的成功之处,香港亦应以此原则去处理本地垃圾。虽然香港拥有回收行业,2009 年回收率亦 达到 49%(这亦是环境局引以為傲的成效)。但这并不反映垃圾得到有效的处理。其症结问题在於废物回收的多寡,完全取决於市场的力量,亦即「赚到钱的就回收,赚唔到的就唔收」。其实欧盟、韩国及台湾等 40 多个地区及国家,早已认识到以资本市场逻辑去运作回收业的盲点,因此早在 1990 年代提出处理垃圾问题就必须要从源头——生產者著手。并推行「生產者责任制」,立法要求生產者承担產品售后的回收成本,特别是没有回收价值的物料。
生產者不单要负责產品的生產过程安全及卫生,更应负上產品售后对环境的影响的责任。否则,眼裡只有图利的商人就会不断使用对环境有害的物料,或製造过度包装的產品,最终受害的只有我们自己。
当然生產者责任制并非万灵丹,因為在资本主义消费模式的生產过程下,废物或垃圾在生產环节就已经製造或產生了。但有当然比没有好,因為假如没有的话,就等於任由商人将环境污染的代价外在化,有的话,至少可以迫令生產商要对环境负一定责任。
第二章 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最初由欧洲的西面冒起,继而迅速席卷全世界。新的社会组织方法需要彻底地推倒旧的社会组织。资本主义出现以前,欧洲社会的主流模式是封建主义。富有的地主剥削佔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大部份的农民都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中世纪时代无数的战争背后的动因,都源自土地的控制权,地主们不是為了保卫他们自己的土地,就是为了掠夺其他人的土地而战。
处于封建主义核心的剥削是绝对地残暴的──农民的生活跟田园诗般的乡村生活相去甚远。他们的寿命很短,而且很少有机会离开他们的出生地附近的范围。生活中充满了艰苦的劳作,而农民大部份的劳动成果都被地主夺去。可是,地主的剥削绝大部份只为满足其个人消费。
因此,对农奴的剥削受限于地主及其随员的所需。尽管他们的消费很可能很挥霍或炫耀,但在封建社会的核心,这种剥削被有效地限制于地主能吃得下多少。
在资本主义下,事情却有著根本性的差异。如今大部份的人并不靠土地為生,而且跟中世纪的农奴不同,资本主义下的工人并没有被束缚在他们的工作或土地上。工人完成某项工作后,老板会支付他们工资,而不是给予他们一部份由他们负责生產的东西。工人需要出售他们的工作能力──他们的劳动力──以换取生存所需。
最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下,对工人进行剥削的中心动因并非為了满足统治阶层或个别老板的消费(尽管有关的问题绝对甚少被忽略),而是基於无日无之的为了利润而追逐利润(pursuit of profit for the sake of profit) 。用马克思的讲法:「累积,累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Accumulate, accumulate!That is Moses and the prophets!”) [11]
生產是由不同的、互相竞争的公司组成。每一间公司都被要超越其他竞争对手的需求牵引著,时刻活在被其他对手超越的恐惧中。没有一个资本家可以承受原地踏步。他们需要不断地找出新的方法来增加对劳动力的剥削──他们利润的首要来源。在任何一个理性的社会,引进新机械的结果应是生活条件的改善及工作日数的减少,可是在资本主义下,所有的改进都只為了扩大剥削以超越竞争对手。
财富的累积只单纯為了累积本身,而不是為了满足人的需要,换言之,资本主义跟大自然的关系与从前的社会相比已截然不同。当马克思及恩格斯写到有关资本主义如何剥削大自然,他们清楚地指出:
「这是第一次大自然纯粹地成為了人类的客体,成了纯粹的实用问题,不再被视为自身的一种力量。而对大自然的一些自主定律的理论性发现,只不过是把大自然从属於人类需要的一种花招,不论是作为一种消费对象,或是作為一种生產工具。」 [12]
在资本主义下,自然环境只是用来剥削以获得利润的东西,或是用来放置这个制度生產出的无用副產品的垃圾场。看看所有的东西,从核废料到污水是如何便投进大海,或是温室气体是如何被泵进大气中但森林却同时被砍光,以致于良田如何被短线的农业操作弄得不能再耕。在利润追逐中,只有短暂的考虑才最重要。正如恩格斯所言:
「当一个资本家为著直接的利润去进行生產和交换时,他只能首先注意到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一个厂主和商人在卖出他所製造的或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心满意足,不再去关心以后商品和买主的情形怎样了。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如此。当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炭足够被当作咖啡树的肥料用一个世代,获取最高利润的时候,他们怎麼会关心到,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呢?」 [13]
可是,独立的公司或工业认为是合理的一些短期的行动,经常对整个地球有著不合理的长远后果。例如持续地燃烧石油可令跨国的石油公司利润滚滚而来,可是长远来说其副產品却以温室气体的形式加速气候转变。虽然以最快的速度去砍伐森林会比维持一个可持续的森林赚更多利润,可是长远的后果可以是灾难性的。
任何一间公司若希望避免有关后果,例如以增加开支来变得更有道德,或是投资更多在可持续发展的措施上,它将会处於一个不利位置,因為其竞争对手可以更低廉的价格来生產货物或提供服务,而且除非他们也准备节省开支否则将会面临破產。
人类一直以来都生產废物,但其规模在资本主义下却激增。希瑟.罗杰斯(Heather Rogers)指出:「过去三十年美国的垃圾產出增长了两倍。今天有接近 80% 的美国產品只经过一 次的使用便遭抛弃。」[14]
事实上,正正是资本主义创造出垃圾问题。从前要不就是因為太穷因此人们只能重覆使用仅有的少数物品,要不就是因為他们拥有的物品都是设计成可被重覆使用的。当商品能够被重覆使用,它们便不会被再次购入,因此公司发明了即弃的產品,并将它们假装成方便,目的是為了出售更多產品及赚更多钱。其逻辑结论便是预先设定的废弃──商品不是过了几年便无法运作,就是它已变得不合潮流。
在 1920 年代,重覆购买產品的行為开始被推销成一种「确认生命的行动」。根据当时一位市场顾问所讲:
「通过购买更多更新奇刺激的產品及服务来实行进步性的废弃,藉此作為登临人类更大满足感的阶梯,这几乎是每个美国人的追求目标。」 [15]
1950 年代汽车工业把这个当成逻辑结论──「每年更换汽车款式增加了我们的销量」,一个福特的业务主管说。这鼓励了车主尽可能经常地更换他们的汽车。[16]
可是,并不是单纯地由於资本主义需要出售更多產品所以浪费资源。由於公司之间要互相竞争,所以在生產上没有一个全面的逻辑。换言之,生產是非理性和没有计划的,并在各层面造成浪费──一方面是过度生產,另一方面是浪费资源。工人及工厂大量生產不需要或是对有需要的人来说负担不起的產品。整个工业吸引了大量的物资、能源及人力,却对社会无甚助益。
经济学者迈克尔.基德伦(Michael Kidron) 曾估计,在 1970 年全年美国有 60% 的生產可以被归类為浪费 [17] ──资源被分配到武器工业、广告或是供富人消费的奢侈品。浪费的数量是惊人地庞大──全球在 2006 年的军事开支是 1.2 万亿美元,同年用於广告的整体开支是 3850 亿美元。相对地,2005 年用於爱滋病研究的预算却只有 85 亿美元。
在他伟大的著作《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如何浪费他称之為「消费排泄物」,意指「人的自然排泄物和破衣布碎等等」。这些都「对农业来说最為重要」:
「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例如,在伦敦,450 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来污染泰晤士河。」[18]
我们的城市设计正正凸显了资本主义造成的浪费及环境破坏──人们从老远的地方跑来上班、上学,这需要燃料大量原材料才能做到。三分之二由发电厂生產出来的电被浪费掉,因為那些电都是由巨形的中央发电厂生產的,距离需要供电的地方非常远。[19]
对主流的经济学来说,大自然并不在计算之内。正如马克思生态学家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 所指出:「由工厂引起的空气污染并没有被视為工厂以内的生產成本,而是被当作為要大自然及社会承担的外在成本。」 [20]
然而,这不代表我们应该反对经济发展因為它不乎合地球利益。那些生活在世界上最贫穷地区的人极度需要进一步的经济发展,但问题是我们需要怎样的增长及发展。在历史上,福斯特形容「全球环境一直在补助财富累积…因此过去五百年的历史是不可持续发展的歷史。」[21] 没有理由解释為何发展就是要跟随已发展国家破坏性的、不可持续的老路。
一些更有远见的资本家亦看出这问题。企业及政府的领导明白他们要应付环境危机。可是对於整个制度及长期来说是合理的东西,不一定对制度内互相竞争的不同组成份子来说是合理的。看看第一个為对付气候转变而產生的国际协定──京都条约。它要求已工业化的国家承诺在 2012 年之前削减 5% 的排放。即使是那么不具野心的目标,对美国来说都是太高要求,因此她以影响经济為由,拒绝确认条约。
资本主义短视的本质、制度核心性的竞争以及因此出现的无效率,加上将有关成本外化转嫁到自然世界,这些都意味著资本主义长远只会造就不可持续的社会。
11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One (Penguin, 1990), p74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86 页。
12Karl Marx, Grundrisse (Penguin, 1973), p41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 46 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93 页。。
13Frederick Engels, “The Part Played by Labour in the Transition from Ape to Man”, in The Dialectics of Nature (Lawrence & Wishart,1946), p295.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386页。
14Heather Rogers, “Garbage Capitalism’s Green Commerce”, Socialist Register (Merlin Press, 2007), p231.
15Heather Rogers, Gone Tomorrow: The Hidden Life of Garbage (The New Press, 2005), p113.
16同上 ,p114.
17Michael Kidron, “Waste: US 1970”, in Capitalism and Theory (Pluto Press, 1974).
18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Three (Progress Publishers, 1978), p10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19Greenpeace, “Decentralizing Power: An Energy Revolu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July 2005.
20John Bellamy Foster, The Vulnerable Planet (Monthly Review, 1999), p123.
21John Bellamy Foste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hat?” in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s, 2002), p80.
绿色就业二三事
现时全世界很多人都寄望以绿色就业来缓解气候变化,可是却不自觉地被其先进和清洁的外表所蒙蔽,而忘记这个新轻工业背后的一些环保、职业安全及公义问题。资源回收业是其中一个危机四伏的『绿色』行业,尤其针对有毒和致癌重金属的处理,包括铅、鎘和砷等。其次,回收业很多时只是老人家拾荒劳动赚取生活费的唯一途径,而且在金融危机下,很多资源的价格下降,也使废物回收变得无利可图,进一步压抑他们的收入,使废物回收行业难以生存。香港泥头车司机协会曾指出了玻璃回收的潜力,可是由於欠缺「市场价值」,被政府和业界都忽视了。
此外,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并没有因為绿色就业而恢复,相反情况依旧。在英国怀特岛发生的维斯塔斯风机厂工潮便是一个明显例子,不久之前隶属丹麦维斯塔斯公司的怀特岛厂方决定关厂,将生產线转移到更具发展潜力的国家。可是,关厂的决定并没有得到工人的集体同意,也没有讨论过关厂以外的可能性(例如卖盘),而工人在过程中一直备受厂方的欺压,态度恶劣。这次事件让英国以至欧洲其他地区的工人和环保人士连结起来,一方面要求恢复生產,另一方面呼吁保障当地人的就业。可见解决气候危机需要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主义。
(此文撮写自李育成《绿色就业是工人回应环境危机的最佳方案吗?》,原文见於劳工世界网:http:// www.worldlabour.org/chi/node/279)
第三章 马克思与恩格斯
以社会主义之名统治的苏联和东欧集团可怕的环境纪录,扭曲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生态学讨论的贡献。但其实,这些政权与两人理想中社会应「按能付出、按须给予」的管治原则关系甚微。
许多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我们现在称為生态学的想法,近年都被福斯特(John BellamyFoster)等作者重新提出和发展,他们应被视為真正属於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部分。
我们已看到人类和他们周遭自然世界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中心位置。但是,对於这种与环境的关系如何在资本主义下塑造社会生活,马克思发展了一套更為微妙的理解。要明白这套想法,我们需要先理解另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异化的理论。
工业和科技的成就创造了我们的祖先无法想像的机遇,它们的承诺却从未被实现。现代化农业具有养活数以十亿人的潜力,世界接近六分之一的人口却依旧营养不良。我们有能力经常把太空人和人造卫星发射到太空,却任由十亿人民活在每天少於一美元的贫困生活之中。如马克思所说:
「劳动為富人生產了奇跡般的东西,但是為工人生產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產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產了愚钝和痴呆。」 [22]
虽然有了支配自然世界的能力,社会却越发变得危险和不稳定。人类劳动的產物似乎是支配而不是解放了我们。马克思在 1856 年如此归纳这个矛盾:
「一方面產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像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徵象,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於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為代价换来的。」 [23]
马克思把这个过程称為异化──在资本主义下,我们作為人类的本质,亦即是人类共同努力以改变自然世界的能力被夺去的过程。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失去控制,我们劳动的成果变作了我们的敌对力量。
马克思在《1844 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了异化的四个面向:把劳动者从 (1) 他/她的劳动產品,(2) 劳动过程本身,(3) 人类本性,和 (4) 与其他劳动者之间割裂起来。
劳动者与他们提供的產品和服务割离,因為工作的成果為他人──资本家,所控制和拥有。马克思总结了劳动者生產的物品如何最终支配了他们的生命:
「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於他而属於对象了。因此,这个活动越多,工人就越丧失对象。凡是成為他的劳动的產品的东西,就不再是他自身的东西。因此,这个產品越多,他自身的东西就越少。工人在他的產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著他的劳动成為对象,成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著他的劳动作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著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24]
接下来马克思理论的第二部分,是劳动者与劳工过程本身的割裂。我们无权决定我们怎样工作或工作条件為何。工作的过程不单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中,更是在与劳动者利益敌对的人──老板和管理层手中。他们一切的利益都在於令我们更勤劳地工作,支取更少工资而工作更久。
现代的生產线强化了这个过程,因為他们的工作只属於更庞大的过程的一小部分,使得他们与他们劳动的產品进一步分离。过去有技术的工匠会从头到尾製成一件產品,在现代工厂劳动者则只会不断地重覆同一过程以生產產品的一小部分。劳动者只是机器的另一个小齿轮。
马克思指出的第三点是我们人类的本质--我们从事社会劳动的能力--已被夺去。工作从创造性的行為变成了它的相反。
最后,我们之间亦互相割离。我们為工作、為加薪、為升职而互相竞争。我们互相敌对,变得更易被分而治之。
更甚者,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被商品买卖所支配。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社会组织的基础在於它如何提供生活基本所需,记得吗?在资本主义之下,数以千计的人牵涉在我们的衣、食、住、行的產品之中。但我们却和他们完全分离,只知道购买他们劳动得来的產品。我们不把其他的人类视為同类,而是把他们视作生產过程的一部分──他们成了或强或弱於我们的竞争者。
因此结论是,异化是劳动者与他们自己的劳动,以及劳动在转化自然的角色之间的割离。
在资本主义下,劳动者被割离於自然世界,然而我们的社会却是建基于自然。
马克思在《1844 经济学哲学手稿》如是说:
「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於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5]
后来,马克思以人类和自然间的「新陈代谢」来命名这个观点,以「给予这个根本的关系一个更坚实和科学的名称,展示人类与自然之间由人类劳动引起的复杂、动态的交流」。[26]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7]
马克思是从十九世纪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环境问题中发展出这观点的,那就是土壤养份的枯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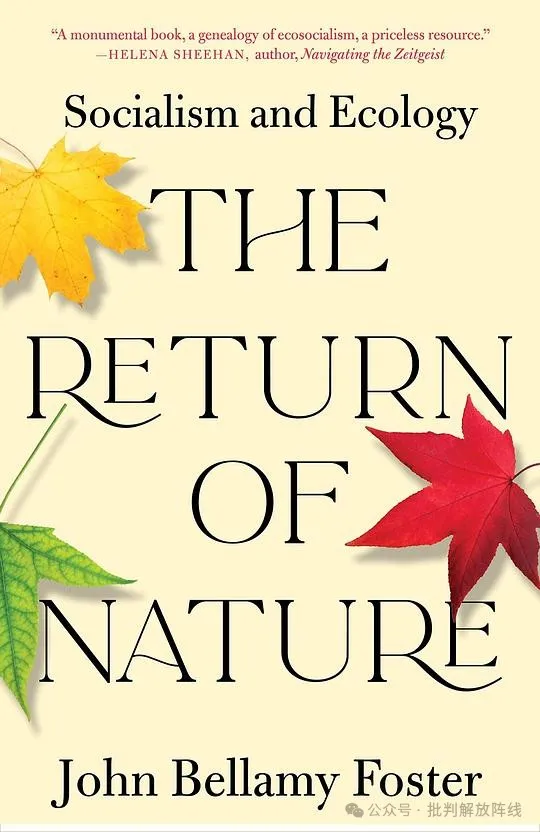
在欧洲和北美等当时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逾加密集的农业引致了「土壤过劳」,使肥料的需求大大增加──到十九世纪中期,海鸟粪便的贸易价值庞大,欧洲的农民甚至不顾一切地「搜掠拿破仑战争的战场……搜集散落的骸骨」。[28]
当时能够製造人工肥料的化工业仍未发展到足以帮助全球农业需求的规模,因此新肥料来源的需求带来了「鸟粪帝国时代」,各国争相吞併海鸟数量丰富的小岛。
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首度提出了农业减少土壤肥力成因的现代理解,即植物生长时从土地中吸去氮和钾等养份。他从此发展出了对于农业系统地掠夺土地养份的批评──土地的养份「年复一年地以农產品的方式被取走」。
李比希固然希望使用天然或人工肥料使过劳的土地复原,他亦相信农业需要一个更理性的形式。如福斯特所言:
「李比希指──基於泰晤士河的状况──城市被人畜排泄物所污染的问题与自然土壤失去肥沃的问题是相关的,把养份带回土地的有机循环是理性的「城市-农业系统」的必要部份。」[29]
马克思从李比希和其他人的思想发展了一套对资本主义农业方法的深入批判。人口愈加集中於大型都市是问题的中心--在乡郊產出的食物被带到城镇,而废物被丢弃到河流和海洋,养份则从农业系统中流失。
马克思明白,假如农业以理性的方式组织,土壤的改良是可能的,但他亦明白「资本主义的生產……破坏著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他更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个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30]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的分析令他相信,真正可持续的农业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下存在:
「慎重而理性地把土地视為社区的永久财產是人类世代存续和繁衍必不可少的条件。」[31]
因此在资本主义下人与自然之间有「代谢断裂」。於马克思看来,这个分裂只可在社会组织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时才可修补。
「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產者,将合理地调解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於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以最小的能量消耗,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32]
换言之,资本主义為更能持续发展的未来奠下了基石,但唯有在另一种修补了人和自然之间裂痕的社会,人们才有进一步发展的自由,而不受资本主义所限制。
22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8-159 页
23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 1856 年 4 月 14 日在伦敦发表》,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3-5 页。
24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2-53 页。
25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6-57 页。
26John Bellamy Foster, Marx’s Ecology, Monthly Review, 2000 , p158.
2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07-208 页。
28John Bellamy Foster, “Liebig, Marx and the Depletion of Soil Fertality” in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p156.
29同上 , p158。
30同上 , p161。中译文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79-580 页。
31同上 , p161。
32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28-929 页。
第四章 马克思,马尔萨斯和人口过剩的迷思
世界人口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参与过最重大的论争之一,且它与今日人类与地球的未来的讨论仍然相关。
今天,人口水平的论争与可持续性的讨论密不可分。环保分子暨新工党政府主要顾问乔纳森.波里特(Jonathan Porritt),是最佳人口信托(Optimum Population Trust,OPT)的赞助人。该信託要求英国的人口减少至三千万,即 1880 年代时的水平。波里特形容,「人口增长,加上经济增长,把世界置于可怕的压力之下。」人口过剩是影响政府最高层的想法。英国移民局局长菲尔.乌拉斯(Phil Woolas)相信,「人口增长下不可能有可持续发展」。
人口过剩对於不少环保分子来说都是「常识性」的主张。大卫.阿滕伯勒(DavidAttenborough)和詹姆斯.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都是 OPT 的赞助人。绿党政策文件指「稳定或缓慢地减少的人口亦是可持续而平等的社会的必要条件」。
把人口水平问题归咎於贫困者最终将会转移对於社会和环境问题真正原因的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深明於此,故竭力挑战这种常识的想法。
1798 年,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Rev. Thomas Robert Malthus)出版了他提出人口增长必然会超出食物资源的一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他的名字成為了以下主张的代名词:世界人口已经或将会过剩,地球只有有限的食物和自然资源,而这不能支撑不断增长的人口。在全球暖化的年代,有些人把这主张扩展到人口越多,温室气体排放也会越多。
与现代的理解不同,马尔萨斯极力避免使用「人口过剩」[33] 一词。对他而言,这并不是论争的重点。
马尔萨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写下他的文章。他在参与的是一场平等社会是否可能的论战。
具体来说,他试图反驳基进作家暨思想家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的想法:
「压迫的精神、奴役的精神和欺骗的精神,是现存资產制度的直接產物……在一个人们活在丰饶之中,大家共享自然的礼品的社会,这些情绪必然消逝。」[34]
马尔萨斯反对这个基于物质关系之外的社会的观点,他相信由於人口增长的唯一限制只有堕落(在他的年代,普遍相信滥交会减少生育)和苦难(瘟疫、疾病、饥荒),平等的社会是不可能的。
「人不能活在丰饶之中。人与人不能共享自然的礼物。没有确定的资產管理制度,每个人都会被迫以武力守护仅有的储备。自私将会大获全胜。」
于马尔萨斯而言,他相信人类自私的本性使私有财產制度成為拘束人口的必要制度── 一个更為平等的社会只会带来苦难,因此必须避免。这样的社会必会失败,因為人们会不停生育直至粮食不足,大规模的饥荒将引致社会崩溃。
马尔萨斯的思想中心是对于贫穷、劳动的人们可鄙的态度。马克思形容这是马尔萨斯作品中「根本的恶意」。但他和恩格斯也指出了马尔萨斯的思想不科学。并没有证据证明马尔萨斯的关键命题,即人口在不受约束下会以几何级数增长(即 1,2,4,8,16……),最终追过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1,2,3,4,5)的粮食生產。[35]
马尔萨斯的主张指责贫苦大眾造的苦难是咎由自取。因此他强调不应有国家贫穷资助。说到底,如果人口超越粮食供应是自然定律,尝试喂饱饥饿的人也毫无意义。很少今天使用马尔萨斯的论据的人会接受他对于贫穷者没有能力作道德约束的信念。但在他 1803 年版的文章,马尔萨斯更进一步说:
「对於非婚生儿童……无论如何都不应给予他们任何的教区福利……相对而言,他们是全无社会价值的,其他人立即可以取代他们的位置……」[36]
稍后他续写道:
「自而然之,我们不能以任何方式支援贫穷者,而不令致他们生育更多儿女,為人类带来更多问题。」[37]
马尔萨斯的这种态度令他相信慈善本身是一个问题,因為它只是令贫困者继续存活在贫穷之中。对於 1817 年爱尔兰饥荒,他主张不应对飢饿有任何的济助,而是把贫民从土地强迁到城市。[38]
这种情绪使很多人批评马尔萨斯。基进作者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如此评论马尔萨斯:「在我一生人中曾厌恶过许多人,但从未如厌恶你一般。」但即使马尔萨斯的想法有这些理论的限制,它们很快就成為了教条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热心地回应马尔萨斯的说法,他们的著作亦不时引述马尔萨斯的文章,并承认他的思想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中有重要的角色。马克思在 1865 年如此写道:
「以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原理》(Principles of Population)為例。在出第一版时,它不过是一种「耸人听闻的小册子」。此外,从头到尾都是剽窃。然而,这本诋毁人类的诽谤书曾造成了多麼大的冲击呵!」[39]
恩格斯如此总结马尔萨斯的主张:
「地球上永远有过剩人口,所以永远充满著穷困、匮乏和不道德;世界上的人数过多,这是人类的宿命,是人类的永恒的命运,因此,人们就分為不同的阶级,有些比较富裕、受过教育和有道德,而另一些则比较穷困、不幸、愚昧和不道德。」 [40]
难怪马尔萨斯的著作成為了「真正英格兰资產阶级的宠儿理论(pet theory)[i] ……因為它是他们最华丽的藉口。」[41]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细仔地把握了马尔萨斯的基本主张。他们指出马尔萨斯如何自相矛盾,承认有些情况粮食生產的提升追上了人口的增长。他们也指出科学、生產程序和农业技术的进步大幅地增加了粮食可能被生產的数量。
恩格斯从一个与主流评论彻底不同的观点切入饥饿的问题。假如食物不够,「为什么生產得太少呢?」他认為:
「并不是因為生產已经达到极限(即使是在今天,在使用现代化的手段的情况下)。不是由於这个原因,而是由於生產的极限并不决定於挨饿的肚子的数目,而决定於有购买力的有支付能力的钱袋的数目。资產阶级社会不希望,也不能希望生產得更多。没有钱的肚子,即不能用来生產利润、因而也没有购买力的劳动,使死亡率不断提高。」[42]
残酷的现实一次又一次地在饥荒时出现。在恩格斯写出上文之前二十多年,马铃薯疫病毁坏了爱尔兰最主要的粮食来源。约一百五十万人死亡,另外一百万人移居海外寻找食物和工作。[43] 在饥荒最严重时,不列颠政府最主要的考虑是饥荒救济不能影响开放市场的食物价格。
数以百万计的人捱饿,食物价格飙升。政府的官方立场是饥荒给予了商人图利的机会。投机者在政府拒绝干预之下赚得了巨款。脱利卫连爵士(Sir Chalres Trevelyan),负责饥荒救济的财政官员,一再拒绝输送食物给灾民,害怕其对私人业务的影响。
这场冲击爱尔兰的灾难并非自然而然。其他国家也受到马铃薯疫病的影响,但并未引起大规模的饥荒。这场灾难是不列颠与爱尔兰人的关系使得他们贫困并依赖於单一农作物,加上政府因為害怕影响商人售卖粮食的利润而拒绝救济所造成。
在 1847 年,大饥荒期间,爱尔兰谷物大丰收。「整个郊野都铺满了收获的谷物,而人们则在饥饿的恐惧中……谷物会被运到国境外出售,以抵偿租金。」在利默里克(Limerick)负责的政府官员写道。
假如当局肯作更多帮助,很多因饥荒而死的人将能存活。英国政府在 1845-1850 年间花了略多于七百万英镑于救济饥荒。这与当局 1830 年代给予西印度奴隶主补偿解放奴隶的二千万镑或是数年后花费在克里米亚战争的七千万镑成了很大的对比。[44]
数以百万计的爱尔兰人死亡和迁移不只是歉收的结果,它是帝国主义和经济政策把利润置於人民之前的后果。
在爱尔兰大饥荒期后每次的饥荒,都有论者主张饥饿是人口过剩的结果。然而这对于1840 年代爱尔兰或之后世界各地的饥荒都不是真的。
在 1970 年代,西非撒哈拉地区发生饥荒。各国中除一国外都生產了足以养活它们人口的粮食。在 1980 年代,非洲撒哈拉以南 31 国受水灾影响,仅有 5 国发生饥荒。[45] 同样问题不在於人口或粮食短缺,而是现有的粮食到不了需要的人手上。今天比 20 年前的粮食供应增加了 15%,但营养不良最严重的地方出口粮食──比如印度,在 1995 年输出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小麦和白米,即使它有超过二亿人口活在饥饿之中。[46]
这与爱尔兰大饥荒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尤其是较富有的国家如何令情况变得更差。联合国饥饿专责小组曾指出,只要发达国家付出国民生產总值的 0.7% 作為援助,便可在 2015 年前把全球饥饿人数减至一半。这些国家亦必须「改革伤害饥饿国家农民的贸易手段,并停止向他们虚弱的市场倾销平价农產品」。[47] 这亦意味著当农作物可生產為养活饥饿人口的粮食时,不应把它们当作高利润的「生物柴油」卖掉。[48]
我们有巨大的潜能產出远多於我们目前生產的食物。根据联合国食物及农业组织 2009 年的报告,全球可作农业用地是现时农地的两倍以上。大部分这些土地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另一份报告,则指出更大的潜力:
「几内亚草原地区,从塞内加尔到南非共六亿公顷的土地,当中四亿公顷适合耕作,而目前只有百分之十正被用作农地。」[49]
马尔萨斯写下他的文章二百年后,世界已变得非常不同。然而他的主张在经济和环境危机威胁地球下,又再度涌现。
指出有足够食物养活全球固然重要,挑战对於人口增长的迷思亦很重要。
全球人口现时约為 67 亿并持续增长,但续长率已大幅下滑。在 1950 年到 2000 年半个世纪,全球人口增长了 140%。但在其后的 50 年,专家估计它只会再增长 50%,而再之后的 50 年则只会增长 11%。随著生活水平提升,以及教育和医疗设备的改进,生育率便会下降。[50]
很多国家的人口,如日本、德国、意大利和大部分前苏联国家在 2050 年都预料会比 2005 年少。在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生育率都低於死亡率。[51]
一个国家的人口密度不必然决定他们的经济繁荣程度。印度的人口密度与日本相近,但它的本地生產总值只有日本的十二分之一。决定他们财富差别的是他们不同的历史。
今天主张世界人口过剩而天然资源有限的人与马尔萨斯在十九世纪犯了相同的错误。而些错误是相信国家的财富是固定,而非因其特定历史条件决定。如马克思所说:
「人口过剩也同样是一个為历史所规定的社会关系,决不是由数字所决定的,人口限制并不是由生產生活手段能设定的绝对界限,而是由一定的生產条件所设定的限制……雅典过剩人口的数字是多麼的微不足道!」[52]
当马尔萨斯的名字被一再提起来主张资源不足支撑世界人口时,我们必须回应指出问题不在於短缺,而是因為经济体系不把粮食供应给有需要的人。
今天,持有这些主张的人最终把制度的经济和环境问题归咎於普通民众,如马尔萨斯一样。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50 年前否定这「对人类的诽谤」,我们今天也要如此。
33John Bellamy Foster, “Malthus’ Essay on Population at Age 200”,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p140.
34Thomas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1st Edition), Chapter 10, Part 5.
35John Bellamy Foster,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p139.
36Second Essay,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quoted in J B Foster, “Malthus’ Essay on Population at Age 200” in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p156.
37同上。
38John Bellamy Foster, “Malthus’ Essay on Population at Age 200”,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p145.
39马克思《论普鲁东(给施韦泽的信)》1865 年 1 月 24 日,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7 页。
40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572-573 页。
41同上。
42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1865年3月29日)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
43Cecil Woodham-Smith, The Great Hunger: Ireland 1845-9 (Hamish Hamilton, 1964), p411.
44数据来自 Sharman Apt Russell, Hunger: An Unnatural History (Basic Books, 2005), p226.
45Esme Choonara and Sadie Robinson, Hunger in a World of Plenty (Socialist Worker pamphlet, 2008), p8.
46同上。
47Sharman Apt Russell, Hunger: An Unnatural History, p212.
48生物柴油被当作无碳的石油代替品,但对於它是否能够减少碳排放仍然是个问号。有关这方面的资讯见 Fred Magdoff, “ThePolitical Economy and Ecology of Biofuels”, Monthly Review, July-August 2008 and http:// www.biofuelwatch.org.uk
49见于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20964/icode
50这一节的所有数据来自 John Molyneux, “Population: Is the world full up?”, Socialist Worker, 5 July 2008.
51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07), “Highlights” i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2006 Revision (2007).
52引自 John Bellamy Foster, “Malthus’ Essay on Population at Age 200” in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pp145-6.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大纲》(Grundrisse),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 46 卷下,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06 页。
第五章 阶级与社会公义
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為环境危机的影响,不成比例地集中於世上最贫穷的国家。不过,如果认為只有这些国家才受到影响,则是错误的想法。其实气候转变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它渗透到每一个国家,只是我们不会同等地感受到。正如联合国跨政府气候转变委员会主席拉金德拉.帕乔裡(Rajendra Pachauri)表示:「除了世上最贫穷的地方的穷人外,富裕社会的穷人同样受到气候恶化的攻击。」
事实上,不仅气候转变威胁到社会上最贫穷的一群,环境问题同样影响他们。因為其的经济状况令他们不能逃避到别处, 富裕人士却可以选择居於远离污烟瘴气的工厂区,以及买到乾净的食水。
恩格斯 曾指出在 1843 年的曼彻斯特,只要有钱就可以住在贫民窟之外,最有钱的更可以搬到「偏远的村落,享受花园,呼吸著乡郊新鲜和自由的空气」。他们被隔绝於工人阶级惨不忍睹的生活中,因為城市设计利用了道路将贫民窟遮蔽在商店之后。
因此,社会不平等的本质,将环境转变的影响更為恶化。举例来说,过冷与过热都可以致命:每当英国的气温较平均冬季温度低 1 度,就会有 8000 人死亡。他们大多是领取退休金人士,不能负担加暖房子的费用。这数字较很多更寒冷的国家还要差,例如俄罗斯、芬兰的人民就更有能力為冬天做好准备。[53]
夏天的热浪在全球亦可夺走数以千计的性命,而最穷的地区则最為受害。一份 2005 年的研究显示,美国有 6200 人因為太热而需送进医院,不少高危人士都是穷人和老人,或没有能力购买医疗保险的人士。
再者,环境灾难造成的破坏是不平等地分佈的。近期的例子,颶风卡特里娜 [ii](Hurricane Katrina)袭击新奥尔良就导致 2000 人死亡。因為地区及国家政府拒绝疏散整个城市,没有汽车、没有能力往其他地方逃生的穷人,或依靠福利援助者,就被遗弃在市内靠自己抵挡风暴。大部份被困在城内的贫民在风暴过后,為了获取基本粮食而打破了店舖的门窗,就被政府及媒体妖魔化,但那时根本没有任何外来的援助。
因此,气候转变所產生的不平等影响,意味著在争取一个更好和可持续社会的斗争中,那些处於社会最底层的人最能得益。其中,工人应是斗争的中心。
不过,许多环保份子将工人视為问题的源头。有时他们会指控那些生活得不够「绿色」的人,把他们当成与政府和企业一样,是製造生态问题的元凶。身处已发展国家的人,时常被教导要牺牲自己,以减低环境问题对生活的影响。
例如乔纳森 . 伯烈(Jonathan Porritt)就要求「每个人都要為自己生活中排放的碳量负责」,但这不必然是正确的。正如英国政府不断以私有化削弱公共交通系统,鼓励使用私家车,这解释了為何那么多人会自己驾车。其实,能源生產过程才是全球最大的单一排碳源头,个人的影响远小於政府的能源政策。
有时要求普通人改变生活方式以拯救地球,会產生更坏的结果。以阿诺.戈尔(AlGore)的电影《绝望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為例,无可否认它是介绍气候暖化问题最仔细的电影之一,以清晰易明的语言揭示其威胁。而在电影最后的部份,它要求我们以个人的方式回应全球暖化,如更换灯泡、為车轮更频密地充气(因為可以减低行车时的耗油量)、光顾绿色商品。
环境运动的活跃份子及新闻工作者大卫.赞臣(David Jensen)认為,即使每个美国人的生活跟随戈尔的建议,碳排放只可减少约 22%;如要将气候暖化变得可以控制,美国的碳排放需要减少 70%-80%,但没有人提及剩下来需要削减的 60% 碳排放。如继续只集中於个人的解决方法,我们将错过更為必须的整体社会改革。
当然,如果我们能生活得更「绿色」,我们的健康、城市以至整个环境都可受惠。不过,很多人的经济条件都难以负担过这种生活。这种方向不能阻止政府和企业继续以现时的运作模式破坏地球。
如果我们只要求个人的生活方式改变,為减碳作出牺牲,那是将责任推在个人身上。当我们看到在「碳密集」工业(carbon intensive industries)工作的人,这是特别重要的。我们要求减碳排,这对煤业、航行业、汽车业的将来有什么意义呢 ? 部份人士回答说只需简单地关闭所有工厂。乔治 . 蒙贝尔特(George Monbiot)认為以政府资助来拯救汽车工业是错的。反之,他主张经济衰退可以减少汽车的数量,这增加了公共交通革命的空间,将高速公路留给在城市间往来的公共汽车。[54]
蒙贝尔特之所以正确,在于政府应给予改善交通及减碳排的计划更多资源。但他的策略其实等同立即关闭车厂,这可能令数以千计的工人失去工作,更被疏离於环境运动中。
因此,社会公义在辩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时,是十分重要的。
如我们要挑战资本主义的优先考虑,就要赢得工人对运动的支持,那必须显示出他们的利益是整个运动的一部份。社会主义者会主张车厂不应简单地关闭,应该转变為生產对社会有用的產物,如公共交通的车辆。所以我们更要争取劳工赔偿、培训、新工作职位给予因闭厂失业的工人,而新的职位应是更环境友善(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工厂要转型為环境友善的生產,不一定是困难的任务。2009 年伟世通(Visteon)公司的 3所汽车零件厂倒闭,於恩菲尔德(Enfield)厂的工人就佔据了工厂為要拯救他们的工作。他们製造塑胶配件,当中的注射成型技术可被轻易地转化应用在其他零件生產上。正如那批工人在记者会上如此形容自己的职业:
「我们的技术──我们能製造任何的塑胶製品──应该被用来製造愈来愈被需要的绿色產品,如单车和拖车配件、太阳能板、循环再用垃圾桶、涡轮机等。」
相似地,在怀特岛的维斯塔斯(Vestas)风力发电厂,工人亦曾佔据并争取反对工厂的倒闭,他们理解抗争不单只是争取工作,而是关于地球的将来。
在资本主义下,工人生產了社会的全部财富。如果没有工人,发电站不能生產电力;工厂不能生產货物;原料不能开採、收集或分配;儿童不能接受教育;我们的工作地点、城市不能得到清洁。这都赋予工人,应说工人阶级,巨大的力量来停顿生產,停顿所有驱动资本主义的过程,以及令老板的利润消失。
马克思与恩格斯了解到,资本主义既可以将大量的工人集中於巨大的工厂及车间中,亦创造了可以改革社会的巨大力量。因此,他们在《共產主义宣言》(The CommunistManifesto)中指出,资本主义会製造它自己的「掘墓人」。
但工人所创造的新社会是怎样的呢 ?
53数据来自 Tracy McVeigh, “Flu and winter freeze set to kill thousands”, The Observer, 11 January, 2009.
54George Monbiot, “Car scrappage scheme will pour good money after bad”, The Guardian, 6February 2009.
第六章 可持续性
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对什么是「可持续性」,提出了三重定义。第一,使用可再生能源的速度,它要受制于再生的速度。第二,使用不可再生能源的速度,它需要受限于其他可持续能源替代它的速度。第三,污染及栖息地的破坏不能超过环境的吸收能力(assimilative capacity)。[55]
这种可持续性是可以与工业文明共存的。蒙贝尔特 (George Monbiot)在他的书《热》(Heat)中,尝试证明在 2030 年前,富有国家是可以既可维持工业社会,又可减少排放温室气体 90%。[56]
关於「可持续社会」的不同想像,其实是可以很直接的。它不能再依赖化石燃料来生產能源,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对再生能源的需求。同时,它需要剧烈地减少整体社会对能源的需求;建筑物需要设计得更為「隔热」;儘量消除浪费式工业,以及改善生產方法,变得更有效率。
一个可持续的城市需要大规模地改善公共交通系统,减少对无效、危险及污染性汽车的依赖,建设更有利单车及行人的空间;同时要重新进行市镇及城市的设计,确保远程通勤(commute)工作的时代已经过去。长距离交通需要向快捷、高效及廉价的铁路发展,并以乘客的利益為营运的最高考虑,非為铁路公司赚取利润。
再者,我们要以集体的社会制度取代依赖个别家庭去满足人类需求,如托儿所、洗衣房应更普及化。这将进一步节省能源,因為可以减少製造家庭电器的物料,以及它所產生的废料。
这些社会改革不单令地球受惠,亦大幅度地改善我们的生活,如工作的通勤、过份拥挤的房屋(工人阶级所依靠的)等。我们的城市可以受到更少污染,道路将更加安全。而一直以来负起照顾小孩责任的女性,能通过免费的托儿所,参与到更好的工作及获得更理想的收入。
以上大部份改变在理论上仍可与资本主义共存,但一个真正可持续的社会,应该以人类和地球的利益為前提,理性地组织生產活动,而不是為追求利润。换言之,生產需要「计划」起来。
不过,计划经济的构思对很多人来说,会联想起前苏联的「官僚指令经济」(bureaucratic commanded economy),即少数非民选出来及非问责的个人负责所有决定。它不但没有為人民的需要而生產,反带来低效、浪费,甚至引起了严重的环境灾难,如切尔诺贝尔事件或咸海的枯竭。因此,不少人对「计划」感到担心是可以理解的。正如蒙贝尔特(George Monbiot)在他的《热》(Heat)一书中指出,「处理气候转变的需要不能成為中央计划的藉口」。
但「计划」的定义可以有根本性不同的版本。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形容理想的计划经济為「一个经济系统的最高原则,就是其资源的分配与使用是由集体决定,建基于民主决策的过程」。[57]
真正的「计划」不等於由少数人作决定,它需要广泛及在资讯充足的条件下,辩论所有生產层面中的工作。关於生產的决定,需要所有製成產品的工人、使用製成品的人及住在工厂附近的人,共同参与。毕竟,要面对生產改变的不单是在车间工作的工人,及產品使用者,还包括经验著更多交通问题、更多污染的本土社区。相较之下,资本主义的生產过程则完全漠视社区。[58]
当然,计划不能只存在於社区中。在每个工作场域的生產决定,需要与其他城市甚至国际层面的连接起来,确保整体的合作性。
资本主义下,每个国家倾向為自己的利益组织生產。但一个更理性的社会应确认到自然资源分配的不均,以及确保任何地区都可使用需要的材料。同时,我们要终结生產物品过程中的不理性,例如选择在薪水最廉价的地方生產货物,然后再运往全球千里以外的角落。如我们要认真处理气候转变的问题以及其影响,则国际性的规划是必须的。
一个理性地组织生產的世界,能够决定需要减少什么,然后要求各產业、城市、工作间採纳碳减排的策略。每个个体将参与决定如何执行需要的改变,构成与同事间的讨论,再将资料、建议回馈到监管计划的团体。
计划生產意味著消除过度生產,减少浪费、低效,集中资源生產质素较佳、更耐用的產品,而非较高利润的產品。
资本主义的逻辑就是要将整个世界变作私有财產。只有当私有财產制不再是主导的產权形式,才可以落实民主决定资源的使用与分配。所谓的「计划」主张把生產财富的工具由社会共同拥有(social ownership),它同时被要求确保地球不会因為短期的生產利益而受到破坏。
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提出:
「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佔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59]
不幸地,目前拥有著和控制著工厂、工作间、矿场、森林、农场的人士,不会轻易地放弃它们,他们希望可以继续保持自己的财富和权力。他们将要面对一个大型革命运动的挑战,将土地、工厂重新分配给最适合运作它的人士。
55John Bellamy Foster, The Vulnerable Planet: 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9), p132.
56George Monbiot, Heat: How to Stop the Planet Burning (Penguin, 2006), p xii.
57Alex Callinicos, An Anti-Capitalist Manifesto (Polity, 2003), p122.
58参考 Michael Albert, Parecon: Life After Capitalism, for a interesting discussion of how democratic planning could work in practice.
59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78 页。
第七章:革命
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使之核心上要依靠燃烧石化原料作能源。事实上,若非依赖石化原料来提供高度集中的能源,人类文明不太可能达到今天在科技及工业发展上的高度。时至今日,几乎没有什么东西的出现不是靠煤、石油或天然气── 80% 的世界能源都来自这些资源。
在 2008 年,全球十间顶尖的企业中有八间的直接利润来自石化燃料工业──它们要不就是参与开发石油,要不就是参与生產要依赖燃油的汽车。[60]
因此任何对石化燃料制度的挑战,都等同於向地球上最有势力企业的既得利益及保护这些利益的国家挑战。
这些企业都精於维护石油的中心地位,阻止任何转变。举两个例子,企业运用数以十亿的资金来污蔑气候转变的科学,另一方面暗中破坏要求强制生產较少污染汽车的立法。
即使石油公司如何谈论要投资在太阳能上,事实是它们早已有数以亿计的投资在石油生產上,这会继续成為它们主要的利润来源。要解决环境危机便要向石油企业作出挑战。
在资本主义下,足以阻止气候不可收拾地转变的减排改革并非绝不可能。但这会否实现则是另一个问题。那些从石化燃料工业获利的势力跨国企业,每年都向世界各地政府中的政党捐赠数以百万英镑。更甚的是,每个政府都企图提倡这些工业的可盈利性,深怕不这样做就会输给其他竞争对手,而长远来说更可能败於其他竞争对手的军事挑战。因此,政府会尽其所能去避免对现状的任何挑战。即使面对由气候转变引起的庞大危机,政府仍不断地向企业利益低头,并拒绝实行有效的措施。
虽然机会很微,但尽管资本主义真的能够解决气候转变,在资本主义下是不可能重新修复人类与自然世界间之间的「代谢断裂」(metabolic rift)。因此我们跟自然世界之间不可持续的关系,仍是会為未来的环境危机造成威胁,工人仍旧会异化於他们四周的自然世界。这意味著我们必须用另一个制度──社会主义,来替代资本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白社会主义世界将会有著跟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一套优先考虑。
今天针对环境议题的斗争,目的是為了在当下赢得改变,同时是要令生态议题成為未来一些群众运动的核心。即使是关於一些小议题的运动,例如争取在工作场所设立回收或改善公共运输等,都可以為工人带来信心以应付更大的环境议题,以及改变我们今天身处的世界。
每当人们挑战现有制度,我们都看见一个新的、理性的社会的可能,一个由那些创造出所有社会财富的人组织及管理的社会。就算是最小型的工潮,男人和女人都需要组织纠察线、筹款及扩大行动。在反对伟世通(Visteon)及维塔斯(Vestas)关闭工厂的佔领工厂行动中,我们看到参与的工人抓紧了具世界重要性的议题,他们讨论、争议及说明世界可有另一种不同的管治。
愈大的斗争需要愈多的组织。当革命运动出现,工人组织拥有社会新的管治方式的种子。从巴黎公社到俄国革命,以及后来出现的所有斗争中,劳动的男女发明了新的民主组织──职场上选举產生的代表组成了委员会或工人议会,都让他们掌管自己的命运。
在革命的当中,这些团体组织起罢工及示威。他们同时组织起来以确保没有人因此捱饿,同时负责通报最新消息,以及管理必须物资的供应。
举例说,可以看看彼得.弗来雅(Peter Fryer)所描述的 1956 年匈牙利革命中的德鲁尔革命议会(Gyor Revolutionary Council),是数以百个起来反抗苏联控制的工人组织之一:
「它们是非常一致的:不论就其自发的情形——就它们的组成;就它们的责任感;就它们对於粮食供应与社会秩序的有效组织;它们对青年中狂乱份子的抑制;它们中多数能用以应付苏军问题的智慧;以及(最后的但非最不重要的)它们在许多方面与初次发生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后来发生於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的工农兵代表会议(即苏维埃)有极其类似之处——来说,都是如此一致的,它们是武装起义的机关——由工厂、大学、矿山与军队选出的代表聚集而成,同时又是人民自治机关。它们获得了武装人民的信任,因此它们享有很大的权威。
当然与任何一次“自下”產生的真正革命一样,这里发生著“太多的”说话,辩论,争吵,人们不停不歇地走动,口沫飞溅著,激动,鼓噪与沸腾。这是图画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方面却是那些平凡男女与青年——他们一向被秘密员警浸没在水底下的,现在则冒升到领导地位上来了。革命推动他们前进,鼓起了他们公民的傲气与潜伏著的组织才干,去在官僚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民主制度。」 [61]
就是这种革命组织构成了民主计划经济的基础──我们所需要的可持续社会的核心,它同时显示了革命过程如何激励普通人及给予他们信心开始掌握自己的生命及利益。
工人阶级斗争的最高峰是 1917 年 10 月俄国工人的夺权。有一个短暂的期间,工人管理自己的工厂及工作场所,為了社会的利益而不是老板的利益,来作出生產方面的决定。可是,由於俄国革命的孤立、资本主义势力对这个正在展翅的工人国家作出的军事攻击,以及俄国本身极度的经济倒退,革命最后转而走上了官僚控制之途。
斯太林的胜利和他「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教条,是对俄国工人阶级最巨大的打击。他对於工业急速及无限扩张的信仰等同是环境的大灾难。一位斯大林主义的计划者曾发起「一个对整个现存世界深刻的重新佈置…一切现存的自然界都只会按照人类的意愿及他的计划来生存、发展及死亡」。[62]
对於「大自然只是服务社会主义利益的工具」的信仰,是绝对不会被促成这场革命的男女所认可的。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第一代布尔什维克之一,就自然世界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作了详尽的书写。1937年,当他仍在狱中等候斯大林对他的处决,他写了《哲学花纹》(Philosophical Arabesques),当中他直接地否定了史达林主义官僚的信仰,并充份讨论了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
革命不等于简单地要求统治阶级放弃他们的财富及权力,虽然这是必须的。在资本主义下,工人遭到异化、分化及感到无力。只有经过革命的过程,一同体会组织、斗争及辩论,才可以将这些思想及感受转化成集体层面。
只有在革命过程中,工人阶级才可以「摆脱多年来的污秽及胜任於找寻新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的积极性不是因為要贩卖劳动力以求生存,而是因為他们是社会的一份子,而这个社会是按他们的利益来组织的。生產是以地球的利益為核心,其目的是要满足人的需要,而非為了一小撮老板的利益及盲目的经济增长。
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并不会在推倒了资本主义后一夜间出现。马克思指出在革命胜利之后,新社会仍会继承资本主义的方方面面,需要逐步来处理:
「我们这裡所说的是这样的共產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的了,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產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各方面都还带著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跡。」[63]
由於存在于资本主义时代的生產机器都被设计及创造成只為生產利润,它们很大部份需要彻底的改进及重新考虑,也有一部份需要完全地抛弃。
创造出这个新世界的人仍有很多的工作要完成,包括重新设计我们的城市、运输网络、工业、食物生產及分配制度,以确保其运作乎合大多数人及地球未来的利益。但只有取代了资本主义后,我们才能探索创造可持续未来的全部可能性。
60Fortune Global 500 list, 2009。见於 http://CNNmoney.com。
61彼得.弗莱雅《匈牙利的悲剧》(Hungarian Tragedy by Peter Fryer),王凡西译,信达出版社,1971 年出版。
62见於 Joel Kovel, The Enemy of Nature, (Zed Books, 2007) p 225.
6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0 页。
第八章:总结
对於资本主义是否可以解决目前的环境危机仍然是一个问号。我们身处的制度的非理性及无计划的本质、既得的利益,以及资本主义反自然的天性,就算在最理想的情况,这都意味著一场苦战。
然而社会主义者并不会坐下来等待革命的出现,我们相信要争取今天的改变。每一次环境运动的胜利,除了可以令世界变得更好,也同时强化了一般人改变世界的信心。
这就是為何我们要动员群众示威,以争取最好的国际减排协议。这就是為何我们要促请工会将环境保护放到他们政策的核心。这就是為何我们要支持反焚化炉和争取可再生能源的运动。这就是為何我们要争取创造千千万万个绿色就业的机会。
马克思及恩格斯的著作不单清楚剖析了世界為何会如此,它们同时是行动的指引。他们的思想帮助指出了整个制度的问题,以及提供了改革的策略。
世界的未来正面临危机,在未来数年我们很有机会看到一些争取改变的大型运动。社会主义者的目标是参与到这些斗争的核心,跟来自不同运动、不同传统的人合作,為能够永久地改变这个制度的策略提出理据。愈多人参与,我们便能做得愈好。世界的未来正面临危机,加入我们吧。
进阶阅读:
还有很多有关气候变化的书值得读者进一步阅读:两本站在激进立场解释有关问题和提出解决办法的书是 George Monbiot 的《热》(Heat)和 Jonathan Neale 的《叫停变暖,变革世界》(Stop GlobalWarming, Change The World)。Fred Pearce 的《最后一代人》(The Last Generation)非常好地讲述了历史上的气候变迁以及人类的应变机制。Heather Roger的《飘逝的明天:垃圾的隐秘生活》(GoneTomorrow: The Hidden Life of Garbage)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垃圾问题进行了独到的分析。
Chris Harman 在《马克思主义与历史》(Marxism and History)一书中的文章是介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极好读物。他的另一部著作《人民的世界史》(People's History of the World)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人类各阶段的历史进行了精辟的概括。Jared Diamond 的两本书《枪炮、细菌与钢铁》(Guns,Germs and Steel)和《大崩溃》(Collapse)很新颖地分析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
John Bellamy Foster 关於生态的作品都很值一看,尤其是其文集《反资本主义的生态学》(EcologyAgainst Capitalism)对很多问题都有很好的讨论,他的《马克思的生态学》(Marx’s Ecology)发掘了马克思著作裡的生态思想,其最新著作《生态学革命》(The Ecological Revolution)则在生态学领域重新树立起了革命社会主义传统的大旗。
Esme Choonara 和 Sadie Robinson 的小册子《富饶世界的饥饿问题》(Hunger in a World of Plenty)集中讨论了当今世界的食物生產与人口过剩的问题。
阅读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原著也是不可或缺的。就本小册子的讨论问题而言,有几本著作是很值得阅读的,特别是《资本论》。其他的有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它有力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破坏性一面;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自然科学问题的很好范本,这同样适用於对当前科学问题的分析。
马克思的短篇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裡包含有许多有关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运行的思想。AlexCallinicos 的《反资本主义宣言》(An Anti-capitalist Manifesto)认為民主的计划经济是适用於任何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的。Michael Albert 的《参与型经济》(Parecon)比较细緻地描绘了计划经济应该如何运转。Joseph Choonara 的小书《解剖资本主义》(Unraveling Capitalism)非常好地介绍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