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刘继明《人境》上部第二十六章
一本书其实跟一株农作物的生长的过程差不多。只不过农作物植根于大地之上,而书是植根于人的内心。
平原上的秋天总是那么短暂,往往还没等人们摘完田里的棉花或抜完棉梗,掐掉穗子的高粱和拔去棒子的玉米只剩下光秃秃的秸秆等着焚烧,天气就骤然冷下来了。头天身上还穿着单薄的夹衣呢,第二天早上起来推开门,一股逼人的寒气迎面扑来,冷得不由缩了下脖子,地上白乎乎的,像铺了一层薄薄的盐,或下了一场雪,睁大眼睛细看,原来是落霜了!
在乡下,秋天到冬天的更替,类似于彩色片向黑白片的转换。不是么?随着树叶一片片从树上飘落殆尽,裸露出铁青色的枝干,菜园里的青菜变得日渐单一、稀疏。沟渠的水早已干涸,露出了肮脏的淤泥和杂草。田间地头和沟坡上的野草一片枯黄。绿色像一支溃败的军队,在严冬的威逼下,正一步一步地从人们的视线里退却。乡村的景色正变得枯索凋敝,暗淡无神,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者。但庄稼人并不在乎色彩的变化。他们心里只装着24节气,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农事。一年四季环环相扣,循环往复,永无穷尽。他们对每个季节一视同仁,如同对待生老病死一样。在真正的冬天来临之前,他们照样很忙碌,抓紧时间抢播冬小麦、油菜籽和别的绿肥,以备来年的春耕。
对庄稼人来说,总是有忙不完的事情。忙碌是他们的宿命,忙完庄稼活儿,又轮到忙着操持一下自己的事儿了。最大的一件事当然是准备年货。在神皇洲,“年货”的内容极其丰富,从进入农历冬月开始,打糍粑、打豆腐、做豆筋子、熬米糖,杀猪、宰羊,一桩接着一桩,直到大年三十晚上,才算消停下来。
乡下人也喜欢把一些“人生的大事”放在冬天来操办。比如为老年人做寿,年轻男女的娶妻嫁人,甚至不少老人都是在冬天里寿终正寝的。所以每到冬天,乡下人总是有喝不完的喜酒,吃不完的寿宴或丧宴。每天都能听到红白喜事的鞭炮声,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一天到晚都不间断。在乡下人心目中,不仅是春节,就连整个冬天都是他们的节日。
对神皇洲人来说,今年冬天最大的一件事无疑是赵广富的小女儿赵满月出嫁。
早在几个月前,赵广富就开始为操办喜事准备,不间断地开着他那辆农用车去镇上打货,从置办酒席的各种食材,到待客的烟酒和糖果瓜子儿,一趟趟地往家里拉。这个神皇洲的种棉大户平日里由于把全部精力扑在庄稼活路上,总是心事重重,见了人也难得露出笑容,但现在像变了个人似的,见了村里的每一个人都满脸笑容,主动打招呼:“记住初八来吃酒,就不另请啦!”对方赶紧说:“一定上门恭贺,一定的!”
离初八还有几天,赵广富就把家里一头最大的猪杀了,接着,从外村请来的厨师挑着蒸笼案板,正式进入到赵家,蒸鱼糕,炸肉圆子,杀鸡剖鱼,开始大张旗鼓地张罗酒席。这个厨师跟赵广富是出了五服的本家,在河口镇颇有些名气,四乡八村有头有脸的人物置办酒席都是请的他。赵姓厨师名气大,派头也不小,光徒弟就带了两三个,再加上曹桂秀请来的几个来帮忙的信教的弟兄姊妹,这么多人,足可以置办几十桌酒席了。
初八前两天,满月坐着他哥长青的小轿车从县城回到了神皇洲。长青平时忙于生意,很少回家,这次趁着妹妹出嫁,正好带着老婆孩子一起也回神皇洲来住几天。
长青的小轿车还没有停稳,他爹赵广富就在门口点响了一挂万字头的鞭炮。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噼噼啪啪响了差不多半支烟的工夫,传遍了整个村子,村里不少孩子纷纷涌向赵家去瞧热闹。
满月出嫁的喜庆场面,没等到初八就提前开始了。
按照乡下的习俗,谁家儿子结婚或女儿出嫁,除了那家人的亲戚,本村人除非跟那家人发生过严重的过节,或者那家人在村里不受“待见”,大都是要登门贺喜的。神皇洲把这叫“份子钱”。早些年五元十元也能出手,近些年像物价一样渐渐涨到了五十元一百元钱。无论钱多钱少,都是一份人情。主人家按例都要一丝不苟地登记在册,以便日后还对方的“人情”。以赵广富多年来在神皇洲积累的人脉,村里来送“份子钱”的踏破了门槛,不少外村的人也都来了。其中一些人不仅是冲着赵广富,还是冲着赵家新女婿李海军来的。他们都是抗虫棉的种植户,今年棉花的大丰收,使这些尝到“抗虫棉”甜头的农户对李海军心怀感激,正好借这个机会表表心意。所以他们出的份子钱也比一般人家多,两百三百的都有。赵广富对此心中有数,派席时,他把这些人跟抗虫棉种植合作社的农户安排在同一张桌子。
让赵广富感到意外的是,马垃和谷雨也送来了“份子钱”,随他俩一起来随礼的还有小拐儿。马垃送的是五百元,跟村支书郭东生一样多。这个数目远远超出了一般的份子钱“规格”。刹那间,赵广富觉得以前跟同马垃和谷雨之间的那点儿“积怨”都变得无足轻重了。乡村的人情世故就是这样,怨愆产生得快,消失得也快。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他把马垃和村支书郭东生一起安排坐在上席,不但自己陪坐在旁边,还把长青和满月叫出来给“马老师”和“郭书记”敬酒。
满桌的人都争相给村支书郭东生和同心合作社理事长马垃敬酒,谷雨却只给自己的老师马垃敬了酒,对郭东生就像没看见一样。这多少让郭东生有些尴尬,他清楚谷雨心里对自己的“敌意”,但他毕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像没事似的举起酒杯,对马垃和赵广富说:“你们是两个合作社的当家人,今天得喝一杯呢!”
马、赵两人互相看了对方一眼,不约而同地举起酒杯,喝干了杯子里的酒。
“今后村里的发展就看二位啦,我借满月的喜酒敬二位!”郭东生说着,也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
赵广富是个懂得礼数的人,他还亲自去堤上的哨棚把村支书郭东生他爹郭大碗也请到家,坐了一次上席。
来吃喜酒的人越多,赵广富心里越高兴。份子钱的多少已无关紧要,他看重的是自己作为“大户”,在乡亲们心目中那份厚厚的人缘和“名望”。对庄稼人来说,这是对他在土地上劳作了一生的最高奖赏。
接连两天,流水席从摆早到晚,几乎没有间断过。从赵家屋子弥漫出来的浓浓酒肉香味在空气中飘荡,村里的猫狗也被熏得直淌涎水。
初八当天,赵家请来的荆河戏演出队在村中心的闸坝上搭起戏台,荆河戏名角武海生和白小娥主演的传统老戏《三娘教子》,让神皇洲的新老戏迷们大饱了一次眼福。
整个神皇洲都沉浸在节日一样的欢乐气氛中。
这天下午,从县城开来的娶亲车队,一溜十来辆簇新铮亮的豪车沿着新竣工不久的水泥路,开到了赵家的大门口。新郎李海军西装革履,胸前佩戴着红花,因染了发满头乌发,红光满面,看上去一点不像已经年过五十的人了。他从最前面的一辆奥迪轿车里钻出来,跟以证婚人身份上前迎接的村支书郭东生手拉着手,肩并肩地走进了赵家。
傍晚时分,在热烈的鞭炮声中,车队又从赵家开了出来。新娘赵满月和新郎李海军坐在最前头的那辆奥迪车里,长青自己开着车在车队最后面,作为新娘的哥哥,按照习俗,他要把妹妹一直送到县城去。
赵广富和曹桂秀老两口站在欢送娶亲车队的人群中间,目送着车队浩浩荡荡地开出村子,消失了好一会儿,才收回目光……
满月出嫁后不到一个星期,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就降临了。大雪整整下了三天,头一天下的是盐粒状的雪子儿,刷刷刷地落到地上,打在人的耳朵上生疼生疼,到第二天傍晚,雪子儿变成了雪片儿,小的像鸡毛,大的像鹅毛,洋洋洒洒,漫天飞舞,到第三天早上,田野、村庄都穿上了雪白的大氅,连干涸的水渠里也快要被厚厚的填平了。道路上的积雪足有一尺来深,行人一只脚陷进去,另一只脚就很难拔出来。村边的那口水塘也结了冰,整个神皇洲呈现出几十年都未曾见过的雪景……
在这样罕见的大雪天,除了雪地里打雪仗、撵兔子的孩子,大人们都猫在家里,燃起热乎乎的树兜子火,端出早就准备好的年货,扯闲话、看电视、打牌,尽情地享受着老天爷赏赐的闲暇时光。
马垃身边除了小拐儿,多了条狗──“社员”。大碗伯被儿子郭东生接到镇上过冬去了。在严寒的冬天,怎么能让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独自待在哨棚里呢?但郭东生的老婆张玉兰最害怕狗,她给郭东生接他爹去家里过冬开出的条件是:不允许“社员”进门。所以大碗伯临走之前,把“社员”托付给了马垃。这倒让马垃求之不得。他和小拐儿都喜欢“社员”,有什么吃的总给它留着,久而久之,“社员”都有点舍不得离开他俩了……
这是马垃回到神皇洲度过的第三个冬天。由于身边多了一个少年和一条狗,这个冬天虽然比起那两个冬天都要寒冷,但他却一点也不觉得难捱,反而感到其乐融融。
这样的日子正好让马垃暂时放下合作社的事情,静下来专心写那本书。自从在劳改农场开了一个头之后,他就再没有往下写了。但他从来没忘记过这件事。仿佛一颗种子,随着季节的更替,它会扎根发芽,不断生长,直到结出丰硕的果实。一本书其实跟一株农作物的生长的过程差不多。只不过农作物植根于大地之上,而书是植根于人的内心。人的内心也需要大地的滋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写书的人跟一个种庄稼的人是同一类人,身上应该具有相同的气质,比如勤奋、忍耐、自尊、仁慈和爱心,以及一种几乎与生俱来的责任感。毋庸讳言,马垃就是这样一种人。写作跟在土地上劳动一样,对他都具有同样的诱惑。最重要的是,写作不需要别人授权,只要有表达的需求和能力,你就可以拿起笔来。这跟种地差不多一样。只要你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就可以在上面耕作、播种、收获,甚至即便你没有土地,也可以扛起䦆头去开荒垦殖,用自己的双手开垦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
大雪封门的那几天,马垃几乎整天把自己关在楼上的书房里写作。虽然他已能够熟练地使用电脑和网络,但他还没有习惯在电脑上写作。他还像以前一样,在那个黑色塑料外壳的笔记本上写,而且还是用的那种老式蘸水钢笔。光墨水就买了好几瓶,摆在书桌前,供他随时补充墨水。马垃觉得,手里的钢笔仿佛一根小小的魔术棒,将自己带回到了过去的岁月,就像一些科幻电影里的人物那样,他又回到了三十年前的神皇洲和二十年前的河口镇以及沿河县师范,看见了父亲、娘、哥哥、逯老师,以及壮年时期的大碗伯和青年时代的自己,还有那些熟悉的但已叫不出名字的人。许多消逝的往事宛如电影的胶片在眼前一一重现。他觉得自己的心跳加速,呼吸渐渐变得粗重,眼睛也忍不住潮湿起来。那一刻,马垃完全被自己的写作“俘虏”了。此时的他,已不再是一个曾经的企业家和刑满释放者,或者是神皇洲一个的桃园的主人和同心合作社的理事长,他只是一个正在写作或劳动的人……
马垃写得如此投入,以至忘掉了外面纷飞的大雪和冻彻入骨的寒冷。当他停下笔来,发现自己的手差不多快要冻僵了。他不得不站起身在屋子里走动一会儿,活动一下身体,让渐渐麻木的四肢恢复知觉。和四肢一起恢复知觉的还有饥饿感。因为这时到了中午或者晚上,也就是说他已经有半天没吃东西了。于是,走下楼去,跟小拐儿一起做午饭或晚饭。
大碗伯被郭东生接到镇上去过年之前,把他养的两头猪卖掉一头,杀掉了一头,大碗伯让郭东生拿走了一半。马垃把另半边买来了,有一百来斤,腌制成腊肉,够他和小拐儿吃一个冬天了。在乡下,冬天尤其是雪天的饭食比较简单。火塘里架着树兜一天烧到晚,想吃什么就支起一个三脚架,把锅放在上面,吃的喝的都在火塘边,既省事又暖和。腊肉加白菜萝卜,放在火塘上炖得烂熟,香喷喷的。马垃和小拐儿天天吃都吃不厌。一段时间下来,不仅他们俩都胖了许多。就连每天吃他俩啃完的骨头和剩菜剩饭的“社员”也养得膘肥体壮,身上的毛跟绸缎似的又光又滑……
雪停了。但气温仍然很低。整个大地都被被封冻起来了,屋顶上堆满了厚厚的雪,树枝上披着沉重的雪衣,树枝不堪重负落到积雪上,戛然断裂成几节,发出令人心碎的呻吟。如果这时正好有人从树下走过,难免不被溅起满身的雪粒儿,吓一大跳,如果折断的树枝正好砸到身上,那就更倒楣了。
马垃惦记着他的那些猕猴桃树,暂时放下写作,拿起一把竹杆儿,叫了一声正在火塘边烤火的小拐儿,“走,跟我一起去桃园看看!”这大雪天的,小拐儿连去村里串门都去不了,整天只能在火塘边烤火,正闲得无聊呢,赶紧起身去换长筒靴。出门时,“社员”像条尾巴似的也跟了过来。
江堤像一只披挂着雪白铠甲的巨蟒横卧着。堤坡上的积雪有一尺多深,差不多快到膝盖了,马垃把竹竿儿当拐杖,从堤脚爬到堤上,摔了好几个跟头,身上裹满了雪,像个大雪人似的。小拐儿也强不了多少,一只靴子现在雪地里,拔了好一会儿才拔出来。倒是跟在后面的“社员”,四只蹄子轻快地点击着冻结的积雪,眨眼的工夫就跑到了堤上。
站在堤上望去,防浪林像一道冰雪砌成的屏风,银光闪闪,老远就能让人感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凌冽寒气。荒芜的外滩白雪皑皑,变成了一片茫茫的雪原,江水像一块蓝色的宝石,静静地躺在在雪原的尽头。
马垃带着小拐儿和“社员”穿过防浪林,来到了桃园。正如他担心的那样,猕猴桃树上厚厚的积雪,原本柔韧的枝条承受不住,东倒西歪,不少树枝已被压折了。为了防冻,马垃和小拐儿入冬之前给每一棵树干都裹了层保暖的稻草,但现在这些稻草已被连日的雨雪沤烂,纷纷剥离掉了。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不等雪融化,猕猴桃树就会在大雪的重压下死掉。
马垃和小拐儿挥动竹竿儿,将猕猴桃上的积雪掸掉。不到一会儿,两个人的手就被冻得竹竿儿都握不住了,只好停下来,往手上不停地哈气,直到手重新能握紧竹竿儿,又开始掸雪。他俩从早上干到中午,回去简单吃了点午饭,又回到桃园接着干。快天黑时,才把桃园里所有猕猴桃树上的积雪掸掉。正当他俩要离开桃园时,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社员”急促的吠叫声。
小拐儿拄着竹竿儿聆听了片刻,很有把握地说:“准是‘社员’逮到野物啦!”,说罢,不等马垃反应过来,便拔腿向狗吠的方向跑去。过了没多久,小拐儿就回来了,手里拎着一个什么东西,边跑边喊:“兔子!‘社员’逮到兔子啦!”
话音未落,“社员”像一道黄色的闪电来到了马垃面前,得意地围着他转了好几个圈,还把前爪伸到他胸前抓挠着,似乎是向他索要奖赏。
小拐儿拎着兔子的耳朵,兴冲冲地跑到马垃面前,说:“马叔,今天咱们炖兔肉吃吧!”
“好啊,换个口味吧,兔肉比猪肉好吃多了!”马垃一边说,一边咂了几下嘴巴。那只野兔只是被“社员”咬伤了,还没有死。这个可怜的家伙,大概是被饿得受不了,溜出来找吃的时被“社员”逮住的。他想。脑子里浮现出小时候在雪地里撵兔子的情景。也是在这外滩上,也是一个大雪天,他曾经和哥哥徒手逮到过一只兔子,足有三斤种,他和母亲、哥哥三个人吃了两顿才吃完。那是他吃到的世界上最美的野味……
天终于放晴了,太阳总算露出头来,田野上的积雪在一点点融化,屋檐下的凌钩子不断地缩小着体积,水珠叮叮咚咚地滴个不停,把地上都砸出了一个个窟窿,到晚上气温变低后,又凝结不动了。
春节一天比一天近,各家各户都加快了做年货的节奏,杵的杵糍粑,熬的熬麻糖,杀的杀年猪。村庄上空的年味儿越来越浓了。
在神皇洲,糍粑是不可缺少的年货,如果不是家里的情况太糟糕,怎么也得杵几个糍粑。杵糍粑是个力气活,至少要四个精壮的男人,一般人家人手不够,总要在村里请几个人来帮忙。所以每到春节前的那段时间,村里的男人们显得比平时还要忙,常常是这家的糍粑还没杵完,那家人就来请了。但即使再忙,男人们也很乐意这份差事。杵完糍粑,主家还有好酒好饭招待,何乐而不为呢?
神皇洲今年多数人家的收成都不错,无论种棉花还是水稻,都是一个难得的好年景,所以杵糍粑的也就比往年多。可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去外面打工还没回来,不少人家杵糍粑都缺人手。有人想到了住在堤脚下的马垃。一开始,他们对能否请得到并没有信心。在很多人眼里马垃还是个“客人”。同心合作社的几家农户倒没有那么多顾虑,抢在别人家之前去请马垃。但他们与其说是请马垃帮忙,倒不如说是借此机会把“理事长”接到家里吃一顿饭。平时,他们想接“马老师“到家里吃顿饭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合作社章程里严格规定,理事长不得接受合作社成员的吃请和礼品呢。
这样一来,马垃在春节之前的一段日子里成了个大忙人,差不多每天都有人上门来请他去帮忙杵糍粑。对于这份意外的差事,马垃倒是挺乐意的。他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多跟村里人接触,增加一下彼此的感情,免得总是被当做客人。
马垃离开堤脚下那座带风车的房子,往村子里走去。虽然马垃不愿意被村里人当做“客人”,但每次去给人家打糍粑时,总是像出门做客一样,穿戴得整整齐齐,脖子上还系了条围巾,头发梳的一丝不苟,衣服上看不到一点泥星子。这是他从前教书时养成的习惯,也是神皇洲人很难把他当成一个地道庄稼人的原因。
雪后的天气虽然晴朗,气温却仍然很低,夜里和早上都在零度以下,中午前后才渐渐暖和一些。田野上的积雪越来越稀薄,有的地方已经露出了黑色的泥土和一点浅浅的深绿色,那是刚绽芽不久的冬小麦。道路上的冰凌还没有完全解冻,只是由于行走的人渐渐增多,冰凌和泥巴混合在一起,踩踏的人多了,路中间就变得越来越泥泞难走。幸好路两边的积雪尚未融化,行人便小心翼翼地踩着路边的积雪往前走。但时间一长,路边的积雪又被人的脚步踩得稀巴烂,化成了一片泥泞……
马垃穿着一双长筒雨靴,不在乎路上的泥泞。在村口,不时有人迎面走过来,如果对方挑着担子,他就提前在路边停下来主动打招呼,对方也赶紧停下步子,抬起被风吹得通红的脸,谦恭地招呼一声:“马老师,这是去帮人杵糍粑呀?”如果恰巧那人过两天要杵糍粑,多半会趁机发出邀请:“马老师,过两天请你帮忙杵糍粑,你可得赏光呀!”马垃知道这只是一句“搭口话”,不必当真,无须正式答复,所以只是含糊地嗯哪一声。如果那人是认真的,第二天自会专程上门去请他。
进村后,碰上的行人更多了。每走几步,就有人跟他打招呼,神情和语气多少有点儿新奇。因为,平时他们是很少看见马垃在村子里出现的;即便出现,他也主要是跟合作社的农户谈事情,很少跟其他农户打交道。但现在,由于“杵糍粑”,马垃开始走进更多的农户家里,如同走亲戚一样。这使他在回到神皇洲整整三年之后,真正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村民们那一张张质朴、热情的笑容,让他感到亲切。这使他意识到,自己跟这块土地以及这群人之间无法割断的血缘般的联系。这种联系仿佛种子一样,从他两三岁跟着母亲和哥哥流落到神皇洲之后,就在他心里播下了。这是一种彼此牵挂、休戚与共,只有亲人之间才有的情感。正是由于这种情感的存在,他才不感到孤独,并且从中体验到一种“不被肉体所摧毁”的幸福。
在闸上老万的小卖部门前,马垃看见一些穿着时髦羽绒服的陌生年轻人。他们都是刚城里打工回来过春节的。这些年轻人大多不认识马垃,见了他便远远地投过来好奇的目光。由于从前的经商经历,马垃对这些打工的年轻人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他主动走过去打招呼,问他们是谁家的子女,在哪个城市打工,每个月能挣多少工资等等,这些在外打工年轻人本来就擅长交际,很快就和马垃熟络起来。跟他们聊了一会儿,马垃感到自己也变得年轻了许多,连吹到脸上的风也没有刚才那么寒冷,仿佛春天已经提前来临了似的。他觉得,平时几乎只能见到中老年人的暮气沉沉的神皇洲,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青春靓丽的面孔,整座村庄也变得年轻了……
谷雨家有几年没杵糍粑了?他自己恐怕都说不清。前些年,家里欠了一屁股债,他在外面打工,挣的钱能填饱全家老小的肚子就不错了,哪有闲粮去换糯米打糍粑呢?那时候,谷雨为躲村里的债务,春节时连家也不敢回,茴香只好带着孩子回娘家去过年,自家也就什么年货也顾不上置办了。
这两年的情形自然不同了。从去年成立合作社起,谷雨家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过。特别是今年,他家养的两头猪都超过了一百多斤。这两头猪简直就像两台大功率的造粪机,为他家的沼气池提供了足够的能源,家里那几亩稻田的施肥问题也得到了根本的解决。谷雨家仅今年一年的水稻收入,就超过了前两年庄稼收入的总和。入冬后,他重新修整了一下房子,还添了几件新家具。原来那个破破烂烂的家焕然一新,一直穷得抬不起头来的谷雨,总算找回了自己的尊严。作为男人,他现在不仅可以让老婆孩子吃饱穿暖,还因为跟马垃一起为同心合作社的成立和发展操心奔忙,获得了农户们的尊重。以前那个很少有人拿正眼瞧的谷雨,越来越成为神皇洲一个不能忽略的人物了。想到这一点,谷雨激动得夜里都睡不好觉。一睡不着觉,他就和茴香开起了“被窝会”。
谷雨说:“今年过年,总算可以杀头年猪了。”
茴香说:“杀大的还是小的那头?”
“当然大的那头。小的那头卖了再换两只,不,换三只猪娃子!”
“杀大的,吃的完么?”
“不只是自己吃,还要送人呢!”
“送谁咧?”
“你爹妈,我老丈人和丈母娘嘛。前几年你娘家可没少帮衬咱们。”
“算你还有点良心……”
“还要送两刀肉给马老师……没有他,就不会有合作社,我谷雨也就不会有今天。”
“那是。马老师是咱家的福星呢!”
“不只是咱家的,还是全村的福星啊!”
“今年还是请马老师咱们家吃团年饭?”
“把小拐儿一起请。这一大一小两个男人,终归不像一个家啊……”
“你说马老师这么大年龄,怎么一直不成个家咧?”
“唉,马老师这样优秀,能配上他的女人太少了。”
“……今年村里打糍粑的人家越来越多了。”
“嗯。咱们家今年少说也要打五十公斤糍粑,而且要去河口镇市场上换最好的糯米!”
“你这口气大的!不打就不打,一打就打五六十公斤,赵广富家也不过打这么多咧……”
“我就是要跟他老赵家比!”
“还在跟人家赌气?别忘了赵广富差点儿成了你老丈人……”
“你说你这人,都陈谷子烂芝麻的事,老提它搞么子?”
“好好,不提了。还是说打糍粑的事儿。你说吧,请哪几个人来帮忙咧?”
“马老师一定要请,别的人你定……”
“只怕你不一定能请得到马老师,村里人都争着请他……”
“嗤!我跟马老师是什么关系?哪个也争不过我,别人请马老师他可以不去,我去请他能不来?”
……
谷雨说的没错。杵糍粑那天,马垃不仅早早地来到了他家,还把小拐儿也一起带来了。谷雨很高兴,小拐儿虽然使不上多大劲儿,但多一个人,就多一份热闹。打糍粑不就是为了图个热闹么?
这天晚上,谷雨家像过年一样热闹。家里被电灯照得一片亮堂,门口屋檐下也临时装了一只100瓦的灯泡,炫目的灯光照得四周白晃晃,连门口的篱笆和厨房里飘出来的炊烟和蒸汽也看的清清楚楚。茴香一个人忙不过来,请了胡嫂来帮忙。两个女人在厨房里忙的团团转。木柴火在灶膛里哔剝作响,大铁锅里已经添了几次水,蒸笼里的糯米开始飘出阵阵香味。
堂屋里,谷雨已经把碓窝子洗的干干净净,糍粑棍插进放满清水的木桶里,就等蒸熟的糯米出笼了。
杵糍粑可是需要一把子蛮力的。小拐儿腿瘸,杵糍粑使不上劲,谷雨就安排他从厨房往堂屋端糯米。当厨房里茴香揭开蒸笼盖,将蒸熟的糯米舀到筲箕里,小拐儿便端着筲箕冲出厨房,向堂屋奔去。糯米是粘性的,必须趁热才能杵烂,从蒸笼到碓窝子之间的时间越短越好。所以小拐儿跑得飞快,那条瘸腿像上足发条的时钟指针一样直往前窜,一点也不比健全人慢。马垃和几个汉子也忙起来了。他们操起糍粑棍,围着碓窝子一边用力杵,一边转着圈子。不到一支烟的工夫,碓窝子里颗粒分明的糯米就变成了一团黏糊糊的“米团子”。这时候,几根糍粑棍同时一用力,糯米团子被高高地举起来,重重地落到旁边用木板做的案板上,早就做好准备的谷雨捋起袖子,不一会儿就将“糯米团子”做成了一个又扁又圆、形似车轮的糍粑。
每杵完一个糍粑,棍子上都沾了不少杵得很烂的糯米,神皇洲叫“糍粑箝子”。这可是小孩们眼里“美食”,往往不等大人们放下棍子,就被抢走了。谷雨的儿子蝌蚪也不例外,糍粑还没杵完一半,他的肚子已经被“糍粑箝子”撑得圆溜溜的了……
一场糍粑杵下来,再壮实的男人都会精疲力倦。不过,茴香已把夜宵准备好了。说是“夜宵”,其实比正式的饭菜还要丰盛。因刚杀完年猪,谷雨特意把猪心肺留着,就是为今天打糍粑准备的。在神皇洲,被请来喝心肺汤的都是尊贵客人。对谷雨来说,马垃就是他的贵客,所以吃饭时,理所当然地被请到了上席就坐。
马垃心里自然很高兴。这几天他心里都高兴。隔三差五被村里人请来请杵打糍粑,使他恍若回到了小时候,每逢村里谁家杵糍粑,一帮子伙伴就跑到能那人家里,专等大人放下棍子,便一哄而上地争抢,抱住棍子啃糍粑箝子。那时候,杵糍粑带给小伙伴们的乐趣仅次于过年。
当然,更让马垃心里高兴的还有谷雨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了。在他心里,谷雨可不是一般的村民,甚至也不止是从前的学生,而是这几年跟自己一路打拼下来的同心合作社的“战友”和“助手”呢!
人一高兴,就忍不住想喝酒。酒一喝多,脑子里就活跃起来。马垃很长时间没有沾过酒了,今天算是破了戒。他就是在这会儿冒出那个想法的:“谷雨,村里回来不少年轻人,咱们组织个舞龙队,活跃活跃村里的气氛吧?”
此言一出,不仅是谷雨,其他几个人也纷纷表示赞成:
“好!咱们村好多年没玩过龙了,过年也越来越没意思……”
“马老师,我小时候就学过玩龙灯,要真成立舞龙队,我第一个报名!”
“这些年村里死气沉沉的,也该热闹热闹啦!”
但也有人提出了疑问:“成立舞龙队可是要花钱的事,可钱从哪儿出呢?自从国家免掉农业税后,村委会那帮干部么子事都懒得管,更莫说掏钱……”
谷雨手大大方方地一挥手:“ 莫指望村里啰,这笔钱我们合作社出!”说完,把目光转向马垃,似乎在向他征求意见。
但马垃没有马上表态,而是想了想,才对谷雨说:“合作社章程上没有这笔支出,咱们得严格按规定办事呢。”
谷雨有点急了:“那……怎么办?”
“没关系,钱不多,由我来出。”马垃笑道,“今年我的猕猴桃可是买了些钱哟!”
谷雨摇了摇头:“不行,村里的事儿,怎么要你一个人出钱。再说,成立合作社时你出的基金’还没还你……”
“谷雨,你么时变得婆婆妈妈,尽算这些拈不起筷子的账呢?”
听马垃这么说,谷雨脸不由一红,当即就表态道:“既然马老师要出钱,我也出一半,我家今年收成也不错咧,再说了,我好歹是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哪能落后?”
马垃见谷雨这副认真的架势,就半开玩笑地说:“家里开支的事,茴香不点头,你一个人做得了主?”
“马老师,这你可看低了茴香,自从我从城里打工回来后,她可从没扯我的后腿……”
话音未落,茴香端着一盘刚炒好的菜从厨房进了堂屋,她警惕地瞪了谷雨一眼,问:“我何时扯你的后腿啦?”
大家哄然大笑。谷雨只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茴香放下菜碗,看着马垃说:“马老师,别的事谷雨说了不一定算,这事儿我支持!”
马垃的目光在谷雨和茴香两口子脸上来回扫了一遍,忍不住赞叹道:“真是志同道合的一对啊!来,我敬你们一杯!”
从不喝酒的茴香大大方方地从桌上端起一杯酒,跟马垃碰了一下,一饮而尽。谷雨见媳妇这么爽快,岂能落后,跟着也一仰脖子,把杯子里的酒喝了个精光……
没过几天,神皇洲的舞龙队就成立了,舞龙队除了马垃、谷雨和曹广进,还吸收了两个从城里打工回来的小伙子,基本上都是同心合作社里的人。所以村里人都把这支舞龙队看做是合作社的。
舞龙队很快开始了紧张的演练阶段,地点就在马垃家里。由于神皇洲这么多年没人舞过龙,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很稀奇,像看西洋镜似的跑来观看舞龙队的演练,把马垃那幢有风车的房子挤得水泄不通。
曹广进年轻时候舞过龙,其他几个包括马垃、谷雨都是第一次舞龙,所以曹广进成了名符其实的“教头”。队员中除了他,就数马垃年纪大了,一开始,他做什么动作都不到位,热的几个年轻人发出一阵阵讪笑。这倒激发了马垃那股不服输的尽头,学起来更认真,被曹广进摆弄来摆弄去也不介意。演习了两天,动作最规范的不是几个年轻人,倒成了马垃。
话说这边舞龙队的这帮人抓紧时间在苦练舞龙的本领,争取春节时在全村父老乡亲们面前大显身手,另一边赵广富听说了同心合作社成立舞龙队,马垃还亲自参加舞龙的消息,心里“咯噔”一下,从女儿满月出嫁的欢喜情绪中醒了过来。他背着手到老万的小卖部门前转了一圈,听见所有人都在谈论舞龙队的事儿。同心合作社和马垃这回可是真出尽风头了!赵广富忍不住想。神皇洲可不是同心合作社的,更不是马垃的,他赵广富在神皇洲也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这个神皇洲的老资格庄稼人,抗虫棉合作社的理事长,觉得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到今后在神皇洲谁是“老大”和“老二”的大事。赵广富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性。他在家里琢磨了一整天,夜里都没睡好觉,第二天,终于做出了决定:以棉花合作社的名义成立一个舞狮队,全部费用由他一个人承担!
抗虫棉合作社成立舞狮队的消息很快就在神皇洲传开了。村里大人小孩无不拍手称快,直呼今年的春节可真热闹起来了,也有嗅觉灵敏的村民觉得异乎寻常:村里几乎同时冒出一支舞龙队和一支舞狮队,牵头的又都是神皇洲两个合作社举足轻重的人物,好家伙!这分明是一场大比拼、大竞赛的架势么……
仿佛只是一眨眼间,一年一度的春节就来临了。大年初一上午,虽然没下雪也没下雨,但天气干冷的厉害,天气预报的气温都到了零下3度,厚厚的牛皮凌把路上冻得硬梆梆的,不少早起走亲戚拜年的行人脚底板打滑,摔得手里的礼品抛出去老远。
也就是在这个时辰,神皇洲的舞龙队和舞狮队开始闹腾了。铿铿锵锵的锣鼓声把那些还在做梦的小孩子从热被窝里拽了起来,连早饭都顾不上吃,就咪瞪着眼睛往锣鼓喧天的地方奔去。
舞龙队和舞狮队一开始是各玩各的,分别挨家挨户地给村民们拜年。在乡下,龙和狮子都是吉祥物。让它们在自己家里里外外闹腾几圈,既能驱走邪气,又能为新的一年迎来财富和运气。所以都巴不得舞狮队和舞龙队在家里都玩一会儿儿。而且出手的“利市”很大方,都是平时自己舍不得抽的精装白沙烟。如果舞龙队或舞狮队耍得好,拿出百元大钞的都有。所以,两支舞龙队和舞狮队也各显神通,把浑身的解数都使了出来。哪个队的围观者多,就证明哪个队的表演更出色。
小拐儿专门负责帮舞龙队收礼。没多久,他拎的蛇皮袋就装满了各种牌子的香烟。
不知是巧合,还是事先计划好的,舞龙队和舞狮队不约而同地在赵广富家门口相遇了。一条“龙”和一头“狮子”,再加上一直追随在后面的男女老幼观众汇合在一起,赵广富家门口人山人海,像开演唱会似的。
人们自觉地在赵广富家门口腾出一块空地让舞龙队和舞狮队表演。随着锣鼓声突然变得急促高亢,舞龙队和舞狮队表演了各种高难度的动作,一会儿,龙把狮子环绕在中间,一会儿,狮子从龙身上腾跃过去。忽左忽右、忽高忽低、两支队伍的动作和速度越来越快,让人眼花缭乱,分不清彼此,让人紧张兴奋的喘不过气来。后来,龙和狮子忽然各自跳到一边,分别围着赵广富家环绕了三圈。按照习俗,只有德高望重的人家才有“狮龙绕屋”这一出。这是舞狮队和舞龙队给赵广富最高的礼遇。
赵广富放了一挂一万响的鞭炮。满月出嫁时他家里剩下好几挂鞭炮,过年都没用去另买。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赵广富看见马垃跟谷雨几个年轻人举着一条黄色的巨龙,脸上浸满了汗水。其中有一只鞭炮在离他很近的地方炸裂了,飞溅的纸屑落到脸上,他都没顾得上去拭一下,又挥舞着黄龙,与迎上来的狮子展开了“较量”。
这个马垃,四十多岁的人了,还跟年轻人一起玩这种蹦蹦跳跳的游戏,他这么逞能,到底图个么子呢?赵广富正这么想时,舞龙队突然停了下来。人群中发出一阵惊呼。赵广富一抬头,看见马垃不知何时摔倒在地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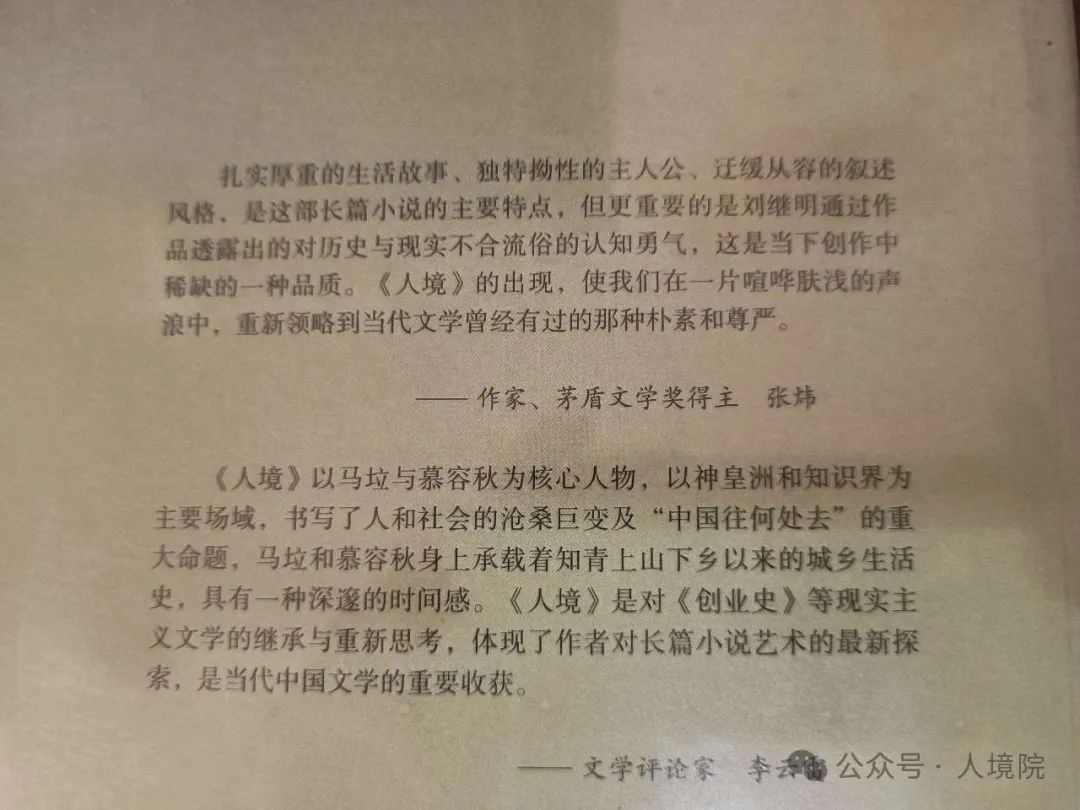
更多精彩连载,请点击进入特别专题:【刘继明《人境》全书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