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刘继明《人境》上部第二十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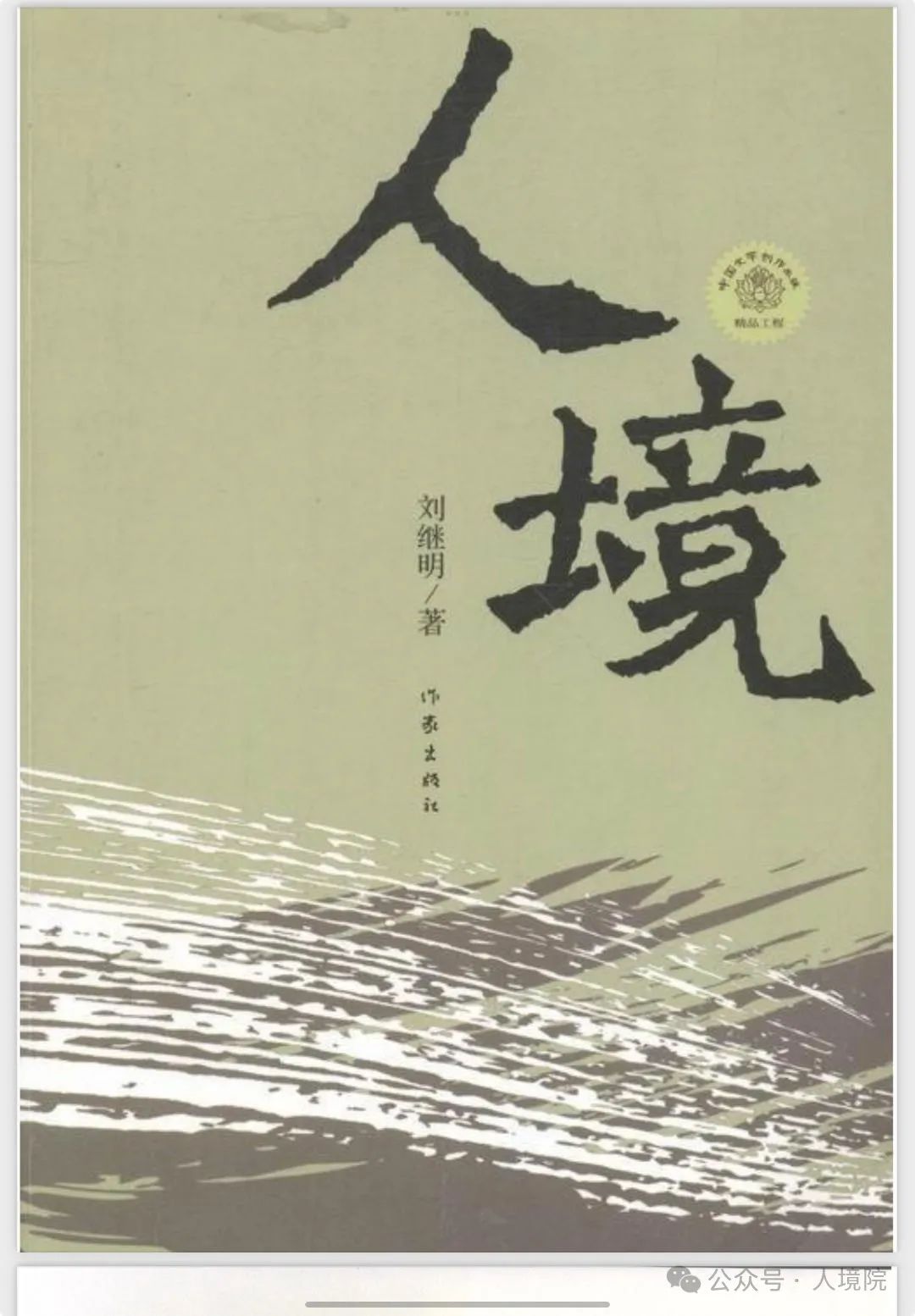
世界上的事情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除了家庭和亲人,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
同心合作社的“旱改水”工程进入了尾声,马垃和谷雨从长沙买回来的稻种也下了秧。
在水稻种植中,下秧育种是个最具有技术含量的环节。稻种泡几天水,秧田里的水几寸深,种子撒的均匀不均以及施多少肥料等等,都很有讲究,出一点差错都会影响秧苗的生长。有人种了半辈子田,始终掌握不了这门技术。在神皇洲,真正掌握育种技术,称得上“行家里手”的只有赵广富和大碗伯。搞集体那会儿,每到春夏季节,生产队里就要把他俩抽调出来,专门负责水稻育种下秧。分田单干后,每逢水稻下秧时,仍然有农户把赵广富和大碗伯请到秧田去“指导指导”,事情完后,户主往往给他口袋里赛一包香烟作为感谢,礼数更大的还要请到家里吃一餐饭。坐上席,有肉有鱼,还有酒,尊贵得很。
神皇洲的大多数农户都是种的中稻,一个多月前就插了秧,此时田里的水稻都长到了膝盖那么深,唯独加入同心合作社的几家农户现在才开始育种,还兴师动众地把刚割完小麦的旱田改成了水田,引得不少人啧啧称奇,不知他们闹的什么新花样。更让人惊奇的是,年过七十,已多年没下过田的大碗伯,竟然也从江堤上的哨棚里走出来,拄着拐杖来到合作社几个农户的秧田里“指导”, 身边还跟着以前开麻木的小拐儿……
八月上旬,当神皇洲大多数人家的中稻快要收割时,同心合作社的南优1126晚稻也开始插秧了。
可就在耙田蓄水的节骨眼上,同心合作社的副理事长谷雨跟神皇洲的种田大户赵广富发生了争执。
神皇洲的地形东北高西南低,旱田在北边,水田在南边。神皇洲的人平时都把北边叫旱田区,把南边叫水田区。合作社几家农户新改的水田都在北边的旱田区,靠水渠那一边是赵广富的几十亩旱田,谷雨家新改的水田正好紧挨着赵家的棉花田,前不久才从赵广富手里要回来。要想从水渠里引水过来,就得从他的田里过。在神皇洲,这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事,可当谷雨雇人把抽水机都在水渠边安顿好了,赵广富却突然跳了出来,不让他们过水!
那会儿,谷雨和曹广进、胡嫂几个人正在用铁锹疏浚通往水田的过水沟。远远地,他看见赵广富冒着烈日,领着几个短工在自家田里给棉花间苗。由于耕得勤,施肥也足,赵广富家的棉花绿油油的,明显要比别人家的高出一截。谷雨正寻思着要不要过去和赵广富打个招呼,没想到赵广富自己走来了。
“谷雨,这是搞么子呢?”赵广富还没走近,声音先飘了过来。
“赵叔,亲自间苗呀?”谷雨扶住铁锹,站在田埂边,不无恭敬地把整个身子转向走到跟前的赵广富,“不是新改了几亩水田么,这不,马上要耙田蓄水了……”
“这么说,你们想从我田里过水?”赵广富耷拉着眼皮问。
“可不是么,也只能从您田里过么。”谷雨脸上堆起了笑容,并且从口袋里摸出香烟,递了一支过去。
但赵广富没有接烟。不知是阳光太强烈,还是根本就不屑一顾,他连眼皮也没抬一下,嘴里冷不丁冒出两个字:“不行!”
“不行?”谷雨刚浮现出的笑容一下子僵硬了,“为、为么子?”
“不为么子,不行就是不行。”赵广富干巴巴地说。
谷雨没想到,赵广富竟会如此霸道。赵广富这是对自己前不久从他手里把责任田要回来报复呢,他想起当年赵广富当着满月对自己的那顿羞辱,只觉得浑身的血液直往上蹿,身体像打摆子一样颤抖起来。他使劲控制着自己,但终于还是没有控制住,嘴唇哆嗦着,挥舞着手里的铁锹,大声喊道:“我偏要过!我就要过!”
谷雨的愤怒,不仅没让赵广富让步、松口,他脸上掠过一丝傲慢的笑意,鼻子里哼了一声,顺手抄起锄头,二话不说就开始往过水沟里填土。
赵广富这种轻蔑和挑衅的举动,彻底把谷雨激怒了。他果断地抄起铁锹,将赵广富填下去的土又掀了出来。
一个填土,一个掀土,眼看要发生更大的冲突,曹广进和胡嫂一前一后地赶过来了。
“老庚,消消气,”曹广进一把拉住赵广富手里的铁锹,说,“都是乡里乡亲的,这是何苦呢?”
曹广进跟赵广富同年,在神皇洲,同年出生的人彼此之间叫对方“老庚”,这样显得亲近。赵广富正高举着锄头把,若不是曹广进及时赶到,锄头说不定就要落到谷雨头上去了。虽然赵广富一向不大瞧得起曹广进,但也只好住了手。不过,由于刚才掀土过于用力,他不停地喘着粗气,再闹下去有点力不从心了。
年轻力壮的谷雨,自然不甘示弱,手里的铁锹虎视眈眈地对着赵广富,如果真打起来,吃亏的肯定不会是他。
随后赶来的胡嫂见此情景,倒吸了一口冷气。她赶紧把谷雨拉到一边,小声说:“好兄弟,你可不能犯糊涂,咱们不是有理事长么?再大的事也得马老师来解决呀!”
听了胡嫂这句话,正在火头上的谷雨想被浇了一盆凉水,头脑总算冷静下来。
胡嫂劝罢谷雨,赶紧往江堤边跑去找马垃。他来到那座带风车的房子,看见楼顶上的风车咕碌碌地转动着,大门却关得严严实实,连个人影子也没见到。胡嫂愣了下神,摇晃着胖敦敦的身体往江边跑。在猕猴桃园,她看加小拐儿在给果树浇水。小拐儿的伤虽然已经全好了,但他还是一直跟马垃吃住住在一起,越来越像一家人。胡嫂前两天还听谷雨说,小拐儿也想加入合作社,还说他已经找过赵广富,要赵广富把那几亩地还给他呢。难怪赵广富那么大火的,莫非是因为这档子事么?……
“小拐儿,马老师呢?”胡嫂用手背揩着脸上的汗问,“他没跟你在一起么?”
“早上他还跟我一起来桃园的,”小拐儿说,停止了给果树浇水。
“唉,我是问他这会儿在哪呢!”
“他说他去哨棚找大碗爹商量件事儿,刚走没多久。”小拐儿眨巴着眼,胡嫂惊慌失措的样子让他不知出了什么事。“出么、么子事啦?”
“么子事?快出人命啦!”胡嫂跺了下脚,转过身又往堤坡上跑去。
当胡嫂气喘吁吁地来到哨棚时,马垃正在和大碗伯商量把他家的猪栏粪作价卖给合作社几家农户的事。
按照马垃的设想,为了保证味道鲜,质量好,合作社种植的水稻一概不施化肥,全都用有机肥。眼看就要插秧了,尽管这几天农户们每天都在起早摸黑地到村里村外、田间地头、路边堤上拾粪,但还是距各家水田需要的农家肥差得远。马垃一寻思,大碗伯每年喂养几头猪,猪栏粪肯定多的用不完,何不跟大碗伯打个商量……
两个人坐在哨棚门口的屋檐下,一边抽着叶子烟,一边谈着事儿。
“大碗伯,如今农家肥比那些花费还值钱呢,每桶猪栏粪多少钱,您说个价,一分钱也不能让您吃亏……”
“垃子你这是跟我谈生意呢?”大碗伯磕了磕旱烟斗,满脸不高兴地说,“你莫忘了我还是合作社的人呢,几桶猪栏粪还要钱,你当我钻进钱眼里去哒?”
大碗伯粗声粗气地说。他心里很生气。马垃太把他当“外人”了。大碗伯想。自从马垃跟谷雨发起成立合作社以后,大碗伯似乎年轻了许多。他越来越在哨棚里闲不住,一有空就往底脚下那座带风车的房子和村里跑,对合作社的一举一动东充满了兴趣。前些日子,合作社旱田改水田时,他每天都要去工地附近溜达一会儿,一边溜达,一边就想起他年前是参加农田基本建设时的情景。那时候,工地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歌声喇叭声此起彼伏,一辆辆东方红推土机你追我赶,比电影里的战争场面还要壮观。比起那时候,同心合作社的“旱改水”工程不过是小打小闹呢!尽管如此,大碗伯心里还是感到一股按捺不住的兴奋。
哦哦,合作社,多么久违的称呼!听到这个词儿,大碗伯就想起了自己的青壮年时代。那时候,他年轻力壮,走路虎虎有力,说话掷地有声。每天有干不完的活儿,甚至吃不完的苦,可他从未抱怨过。为什么?因为心里始终有个“集体”,国家把他们这些泥腿杆子当做主人。他一生中最好的年纪都贡献给了那个“集体”,可是后来, “集体”不声不响地一下子就没了。他就是从那时候突然变老的。而现在,大碗伯觉得自己那颗已然衰老的心脏又开始像年轻时候一样有力地搏动起来。这一切,都因为马垃的那个同心合作社。这个垃子啊,多么像他的哥哥马坷,那个优秀的青年团支部书记。这么多年,大碗伯只要一想到马坷,心里就隐隐发痛。还有姚裁缝,一个多么好的女人,生了两个多么好的儿子!神皇洲有多少人穿过她缝制的衣服,可惜那么早就去世了,他至今还保存着要裁缝为他缝制的衣服。大碗伯浑浊的眼睛有些潮湿……
马垃显然无法体会大碗伯此时的复杂心情。“合作社是个经济组织,跟以前不一样咧,一码归一码……”他想对大碗伯解释点什么,但刚说两句,胡嫂火急火燎地赶来了。
听完胡嫂一番颠三倒四的讲述,马垃的脸色顿时阴郁下来。他二话不说,扔掉还剩一半的叶子烟,“我去看看!”说罢,拔腿就往堤下走。
大碗伯叫住了他:“等等,垃子。”
“大碗伯,您莫拦我,这是合作社的事儿,我必须出面……”
“事情没这么简单咧。赵算盘这个人,我比你了解,他不仅心气高,心机也深得很……”大碗伯嘴巴含着烟斗,思忖道,“今天这事儿,他一准是冲你来的,你俩要是顶上牛,闹得无法收场么样办?”
“那……么样办呢?”马垃一时没了主意。
“火头上的事最好先避一避,等风头过后,你再跟他好商好量么。”大碗伯摆出老资格贫协主席的架势说,“眼下这场火么,还是得我这个老馆子去救。他赵算盘不会不给我面子……”
马垃有点惊讶地望着大碗伯一下子显得高大硬朗的身躯,不禁想起了大碗伯壮年时的模样。
当胡嫂去搬救兵的时候,赵广富和谷雨像两头顶架的公牛一样在过水沟边僵持着,谁也没有让步的意思,但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动作,使矛盾更加激化。
赵广富毕竟上了些年纪,刚才闹腾时消耗体力太多,这时两腿还有些发软,索性放下锄头,横在过水沟的这一边,一屁股坐了下来;谷雨因年轻力壮,刚才那点闹腾对他不算什么,所以还是扶住铁锨把,稳稳地站在过水沟的另一边。两人虽然都故意别着脸没有看对方,但其实心里都在揣摩着对方,对于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情况,他们各自心里都没有什么底——也许一切都得等马垃来了才能见分晓。
像这样因过水发生争吵的事情,以前在神皇洲也不只发生过一次两次,但一般来说,只要用水的一方向过水的一方讲几句软话好话,或者实在不行,象征性地给对方赔偿一点“青苗损失费”——水从人家田间过,对庄稼毕竟会有些影响么——事情也就过去了,但赵广富今天的态度如此蛮横,就显得异乎寻常了……
实际上,在赵广富的心里,他早就盼望着这么一次发泄情绪的机会了。这股“情绪”在他心里已经憋了很长时间,特别是最近一段日子,他吃饭吃不香,睡觉睡不好,曹桂秀还以为他病了,不停地催他去吴道坤的诊所看看。只有赵广富本人清楚自己害的是心病。这个“心病”跟马垃有关。
自从谷雨把他家的责任田要回去后,赵广富就从这件事的背后看到了马垃的影子。他心里隐隐地产生了一丝不安。以赵广富对马垃的了解,他绝不相信一个吃过国家饭,在外面见过大风大浪的人回到神皇洲会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人,安安分分地过日子。如果这样,那他还是马垃吗?从那会儿起,赵广富心里就开始担心出什么事儿。有时候他去江边放牛,路过马垃种植的那片桃园一天比一天茂盛,或者半夜里起来解手,从屋后头远远地望见江堤边那幢带风车的房子窗口透露出的灯光——这么晚了,马垃竟然还没有睡,他除了拾掇那个桃园,就把自己关在那座房子里,究竟在干些什么呢?赵广富脑子里会冷不丁跳出这样的念头。这个人太特别了,让人觉得他根本就不像是神皇洲的人。实际上,他也算不上是神皇洲人。马垃和马坷,还有他娘姚裁缝终归都是外地人啊……
很快,果然发生了让赵广富,甚至全神皇洲人都惊讶不已的事情,马垃带着几个农户成立了一个同心农民专业合作社。起初刚听到这名字,赵广富几乎吓了一跳。几十年前,当他还是个半大小子时,神皇洲就曾闹腾过“合作社”,不过那时叫“农业合作化”。他家的十几亩好天就是从那以后变为集体的土地的。难道分到农户手里的责任田又要被“充公”了吗?听说这事当天,赵广富一夜没说好觉,第二天一早他就跑到镇上找到支书郭东生问个究竟。郭东生一听笑了,“广富哥,你莫瞎想,现在这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跟以前那个‘合作化运动’完全是两码事儿,根本不改变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制,只不过农户们自觉自愿联合起来,搞一些种植和经营活动。国家现在把这个东西当做新生事物在鼓励和扶持呢……”
郭东生的话虽然消除了赵广富的担心,但他内心里的疑虑并没有消失,反而像一个疙瘩在心里越来越大了。
不久,马垃带着那几家农户把旱田改成了水田。在赵广富这个种田行家看来,他们那是在瞎胡闹。在神皇洲,不,在整个江汉平原上,谁不知道种棉花比种水稻的收入高呢?这不说明马垃在庄稼活路方面完全是个外行么?可他不愿意相信有知识有文化的马垃会干出这种蠢事。这里面一定有自己不理解的奥妙。赵广富想,心里变得更加不踏实了。但几十年的历练告诉他,对一桩还捉摸不透的事情,不能毛糙,得沉住气……
但几天前发生的一件事,让赵广富再也无法“沉住气”了。那个以前经常在他家蹭饭吃的小拐儿竟然也提出把他家那几亩责任田要回去!前些天,赵广富就听说小拐儿跟一伙小流氓斗地主赌博,不仅输掉了三轮麻木,还被人打个半死,被马垃和谷雨抬回家养了好几天。这身上的伤还没好利索,就来找他要责任田。他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还会种田么?分明是要拿这几亩田加入到那个同心合作社去呢。赵广富的第一个反应,这肯定是马垃的主意。好家伙,这不是在挖我的墙角么?拉走一个谷雨还不罢休,又冒出一个小拐儿,接下去,不知道还有谁找我要田呢。但责任田是人家的,要回去天经地义,我能赖着不还吗?可如果就这样眼睁睁地由着人家把田一块一块都要回去,岂不只剩下自己家那几亩责任田了,那我还算什么种田大户呢?
赵广富越想越气愤。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一种莫大的羞辱,而羞辱他的的就是马垃和他的那个“同心合作社”。
一连几天,赵广富肚子里都憋着一把火。他觉得这把火越烧越旺,再憋下去,非把他憋死不可。无论如何,我得找个机会把肚子里的这股火的发泄一下,要不也太窝囊了。就在这时候,谷雨要从他田里过水。赵广富觉得,机会终于来了……
这会儿,赵广富坐在过水沟边,怀着一种报复的快感耐心地等待着马垃的到来。他倒要看看,这个见过大世面、见多识广的人今天怎么收拾这个局面,是委曲求全地同他说好话,还是像谷雨这个愣头青继续耍横,强行从他田间过水呢?如果是前者,他或许会看在当年跟他哥马坷在生产队搭档过的份上,让他们过水算了,毕竟,他只是想通过这发泄一下心里的气愤,提醒一下马垃不要把手伸打太长。我在村里好歹算是个有头有脸的大户么,岂能由着人在头上拉屎拉尿,连屁也不放一个?但如果是后者呢,赵广富很不情愿地想到了这一点。如果是这样,那我就宁愿拼个鱼死网破,也不能让一滴水从自己的田里流过去。在我的责任田里,哪怕是一只鸟要从这儿飞过,也得我同意才行。这道理到哪儿都讲得过去!
眼看快到中午了,炽热的太阳像一个巨大的火盆,高悬在头顶的天空,烤的汗珠子刷刷地往下淌,连眼睛也睁不开。赵广富和谷雨都有点撑不住了,扭着脖子不停地往江堤方向张望,两个人都在盼望着马垃早点出现。
但谁也没有料到的是,他们盼来的不是马垃,而是年过七旬的大碗伯。“社员”吐着红红的舌头一马当先地跑在前面。
看到郭大碗拄着一根杨树拐杖从田埂上走来,赵广富一时没有回过神来。这时,谷雨已机灵地迎上去,双手去搀扶住大碗伯,但对方一伸胳膊,把他的手甩开了,“我还没到老得走不动路的年纪咧!”谷雨脸一红,有点尴尬地退到田埂边,让他往前走。
赵广富愣怔了片刻,赶紧从地上站起来。对这个当过神皇洲大队贫协主席,而且比自己年长一辈的人,赵广富不敢有丝毫怠慢。但他原来针对马垃在肚子里反复了多遍的那些话,却一句也排不上用场了。他吭哧着不知说什么,只好习惯性地从上衣口袋里掏烟。他磨出的是一盒硬装的中华香烟。这是过端午节他女儿满月的“对象”李海军送的,他一直舍不得抽,但还是经常带一包在身边,碰上有头有面的人物,递上一只,也显得有档次。
但大碗伯对赵广富递上去的高级香烟瞧也懒得瞧一眼,就用手背推开了。他这才想起来,大碗伯只抽叶子烟的。
赵广富把那支香烟重新放回烟盒里,试探地问:“大碗伯,大热天的你这是来……”
“都快闹出人命案了,我能不来么?”大碗伯的目光在赵广富和谷雨两人脸上扫了个来回,最后落在了赵广富脸上,“广富,不管做人还是做事,你可都是神皇洲的一块牌子了,今儿是么回事呢?”
老贫协主席显然是话里藏锋。“这个……”赵广富一时回答不上来。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大碗伯是给马垃当挡箭牌来了。他觉得很恼火。摊上事情自己当缩头乌龟,让一个老倌子出面,这算什么英雄好汉呢?
“以前搞集体时抗旱,生产队之间还讲究发扬个龙江风格,现在虽说是个各干各的,也各家各户也要互相帮村,方便别人也是方便自己,自古以来就这样么……”大碗伯用从前给人调解矛盾时的那种口气说,“这水跟庄稼的命根子一样,断了水就等于把一茬庄稼都给毁了,谁忍心做出这种缺德事呢……”
大碗伯尽管没把话挑明,但赵广富觉得句句戳在自己脑门上。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但又找不出适当的话反驳。吭哧了半晌,才憋出一句:“大碗伯,不是我想跟他们过不去,是马垃他太过分了……”刚说了半截,他忽然觉得后面的话上不了台面,他能说谷雨和小拐儿要回自己的责任田是马垃支使的么?如果大碗伯反问他有什么凭据,他去哪儿找凭据呢?到头来,他在大碗伯眼里倒成鸡肠小肚了!
大碗伯见赵广富说了半截话忽然停住了,他尽管年纪大了,可心眼一点也不迟钝,似乎猜出了什么,就说:“广富,我不晓得你跟垃子两人有什么瓜葛,可庄稼活路是大事。节气一天也耽误不得,等过完水,我让他去找你把事情说开,乡里乡亲的,有么子疙瘩解不开的呢,嗯?”
话说到这个份上,赵广富没有了退路。他觉得自己像一头被人强按下头喝水的牛,再次产生了一种被羞辱的感觉。
这天晚上,赵广富连饭也没吃就上床睡了。其实他也没睡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跟贴烙饼似的,不时发出一俩声长吁短叹。曹桂秀以为是前些日子收割小麦,赵广富受了累,老腰病又犯了,就过来坐在床边给他捏腰,手刚挨到他就被推开了,火气很大地喝斥她:“一边去,让我清净会儿!”曹桂秀有点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老倌子这股邪火是从哪儿来的。她只好一边在胸前划着十字,嘴里一一边咕叨几句“上帝保佑吗,阿门”之类的话,蹑手蹑脚地走开了。
赵广富还在为白天的事生闷气。今天上午,他本想通过堵住过水沟,给马垃一次教训,可谁料到半道上杀出个郭大碗来,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让郭老倌像教育年轻人那样劈头盖脸地训了一顿。他这是倚老卖老,不,他这是拉偏架呢!赵广富愤愤不平地想。可我也是一把年纪了,在神皇洲不比你郭老倌的分量轻,凭么子像小孩一样地挨你训呢?你以为你还想过去那样当贫协主席么?要说,这眼下在神皇洲管事是你儿子郭东生,可你一条腿都快埋到土里了,还到处凑个么热闹呢?赵广富把所有刻薄的言辞都撒到郭大碗身上了。他觉得今天郭大碗出头给马垃出头,一点也不偶然。嗯,多少年前就是这样,他把马坷、马垃两兄弟看得像自己亲儿子一样。不,他对亲儿子郭东生也没那么亲呢!说一千道一万,还不是他跟马坷、马垃的那个做裁缝的妈暗里有一腿么?如果姚裁缝还活着,两个人现在只怕早就在一起过上了。赵广富的思绪飘得很远,一下子收不回来了。他想起当年在生产队当会计时,夹着一把算盘,寸步不离地跟在马坷身后,从村东走到村西,又从村南走到村北,生怕落后了半步。那时候,马坷不仅是生产队队长,还是大队的团支部书记,是大队贫协主席郭大碗一手一脚培养起来的。平心而论,从为人做事上,赵广富打心眼里佩服马坷,可他在心理上始终觉得和马坷隔得很远。如果要赵广富像马坷那样除了一日三餐饭,把全副精力动用在集体的事情上,他无论如何做不来。再说,他不像马坷家里只有一个弟弟马垃,他家里有父母兄妹好几口人,家大口阔,值得牵挂的事多着呢。退一步说,既便家里没什么牵挂,他能像马坷那样大公无私,一心一意地把精力扑在集体的事情上么?赵广富断然地否定了。他记得他爹说过,这世界上的事情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除了家庭和亲人,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就说这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小队,轰轰烈烈闹腾了几十年,闹得最欢时连每户人家多养几只鸡都不行。分田到户后,爹对他不无得意地说:“当时我就晓得,这样搞下去不会长久的。这不应验了吗?”可赵广富得意不起来。他的老搭档,那个把集体看得比自己性命还重要的马坷不在这个世上了!他觉得好可惜。如果马坷不是为了队里那点种粮丢了性命,而是活到现在,以他的能力,至少过得不会比郭东生差吧?不过,世事难料啊……赵广富的脑子里浮现出马垃的影子来。他觉得马垃比他哥马坷还要让人捉摸不透。你好不容易读书成了国家人,舒舒服服拿工资比干什么不好,却改行做起了生意。做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却忽然被抓进了班房,到头来竟然回到神皇洲,四十出头的男人,还形单影只的,身边连个女人都没有。按说这人跌了大跟头,该安安生生过日子了,可马垃现在的架势,分明是想在神皇洲闹出些大动静呢。你有本事就去外面闹腾么,外面的世界大得很呢,神皇洲就这么个比巴掌还小的地方,都是一些没什么见识的庄稼人,经得住你闹腾吗?闹腾就闹腾吧,可你跟我赵广富较什么劲呢?我招你惹你了吗?不管怎么说,当年我和你哥在生产队还搭档了那么多年,就冲这一点,你也不该挖我的墙角嘛……
半夜里,赵广富听到牛棚里传来牯牛哞哞的叫声,他想起来去给牛喂草料。每天夜里他都要起来给牛为一次草料的。可他刚下床,就觉得眼冒金星,身体摇晃了两下,差点儿栽倒在地上。他伸手摸了摸额头,滚烫滚烫的,在才意识到,自己真的病了。
赵广富在床上整整躺了两天,茶饭未进。曹桂秀把吴道坤请来,连着打了两吊瓶头孢,身上的高烧才渐渐退下来。第三天早上,赵广富觉得肚子饿了,就让曹桂秀弄点吃的来。这两天,曹桂秀白天黑夜等候守在他身边,连门也没出。现在见他想吃东西了,高兴得赶紧去厨房煮了几个荷包蛋,端到床边,用勺子喂他。两天没吃饭,赵广富大概是饿极了,不耐烦地从老伴手里把勺子抢过去,一口一个鸡蛋,眨眼的工夫,碗里的荷包蛋就全进到他肚子里去了。
曹桂秀看见他那副贪婪的吃相,一边为老倌子的病总算好了欣慰,一边心里却想着怎么安慰安慰他。
就在昨天,曹桂秀去闸上老万的小卖部买东西时,听胡嫂说了赵广富为了过水跟谷雨差点儿打架的事。她马上明白了老倌子病倒的原因。这个从小就到处流浪乞讨,连自己的出生地都不知道的女人,自从嫁给赵广富之后,在家对公婆孝顺,对男人温顺,在外面与人为善,从未像别的女人那样,动辄为一点蝇头小利跟村里人争争吵吵,是神皇洲出了名的好人。她以前信佛时,笃信积德信善,改信耶稣后,笃信爱人如己,在曹桂秀心里,这是同一个意思。她记住了《圣经》里的一句话:“当有人打你的左脸时,你就把右脸也伸过去。”她经常想,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她就得道成佛,死后能进天堂了。心里有了这样一份虔诚的念想,曹桂秀对许多事都看得很开。现在,他见老倌子的病总算好起来了,就忍不住想劝说几句。
“他爹,听说前天你跟谷雨吵起来了?”
“嗯哪。”赵广富耷拉着眼皮,有气无力地应答着。
“就为谷雨他家那几亩要回去?”
“就谷雨一个吗?”赵广富气哼哼地说,“连小拐儿也跟着凑热闹呢!”
“说来说去,还不就是为多种和少种几亩田么?”曹桂秀细声和气地说,“你都快六十岁的人了,早该抱抱孙子,享享清福了,还跟年轻人较个什么劲呢?再说,那田本来就是人家的责任田,他们要回去自个儿种不是天经地义么?”
“这个道理我懂。可他们把田要回去不是为了自个儿种,是要跟着马垃一起闹腾!”
“我晓得你说的是他们那个合作社。那几户人家老的老,幼的幼,每年种田的收入连肚子都填不饱,马垃把他们几个拢在一起,那是做善事呢,你管他们做么子?”
“他们不是闹腾到我头上,我才不管那个闲事呢!”赵世提高嗓音,说话又变得中气十足了。
“你心里就是不服老,眼看着别人红红火火的,像唱戏那样,担心人家马垃抢了自己的戏份……你这是跟自个儿过不去咧!要是真想跟他们比试,也找几个困难户拢在一起,相帮着……电视上怎么说的?对,共同致富。你愿意这么做么?”
曹桂秀不温不火的一番话,句句地点中了赵广富的“心病”。他很纳闷,平时言语不多的老伴儿,怎么今天变得这么能说会道,作为一个平时在家里说一不二的男人,这让他觉得面子上有点过不去。他想反驳几句,可又找不出合适的理由,只好一赌气,在床上重新躺下,不吭气了。
这当儿,大门口有人叫了一声:“广富哥在家吗?”
曹桂秀小声说:“好像是……马垃呢。”
“莫理他!”赵广富背朝着曹桂秀,闷声闷气地说,“你就告诉他我病了,这会儿还睡着呢。”
曹桂秀有些犹豫:“这不好吧?马垃是第一次上我们家呢……”
“反正我不想见他。”赵广富硬邦邦地说,毫无通融的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