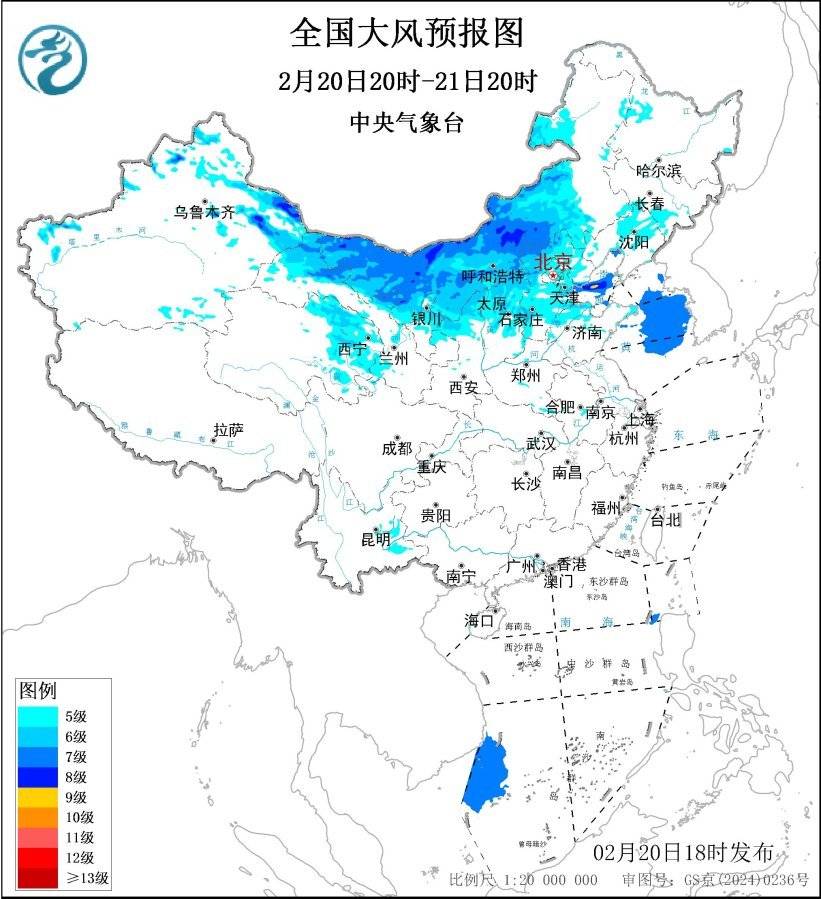古明浩:驳阎连科的日军糖果
阎连科又得外奖了,且还是美国人专设的华语文学奖,他秉持一贯的编故说事风格,于颁奖典礼上以《一个比世界更大的村庄》为题大放厥词,其中有一初尝糖味母亲的念日情怀:
“有位母亲七十多年来,无论是在电视上或是村人的谈论里,当大家看到或谈到中国与日本的仇杀历史时,那位母亲总会记起1945年,日本军队从中国败退时,一位穿着破烂、身上挂彩的日本士兵,拄着拐杖从口袋里摸出一颗小糖给了她。这位母亲说,这是她人生第一次吃到的糖,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种叫糖的东西,竟然那么甜。所以她终生记住了糖的味道和那张流血的日本士兵的脸,终生都渴望还给那个日本士兵一些什么去。”
解放军出身者的这段故乡旧闻極可能改编自藏族干部娜喜对解放军入藏的回忆:
“当时解放军就借驻在孤儿院旁边的小学里。我们常常会偷偷跑到解放军驻地“偷窥”。那群哥哥姐姐们也发现了我们,然后跑过来笑着跟我们这些脏兮兮的孩子打招呼。
由于当时我们听不懂汉语,与解放军哥哥姐姐们的交流完全靠手势,但我从他们的脸上感受到了温暖和亲切。他们不像那些官家、贵族家的人一般刻薄冷酷。一次,一个姐姐笑着递给我一颗彩纸包着的东西,示意我剥开放进嘴里。当我把它剥开放进嘴里的那一刻,那甜蜜的味道一下子刺激到了我的味蕾。后来我知道这是糖果,那个甜味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记住了,那颗让我甜了一辈子的糖果,是解放军给的。”
把解放军身上的糖果移花接木给日寇的手法,真不输莫言在《丰乳肥臀》中以接生特写来美化鬼子:
“一个白鼻梁上架着金边眼镜的日本军医跟随着他的长官,走进上官鲁氏的房间。军医皱着眉头打开药包,戴上乳胶手套,用寒光闪闪的刀子,切断了婴儿的脐带。他倒提着男婴,拍打着他的后心,一直打得他发出病猫般的沙哑哭声,才把他放下。然后他又提起女婴,呱唧呱唧地拍打着,一直把她打活。军医用碘酒涂抹了他们的脐带,并用洁白的纱布把他们拦腰捆扎起来。最后,他给上官鲁氏打了两针止血药。”
一次接生或一颗糖果能抵消屠杀三十万生灵的罪孽吗?
“2014年,我把村里这位母亲的心愿带到了日本去,从此有了更多的日本读者和老人,都渴望到这个村庄走一走,渴望见到这个村里的人。爱,是可以化解一切的。”
如此体贴日本人,难怪阎连科与莫言都跻身最受日人喜爱的支那作家之列。其实亲扶桑人士真想化解什麼的话,与其妄想一颗糖果的神奇效果,不如诚心面对一位尼姑的惨痛过去,那是温书林于《南京大屠杀》的控诉:
“1986年8月11日上午10点,南京,浓郁的梧桐树荫掩映着五光十色的橱窗,夏季时装大展销的广告吸引着对对情侣的目光,欢腾跳跃的迪斯科乐曲伴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这座举世闻名的大城市一如平日,生气勃勃,和平繁荣。我在一条小巷口下了公共汽车。与我同时下车的,还有一位身体瘦弱的老太太。她手里挎着菜篮。如果不是那像被人撕咬过的残缺的右耳,我也许不会注意她。她步履蹒跚地走了几步,忽然站住,定定地打量着路边的一棵古槐;瞪大了的眼睛里流露出恐惧和绝望,双手也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随即她怪叫一声,抛下菜篮,转过身没命地奔跑,还不时抓起路边的脏物向后扬去,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绝望的呼叫声。
‘老太太又发疯了,唉!’行人驻足,回头。
她弱小的身躯剧烈地摇晃着,终于栽倒在地,口吐白沫。
我和几个路人把她送进医院。两鬓斑白的H医生很生气地用听诊器敲着桌子问:‘是谁让她到老槐树那儿的?’
H医生告诉我,这位老人叫静缘,1937年南京大屠杀时,他惨遭日本鬼子蹂躪,地点正是那棵老槐树下。
我被极大地震动了,半个世纪的漫漫岁月,竟无法抹平她心里的裂痕。那该是何等的令人发指的暴行!
H医生把一本珍藏多年的英文日记拿给我时说:‘日本兵攻陷南京时,特莉萨•英格尔小姐正在教会医院工作,他记下了许多中国人被害的情况。1939年回国时她把日记给了我。’
我翻到了日记的第25页:
1937年12月15日
近日来,几乎天天有遭日本人强奸致死致残的中国妇女被送到医院。
上午11时30分,一个名叫叫静缘的13岁中国尼姑被抬进医院。她们的庵观早己被日本兵焚烧,师傅被强奸后,痛不欲生,跳入火中自焚,她侥幸逃出,蹲在一棵大槐树下,今天早晨6点被四个日本兵发现。他们轮流着发泄了兽欲之后,又疯狂地虐待她……三天之后她才醒过来,但精神已失常。”
当天入夜后,温书林一人徘徊长江边,面对大江东去逝者如斯,他感嘆:“时光可以流逝,受害人终离人世,然而历史无法忘却也不应该忘却。”并沉吟:
“作为历史的回顾,我们不能只有四大发明,古国文化,开元盛世,丝路花雨,也应该有南京大屠杀。”
“记住这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它会让我们更加明确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是的,南京大屠杀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要一代又一代去熟读它,读出我们的血性与应有的方向。别具用心,借一颗糖果做文章者太可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