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青年毛泽东:为何有的人年纪轻轻,思想深度却远高于常人?
1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二十四名青年,坐火车第一次离开长沙,走出湖南,前往祖国首都。
毛泽东为何要在那时去北京?
是因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当时恰巧毛泽东从一师毕业、面对着选择今后生活道路的关键时刻。
蔡元培、李石曾等在北京组织华法教育会,搞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当时湖南的政局十分混乱,政权不断更迭。
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都认为这是一条出路,蔡和森在北京和杨昌济商量后,去拜见北大校长蔡元培,两次写信催着毛泽东等邀集志愿留在法国的人员抵达北上。
8月19日,毛泽东到达北京,并同蔡和森把主要精力放在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上。
这时,湖南来到北京去赴法的青年已达五十多人,是全国来的人最多的省份。毛泽东他们发起这个活动时,谁能料到?困难重重。
但却没有一个人灰心丧气的。
当时毛泽东发起了一个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为他们筹措路费而四处奔走。
看着朋友们分别前赴各预备班学习后,毛泽东选择了留在北京。
与毛泽东一起同行的罗章龙考进北大预科,毛泽东却没有按照杨昌济的希望去报考。一方面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也与他一向擅长自学的主张思想有关。
而还有重要原因是,教育部规定,中等师范毕业生不能马上考大学,先要服务几年。
那时,他想:不进大学,总得要找一个立足之地,去获得生存。
10月,因杨昌济把毛泽东介绍给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外,便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
而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毛泽东每月薪资只有8元。但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是称心如意的,他可以阅读各种新出书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
而且北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大学人才荟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加上校长蔡元培的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生长扎根。
这种氛围,是毛泽东在湖南根本无法接触到的,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上天的恩赐。
他在这里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还积极参加北京大学的两个学术团体。
一个是1918年10月14日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这对他以后创办《湘江评论》奠基基础。
一个是1919年1月成立的哲学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以及胡适、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它的主要研究东西诸家哲学等。
毛泽东亲眼见到了新文化运动那些著名人物的活动,也结交了一些名人学者。他在湖南一师时就常读他们的文章,这时自然不放过当面请教的机会。
对于陈独秀,毛泽东是崇拜于敬重的,并认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后来回忆,在第一次到北京期间认识了陈独秀,并受到很大影响。
2
那时,他还在李大钊手下工作,李大钊的思想和行为自然给他以最直接的影响。
就在当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学说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李大钊是在古老中国用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
1918年11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亲自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说。
15日,李大钊的这篇演说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登在《新青年》杂志上面。
从而让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当然,毛泽东还认识了谭平山、王光祈、陈公博、张国焘这样一些后来颇为著名的人物,并与来自湖南的北大中文系学生邓中夏建立了真诚的友谊。
他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大,思想越来越激进。在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以后,也很受影响。
当时无政府个人主义派的一个代表人物是北大学生朱谦之,他比毛泽东还小六岁。两人却颇为投机,朱谦之经常去看望毛泽东,相互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
生活是清苦而紧促的,但北京丰富多彩的景色却给到他心理上的一种补偿,杨先生的女儿杨开慧,更给他以情感的慰藉。
这时,他的心情是复杂的,在北京,五彩缤纷的新世界一下子涌现到他的面前,他无法与它融为一体,对于突然接触到的新思想霎时间,难以消化。但这些让他打开眼界,迈出从湖南走向全中国的第一步。
而作为湖南青年赴法的发起人与组织者,毛泽东自己却没有迈出国门,许多前往法国的朋友都邀请他。
罗学瓒在信中说道:润之兄啊!你是一个有志的人,是我们同伴中所钦佩的人,你如何带一个头,权且努力于研究学问的事呢?
而他仍然选择留下来,他当时在一封信中明确说过:
他留在国内探索有许多好处,能快速看到更多翻译过来原本的书籍,这不仅不影响吸收西方知识,还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1个月后,五四运动就爆发了。二十五岁的毛泽东全力投入《湘江评论》的编辑工作,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他只好亲自代笔补齐。
那时正是严寒酷暑,蚊叮虫咬,一般人难以接受,而毛泽东总是挥汗疾书,常至夜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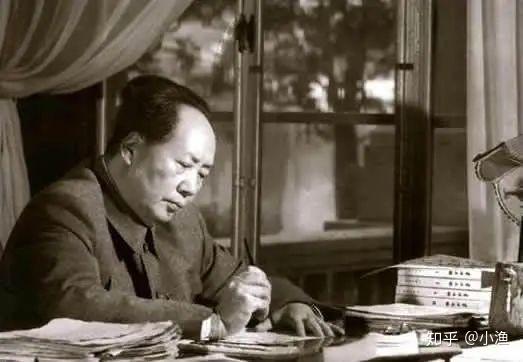
早上,太阳缓缓升起,商专学生易礼容来找毛泽东,他还未睡醒,易礼容揭开蚊帐,不料惊动一群臭虫,它们在他当作枕头的暗黄色线装书上乱窜,每一只都显得肚皮饱满。
就这种生活整整持续了一个多月,而毛泽东竟然为《湘江评论》写了40篇文章。
文章写好了,还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核对,有时还得亲自上街叫卖。
他生活捉襟见肘,修业小学给他的工资除吃饭外就没有剩余,他的行李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身上的灰布长衫和白布裤穿得也很破旧。
就在这种窘困生活中,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探索却进入最活跃的状态。
一个时代发生历史性重大转折时刻,引起人们思想上的冲击,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是平时多少年都难以想象的。
如今,在五四运动大潮的有力冲击下,他的视野顿时变得开阔了。他开始转向现实问题的研究,关注的焦点也转向整个社会的改造问题了。
从这以后,他再也不是只看重单纯个人的力量,而总是把自己置身于民众之内,依靠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这也是他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3
一个人思想上发生剧变,常常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蜕变过程,不是一步就可跨到的。
1918年6月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就曾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寄居岳麓书院半学斋湖南大学筹备处,踏遍岳麓山的各个乡村,想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
他们在这里自学,相互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自己挑水拾柴,用蚕豆拌和大米煮着吃。这一实验,很快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情中断了。
到北京后,毛泽东又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1919年3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日本的新村》,说新村“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这些,在青年中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就连新来乍到在北京的毛泽东也受到感染。
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
一种学理是否正确,最终要靠实践来检验。
如此以来,毛泽东对工读互助运动,既喜欢又茫然。他还需要继续观察它在实践中的效果。他曾到周作人的住所,拜访这位中国新村运动的倡导人。但可以推想也是以“新村”为主要话题的。
这个时候,毛泽东和李大钊接触更是频繁。他们多次讨论了赴俄留学和女子留学之事。毛泽东在1949年去北平前,还在西柏坡这样谈论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
由于李大钊的影响,他对布尔什维主义有了浓厚的兴趣,很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了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
他二月间给在湖南的陶毅的信中说:“即我,历来很懵懂,很不成材,也很少研究。
这一次出行,可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悟道一些人,思考一些事,觉得这几种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
3月10日下午,毛泽东又前往黎锦熙住处长谈到深夜,讨论改造中国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社会主义的问题?黎锦熙也主张中国的问题应该从“根本解决”入手。
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对问题如果不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和透彻了解,他是不肯轻易地作出判断的。
尤其问题越重要,你就越是重视。
他觉得,自己对于某某主义,某某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通过扩张运动的实践,再加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了解,他意识到,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
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
就连他自己,并未详细研究,因此如同“纸上谈兵”。那做人怎么能纸上谈兵呢?
然而,毛泽东,不太愿意去做详细研究。因为他不是一个只从书本里寻求真理的人,加上不喜欢脑子安静,他想做的是更现实的一些具体事情。
令他记忆犹新的是,陈独秀一次在上海,正同李达、李汉俊等筹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向陈独秀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征求意见。谈话中,自然也谈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回湘后,毛泽东就着手办两件大事,一件是关于当前的,一件是关于长远的。
关于长远的,他着力于新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把眼光主要地转向俄国。
毛泽东还准备在两三年后组织一个“留俄队”,他说: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诉你。为什么想要去俄国呢?因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
而刚回到长沙,毛泽东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易礼容等创办文化书社。
他说: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
可以看出,他已经把中国和世界的希望开始寄托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榜样上。
4
毛泽东这种近乎惊世骇俗的构想是大胆的,但又是空想的。
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思想上还存在的内在矛盾,又近似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所鼓吹的“呼声革命”。
只要有机会,他都还想试一试。
所以,你会发现毛泽东不仅敢于思考,也敢于去尝试去行动,也就是“知行合一”。
十一月下旬湘军总司令的赵恒惕,撕下伪装的狼皮。他们知道毛泽东是这场运动的关键人物,便制造谣言,说是毛泽东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还想捣毁省议会。
警察厅随即把毛泽东召去诘问,想借此造成一种高压的恐怖气氛。
毛泽东不得不在《大公报》上登出《辩证函》,郑重声明:“无论何人,不得于我之身体及名誉有丝毫侵犯。”
因此,警察没有再采取什么行动。但一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与“笑面虎”的自治运动,也从此一跌不振。
在无情的事实迫使下毛泽东冷静下来。他似乎也有些心里刀绞,告诉朋友,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11月下旬,毛泽东决定离开省城休息些日子,到了江西萍乡。
在萍乡,毛泽东又从行动回到了思考。原来设想的路走不通了,必须另外开辟一条新路。他一向是个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能够在探索中不断前进。
摒弃那些不符合实际想法的人。当你在一条路上走不通时,那就停下来构想或开辟另外一条新的道路,并且在之前的失败中总结教训与经验,去探索的路上不断精进。
11月25日,他在同一天给向警予、欧阳泽、罗章龙、李思安、张国基等新民学会会员写了五封信。其中三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总结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教训。
其中给李思安的信说:我们须“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这个“他们”,自是指谭延闿、赵恒惕等人。
你会发现,毛泽东总是扎扎实实地走自己的路,这是又一次的自我剖析和扬弃。
事实的教训,使他终于摆脱开对社会改良道路的最后一点幻想,使他更加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下这个决心实在是太难得了,一旦下定了决心,他再也没有回过头。
萧子升随后于1920年12月底回国,带来蔡和森于九月十六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
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的必要性,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并且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回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不难看出,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复,态度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
他说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表明他两年多来经历了一条多么曲折的心路历程啊。
40年后,他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革命不是哪里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我那时当小学教员,当时也没有共产党,是因为形势所逼,不能不干。”
而你要知道,在表明这种态度时,毛泽东也刚好27岁,可见他年纪轻轻思想深度已经远高于常人。
5
写到最后的话:
今天写下这篇文章,一来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二来是学习毛泽东智慧。三来,那就跟标题有关,向大家揭示这问题背后的本质。
我想,看过毛泽东的经历,想问问大家,什么是思考有深度?什么人被称为有思想的人?
而所谓的思考深度,绝不是你会说几句听起来有道理,富有哲理的话、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金句,也不是说我“理解人性以及看透人生啊”等。
而是你所思考的是所有人都会遇到,但极少数人能做到的人生终极命题,并且你思考的首要目的是自己带头或带领别人寻找到并踏上此项人生终极命题的科学道路。
当然,这个过程会异常的艰难,需要你大量阅读、实践、思考、反省,更需要坚韧不拔的勇气与始终如一的坚持。
那时,你想想,20多岁的毛泽东不仅要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在哪里?他还要思考中国未来的道路在哪里?等,而这些问题不管是对国家,还是个人而言,都属于人生终极命题的范畴。
希望我们在对于人生终极问题的思考上多下功夫,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并且可以坚持不懈的一路走到底。
最后想对你说:一个人的思想与眼界,来自于4个维度,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见过的人,干过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