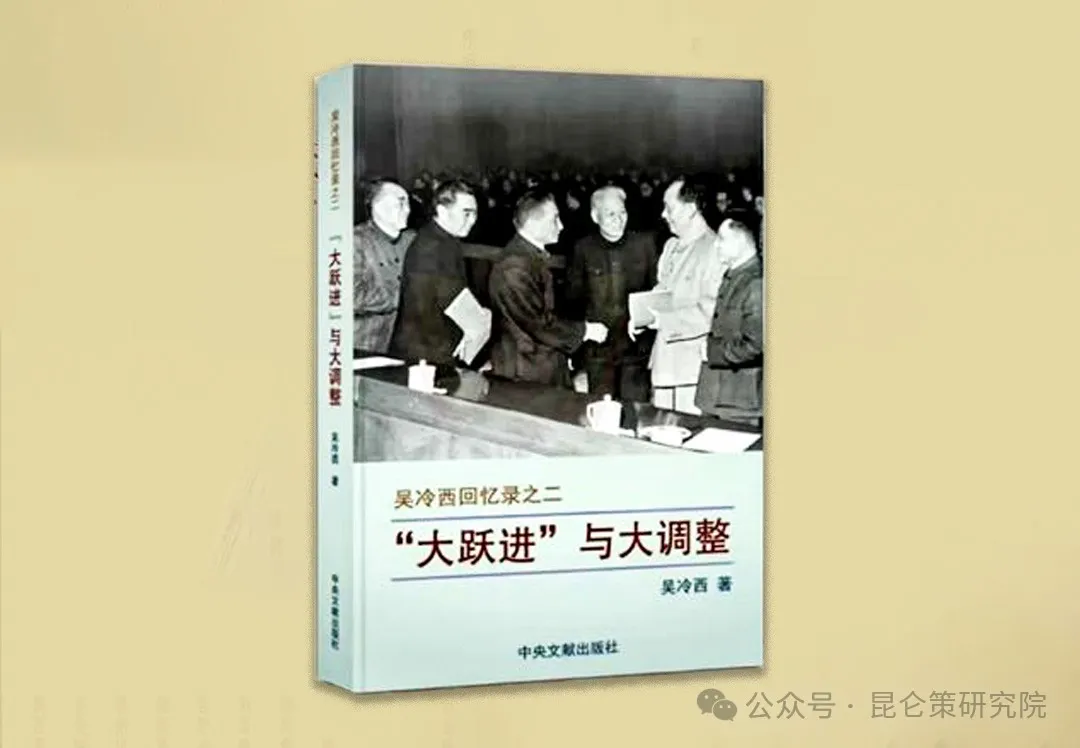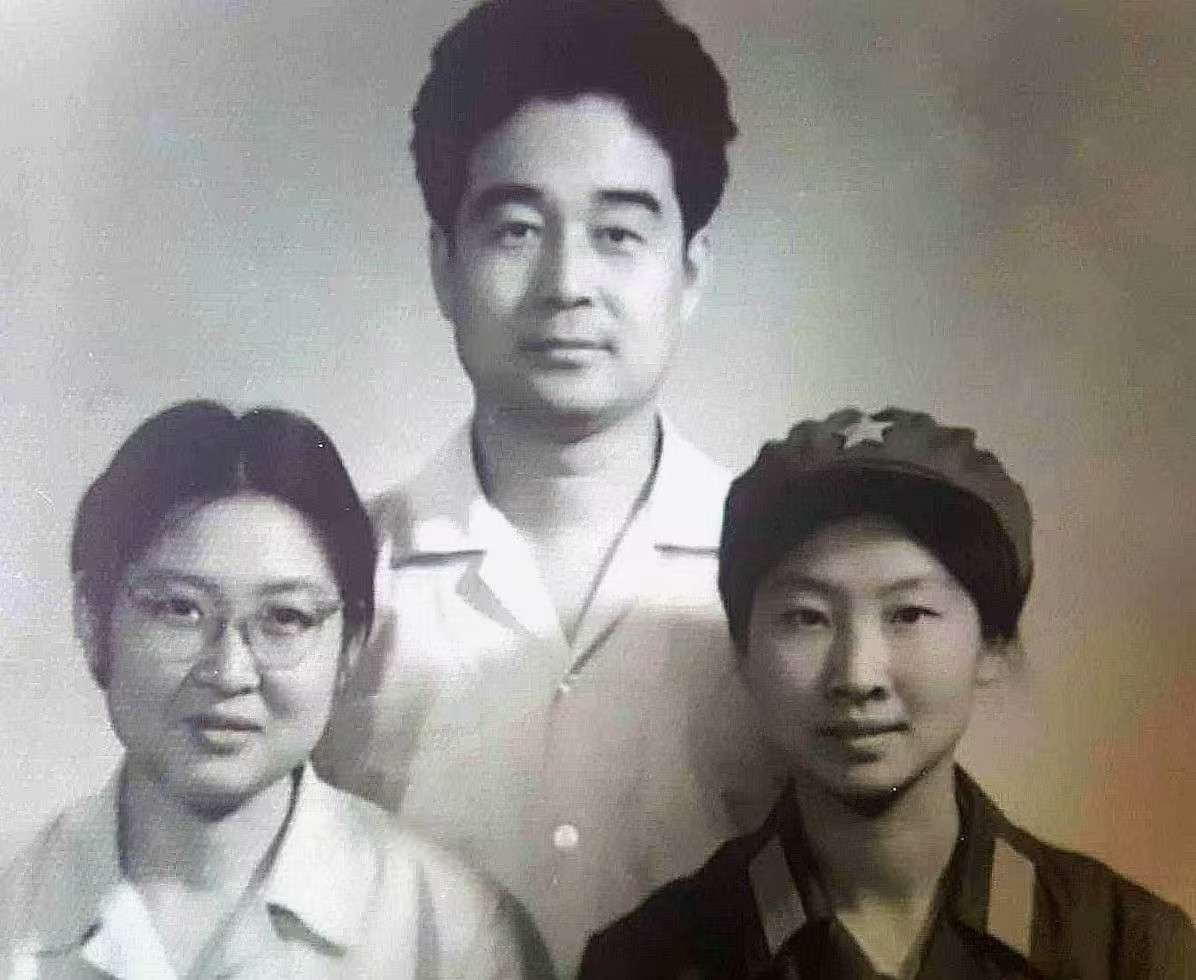三起杀妻案激起巨大恐慌, 无不指向一个诡异的真相
【导读】近期,某男子将妻反复碾压致死、孕妇泰国坠崖案被告人获刑、某热映杀妻骗财电影引发“分手离婚论”等消息密集出现,一时间群情激动。有评论认为,这是本已弥漫的焦虑触碰到一种精神结构的表征,即在这个全球经济停滞的时期,“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重新拥有了它的受众,普通人不仅面临难以保持财富的风险,有的甚至连与之同床共枕的最亲密之人都不再值得信任。
本文指出,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情绪,而如今整个社会弥漫着焦虑的味道。这种焦虑集中在住房、教育、社保、医保、财富、就业、消费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某些人提出焦虑成了一种时代病症。相比恐惧是针对特定危险的反应、会在危险消失之后恢复平静,焦虑则是由一系列并不连贯、看似异常的行动表现出来的,它既无特定对象,也很难缓解和消除。乃至有社会学家改写了罗斯福的名言,“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文化’本身”。
作者描述了这样一个意象:孤零零的个体困在一个强大的、充满风险的外部社会中,社会日益强化个人的恐惧和无时不在的焦虑感。问题在于,这并不仅仅限于自我关系的纠结,现实情况是每个人似乎都成为别人的威胁,每个人都不在其应在的位置上或关系中。作者认为,在这个转型与价值重建的时代,有必要寻求正确的秩序,这不只是指以爱对待原本用爱结成的亲密关系,更指在任何情形中可以安置自我、可以面对、可以转换的能力。
本文节选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9期,原题为《焦虑、恐惧与这个时代的日常生活》。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参考。
焦虑、恐惧与这个时代的日常生活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不少人会援用作家狄更斯的名句,“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显然是将21世纪社会经济突飞猛进的中国类比于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还有一些人则引用心理学家塞里格曼(Martin Seligman)的研究,将中国类比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情绪。20世纪50年代是焦虑的时代。这种情绪基调是弗洛伊德奠定的。他亲眼目睹了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在顷刻间土崩瓦解,而新世界又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当旧的价值体系被破坏,而新的还没建立起来时,那个时代就会充满焦虑和不安。”
无论是哪种类比,都承认了一个社会整体上的现实:这是一个令人兴奋,但又焦虑不安的时代。
确实,整个社会弥漫着焦虑的味道。几乎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不同程度和类型的焦虑,诸如这里所略微讨论的生殖焦虑、财富焦虑、对未来的焦虑等。一些人深深受困于此,出现各种各样的情绪问题,严重者导致抑郁症,甚至自杀。比这种个人性的焦虑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性的焦虑与结构性的焦虑,而这种社会性的焦虑可能集中在住房、教育、社保、医保、财富、就业、消费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以至于一些人提出,焦虑严格来说是一种时代病症,是一种现代性之忧。或者说,“中国人的焦虑是一种本体性的焦虑……没有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两元撞击中找到通向现代社会的共通环节”。有人也认为,焦虑是“发展的问题”,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必然会出现的情况和必须支付的心灵代价。另一个相似的观点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重要的外部原因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特殊历史阶段:一个转型与价值重建的时代。
焦虑、恐惧与风险
焦虑无所不在,应当如何理解?换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在焦虑些什么,或者说因为什么而焦虑?或许这里需要略微处理一下焦虑与另外两个紧密相关的概念的关系:风险和恐惧。
恐惧是由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感觉到的,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恐惧的感觉是主观的。但是,作为一种个人情感,恐惧在情感人类学里更多的被看成是习得的、社会建构的,是被文化、制度、习俗所模塑的一种存在。当遇到现实的、想象的、或者是被建构的可怕之物,恐惧便会出现。而“焦虑研究者——以弗洛依德(Sigmund Freud)、戈尔德施泰因(Kurt Goldstein)、霍尔奈(Karen Horney)三人为例——都同意,焦虑是一种处于扩散状态的不安,恐惧与焦虑的最大不同在于,恐惧是针对特定危险的反应,而焦虑则是非特定的、‘模糊的’和‘无对象’的。焦虑的特性是面对危险时的不确定感与无助感”。也就是说,与恐惧相比,焦虑中的威胁未必更强大,但是却在更为深刻的层次攻击我们。
按照罗洛·梅(Rollo May)的定义,“焦虑是因为某种价值受到威胁所引发的不安,而这个价值则被个人视为是他根本的存在”。一般来说,恐惧源于某种风险、危急的状况或可怕事情的发生。“个人体验到的不同恐惧,是根据他发展出来的安全模式而定的;但是在焦虑的经验中,是这个安全模式本身受到了威胁”。因此,从本质上说,焦虑与恐惧都是对于风险的应对机制,而焦虑是一种更深层次、更为本质性的恐惧。
与恐惧的情感“状态”属性相比,焦虑更被认为是一个思考的“过程”,一种对于不确定的、不可预期的、不能控制的事物的心理应对。“焦虑是基础的、潜藏的反应;而恐惧则是同样一种能力的表达,它只不过是以具体客观的形式呈现出来罢了。”也就是说,恐惧的身体体验可能更为直接和直观,而焦虑更容易以一种挥之不去的困扰的状态存在,甚至找到焦虑的根源也似乎更为困难。比如在恐惧时会出现心悸、发抖、颤栗,但是这种状态在恐惧之事消失之后可能就会恢复,但是焦虑往往可能是一系列并不连贯的、看似异常的行动表现出来的,比如,反复确认房门是否锁好,想去健身但在去与不去之间自我辩论自我否定,尤其是自我论证和自我纠结等等。因此,与恐惧相比,焦虑更难辨析、更难发现,但是对自我的威胁也更大。
这种更为深层的对自我安全模式的威胁的原因是更为复杂的,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分析中可能会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但是焦虑,从根本上说,往往源于无法实现某种期待:自我的期待、别人的期待或社会的期待。正如以“焦虑”为封面故事的美国《时代周刊》所定义的:焦虑源于我们对事情的期望与其真实状况之间的巨大差距。而弗洛伊德则将焦虑细分为:现实焦虑(自我与现实之间的冲突)、道德焦虑(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冲突)以及神经性焦虑(自我与本我之间的冲突)。这种内在与外在的冲突同样具有其文化面向。无论是自我与现实的矛盾,还是自我与道德的冲突,我们都害怕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出错,而这种错误又超出了自我所能控制的范围。正如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所提到的,中国的风水实践至少在某方面是源于焦虑:“焦虑往往出现在当一个人知道对他的状况起着生杀予夺作用的影响因素并不在他的掌控之中。在风水实践中的焦虑同时与主观不能控制的社会因素相关,也与无法预测、无法控制的自然力相关,比如气候”。因此,与恐惧真实存在的、大众想象的、或被认为存在的风险不同,焦虑的重心不在于风险,在于“我”对于风险的无法控制,在于“我”对于风险的(无法)预期和掌控。
显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更为关注的是恐惧、焦虑与风险的社会生产过程及其社会文化意义、以及尤其凸显的更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比如:恐惧可以是实现社会隔离和社会分化的原因和结果。封闭的城市社区的出现,贫富分化的加剧,正如塞沙·劳(Setha M.Low)的文章里提到的,城市空间的不断封闭和隔离会逐渐导致社区的消失,对自身和居住空间安全的考虑,既成为城市分区的原因,也会因为社区纽带的切断及无法预期与控制的犯罪率而成为居住安全恐惧的结果。而焦虑的社会意义生产,可以是围绕食品安全问题而生的科学知识与文化知识的冲突,是新的环境污染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出现,是艾滋病作为致命的“污名化”的疾病的文化建构、仪式对风险控制的失效、以及现代性话语对身份、地位包括幸福感“期待”的完美化趋向。
文化的恐惧
恐惧可能更多地被看作一种个人心理或社会心理现象,因此通常是心理学的研究领域。神学传统中对恐惧也多有关注,最为知名的当数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的《恐惧与颤栗》(Fear and Trumbling)。人类学视角下的恐惧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人类现象,对其研究可以成为帮助我们理解和认识“人何以为人”的一个进路。可以说,这也是在某种意义上重返经典人类学的终极关怀。
恐惧是我们人类生活中一个不可逃避的事实。甚至,恐惧不仅仅不可逃避,还有可能是我们有益的情绪、情感反应机制,并形成对可能遭遇的危险的预警机制。大卫·帕金(David Parkin)根据他的非洲研究经验也指出,不应简单地把恐惧看作异常,并认为其因此是可以消除的。
我们可以先简单看看个体心理以及生理层面上的恐惧。一般来说,在谈论个体的恐惧的时候,比较多的讨论是针对具体事项而展开的。比如,有人特别怕密闭的空间;有人又正好相反,害怕空旷的空间,因为那种无从定位自己,无从把自己放在一个具体的空间的感受让人心里发慌。再比如,高空恐惧也比较常见。当然还有对各种动物的惧怕,常见的如狗、老鼠、蛇、虫以及其它软体动物等。
除了个体层面的恐惧,很多时候的恐惧其实是被告知和因学习而来的。这种学习是在从小到大的日常生活中一直进行的。比如,父母会告诫子女,“这个事情不要做”,“离什么什么远一点”。事实上,我们个体层面上的恐惧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真的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很多的恐惧是被告知和警示的,是一种社会性、文化性甚至道德性的“告知”,比如“人怕出名、猪怕壮”。比如,克莱顿·罗巴切克(Clayton A. Robarchek)所论证的马来半岛塞迈(Semai)人对暴风雨和陌生人的恐惧。这种恐惧在成年人的示范作用和社会文化机制的强化下,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形成。同样的例子可能也包括我们文化中常常用到的“狼来了”的故事,以及俗语“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当然,最令人畏惧的其实还是人,尤其是敌人或陌生人。对于陌生人,我们通常会有天然的戒备,至少会有所提防的,因为总担心他会对你带来的可能的伤害。孔飞力(Philip Kuhn)的《叫魂》中就提到一点:对陌生人的恐惧。多数被当成有叫魂妖术的人,对当地来说都是陌生人:和尚、道士、外乡人。实际上,恐惧是一种在“自己人”与“外来人”的分类基础上产生的对于可能存在的外在风险的投射、甚至放大。简言之,对陌生人恐惧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种恐惧生产方式。
然而,这些讨论大多还是从恐惧的对象出发的,比如,害怕死亡,害怕敌人对我们的伤害,尤其是大规模的屠杀。我们也害怕饥饿带来的伤害,害怕自然的灾害,比如海啸、地震等自然灾害带来的伤害,所以我们会关注这些“恐惧的对象”。但是如今,如果注意观察自己的身边,就会发现“恐惧本身”(fear itself)成了新的威胁。
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就任的时候,讲了一句名言,他说:“唯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当时美国的社会正处在经济危机当中,很多人经受着恐惧。这个表述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将重点从恐惧的对象,转换到了作为情感反应的恐惧本身。而针对美国社会在911之后的风声鹤唳,社会学家弗雷迪将这句话转借表述为,“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文化’(culture of fear)本身”。
作为应对风险的情感体验,恐惧本身的文化性是多元且复杂的,我们对于恐惧的认知、体验,以及应对方式都会受到文化的影响。文化背景会给我们很多关于恐惧的信息,比如,看到某个图像或某个东西你是否应该害怕,应该害怕到什么程度,以及应该如何回应它。
焦虑的生产:失序和不确定
如前所述,如果恐惧是一种“状态”,那么焦虑更接近一种“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似乎可以作此推论:因为有不确定,所以恐惧,恐惧的程度一旦威胁到自我的价值与安全,则会引发焦虑。焦虑同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面向,焦虑什么、如何应对和掌控风险、焦虑对应的策略等,在不同文化中都会有所差异,正如同一种风险可能在不同的社会中引发的恐惧会有很大的差别一样。
无论是在个人层面上感知到的焦虑,还是社会结构意义上的焦虑,都有着某种对于失序或不在其位/出位(out of it splace)的强烈感知和反应。而这正好表明对于“应当如此”(ought to)的向往,对于一种秩序或在位(in its place)的想象。举例来说,手机和钱包在餐桌上一般来说不会是什么问题。但是,一双鞋出现在餐桌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不太干净,不应当,因为这触犯了我们对于一个事物应该在什么位置的认识,于是,鞋放在地上和鞋放在桌子上,给我们带来的观感是不同的。所以,失序源于我们对于秩序的期待。
涂尔干(E. Durkheim)和莫斯(M. Mauss)在《原始分类》里提出:人类有分类的天性,而分类的目的是给我们带来秩序感,秩序又是一种确定性。与我们这里的讨论关联起来的话,可以说是这样一个暗示:“我们怕是因为不确定”。延续这个思路,玛丽·道格拉斯(M.Douglas)在其成名作《洁净与危险》中以“洁净”为关键词展开了关于分类、秩序以及意义的讨论。
与失序相应的另一种解读是关于“不确定”的研究。正如学者常常论证的,在风险中存在着客观的和主观的区分,比如客观的风险可以是真实的威胁,而主观的则更多是由文化的观念及信仰所决定,甚至针对这种风险的知识和认知也是可以协商和改变的。基于这一本质,所谓的失序,既不完全是客观的,也不完全是主观的,而是在一个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出现的,这种“不确定”与人们如何确认、感知、理解和控制风险的一系列观念有关。比如说,我们常常提到的住房焦虑、教育焦虑,也许恰恰是住房和教育承载着我们认为的非常核心和关键的内在价值体系,以及相关路径的控制失败密切联系在一起。同时,这种不确定的增加也与我们对于稳定的文化追求有重要的相关性。
同样,有关焦虑的讨论也往往与理性化、现代化联系起来。斯宾诺莎认为“恐惧是一种不确定的痛苦,源自我们认为某件我们所憎恨的事,将降临在我们身上;而希望则是不确定的快乐,源自我们认为我们期待的好事即将发生”。因此,恐惧是一种心智的软弱,需要理性来克服。而克尔凯郭尔认为,“焦虑是人类在面对他的自由时所呈现的状态”,也就是说,恰恰是现代性对于个人意志、自由、意欲的强调,使焦虑成为现代生活的关键词。作为现代个体的我们,渴望的越多,越焦虑。或者说,在现代的背景下,获得所渴望之物的责任越来越集中在个体身上,这种理性个体选择、以及个体对自我命运负责的倾向也可能引发更多的集体焦虑。
另一方面,不同的未来观会对焦虑的生产也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比如在我们的文化中非常强调对于风险的预知、以及通过预知进而掌控未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良药苦口利于病”,这种鼓励忧思以及“防患于未然”的文化倾向,在面对越发不可控的现代社会,是否可能增加焦虑?
由于对于稳定和秩序的追求而加剧的不确定性,应该活在当下还是防微杜渐的问题导向,现代性对于理智及个人的追求,甚至过度竞争缺乏保障的社会秩序,都可以是大规模集体焦虑的底层原因。而在自我控制的层面,不确定性增加的同时,对控制能力减弱;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所导致的社会网络失效;传统的社会关系与冲突解决策略的失效;以及巨大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内在紧张与压力都可以成为焦虑产生及不断外显化的内在诱因。个体欲望的增加,世界越发失序,自我价值所受到的挑战有何能就是以焦虑的状态表现出来。
需要注意的是,正如阿兰·亨特(Alan Hunt)所指出的,社会的及历史的分析常常将焦虑作为应对社会变迁的机制来研究,但是不应该把焦虑简单等同于一种保守的或者怀旧的力量。从个体焦虑到社会焦虑、从社会焦虑到结构性焦虑,这一进路可以指向更为隐秘的社会现实,比如将内在的不安全感指向对外来人口的敌意,这种由焦虑引发的隐含社会现实,正是社会学、人类学可以不断去探索和发现的。
结语
在当下中国,焦虑已经成为一个广为使用的词汇,而对焦虑的讨论和关注则进一步强化了焦虑的味道。几乎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不同程度和类型的焦虑,诸如这一组文章选择讨论的生殖焦虑、财富焦虑、对未来的焦虑等。比这种个人性的焦虑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性的焦虑与结构性的焦虑,而这种社会性的焦虑可能集中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时代性特征。
中国当然一定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社会处境,“现代”作为一个首先为了表明自己与“过去”的不同的术语,也在试图彰显当今的不一样。换言之,当下中国语境中的焦虑固然有着其“特色”,然而如果将眼光(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放宽一些,就会发现,或许,恐惧和焦虑乃是一个人类生活中某种意义上的“常态”,并不是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一定是现代性的新产物。尽管我们也需承认,或许焦虑在这个时代有某种新的呈现方式,甚至也许在程度上有一定的增强。事实上,即便这一观点也并不是那么令人信服,因为每个时代的人都生活于其具体的恐惧和焦虑之中,这本身是无法比较的。
因此,重要的是去面对日常生活中被感知、讨论和体验的恐惧和焦虑,正如在对日常生活的研究中,需要着力强调日常生活的生成性,也就是在日常生活实践和经验(lived experience)中生成的存在感、身体感受及体验。只有面对无论是作为身体体验、还是社会经验所体会到的焦虑,我们才可能去把握这个时代所面临的焦虑,以及由此凸显的社会问题。无论是按照人类学家道格拉斯的暗示,还是社会学家贝克的明确提法,我们确实已经生活在一个十足的“风险社会”之中。似乎,恐惧和焦虑无法全然避免。
我们大概可以说,正是这样一个意象:孤零零的个体在一个强大的充满了危险或风险的外部社会中,它日益强化了作为个体的人的恐惧和无时不在的焦虑感。问题在于,这并不仅仅限于自我关系的纠结,现实情况是每个人都成为别人的威胁,每个人都不在其当在的位置上或关系中。或者说,作为群体的人似乎也彼此为敌,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竞争性的族群关系、地区关系或国际关系中,使得文明冲突不仅是一种学术观点,在一些地方和人群里更是一种立场和主张。进而言之,人这类物种类别,似乎同样也陷于一个“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陷阱里难以自拔,结果则是整个自然界似乎都在作出反抗和嘲弄,从食物,到土壤,到空气,到气候,到宇宙……
或许,面对这样的一种现实,一个古老的宗教智慧仍然有着其独到的意义:“爱中没有惧怕。”这里的“没有”不是有和无之区别上的,而是指一种可以安置、可以面对、可以转换的能力。换言之,在爱的关系中就可以面对恐惧。进一步,在正确的秩序中或许就可以免于过度的焦虑。个体的人之间如是,群体的人之间也如是,类别的人与其生活的世界也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