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卷空气是一种宿命——评《虚拟资本》(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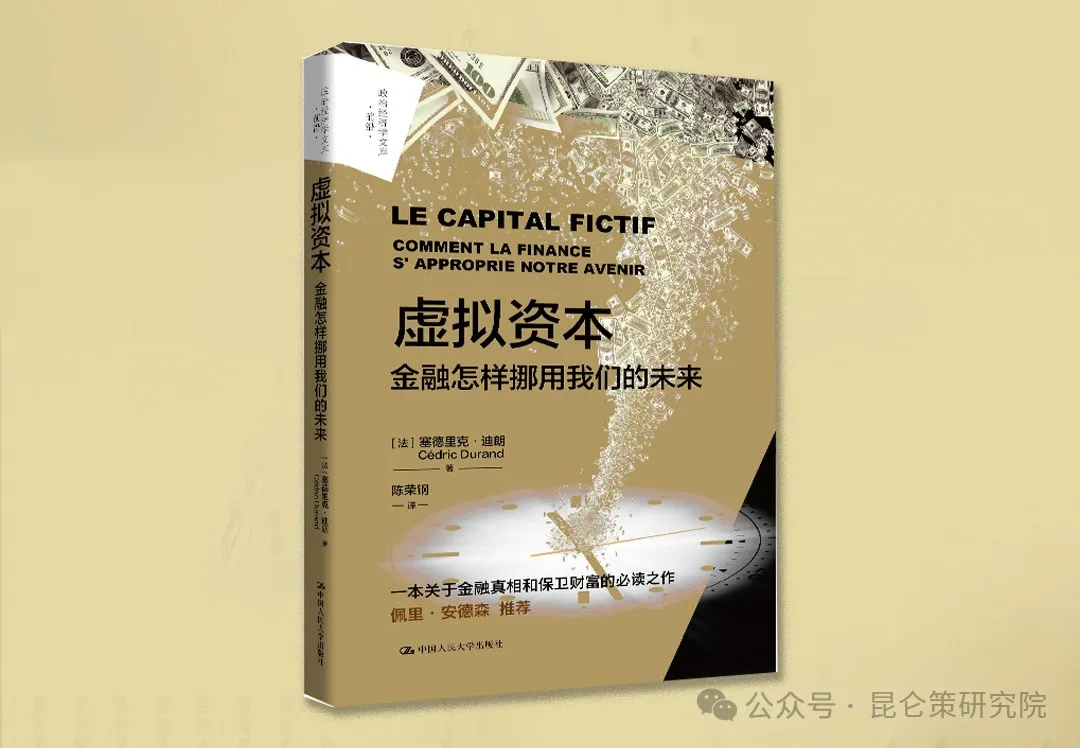
一、资本的使命
关于金融,有一个很常见的观点值得商榷。
这种观点认为,金融资本是好同志,但金融化不是好同志。金融化之所以不是好同志,就在于金融资本一旦“化”了,就会把虚无当作真实,金融的正常功能就被扭曲了。
若就实体经济的衰败而言,虚拟经济的嚣张跋扈确实彰显出金融功能越来越扭曲。
何谓“扭曲”?就是卷曲变形,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内卷”。
然而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在我看来,如果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赚钱)来把握金融化的功能,而不是从满足社会需要的角度来把握金融化的功能,那么金融化的过程不过是金融资本自身使命的扩展而已。
既然金融化是资本使命的扩展,那就很难说这是对金融功能的扭曲。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虚拟经济的做强做大究竟是金融功能的内卷,还是金融功能的外卷?
不过按照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便是金融功能的外卷,这一路卷下去,最终恐怕也难逃内卷的宿命。
何况马克思的积累理论业已揭示,不论是产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不论是外卷还是内卷,卷是资本的历史使命。
把虚无的空气当作真实的财富来卷,乃是虚拟资本的宿命。
二、“脱实向虚”的底线
但金融功能再怎么“卷”,也不能就此告别实体经济,只卷空气就ok了。诚如迪朗所言,“虚拟资产不断膨胀,虽然看似创造了无形的财富增量,但其最终价值仍需由实体财富来买单”。
所谓“由实体财富来买单”,乃是社会经济活动不能“脱实向虚”的最后底线。
那么,金融功能究竟应该卷到何种程度,才不会突破最后底线呢?
正如农业社会必须有90%以上的劳动用来解决吃饭问题,工业社会却只需要百分之几的劳动用于解决吃饭问题一样,到了后工业社会,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日益融入经济活动的背景下,用于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只能会越来越少,其占经济活动的比重只能会越来越低。
如果“实体经济”主要指的是“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那么,被科技发展和人工智能替代的工农业的劳动力又将何去何从,又将进入哪个产业呢?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对于经济活动“脱实向虚”的取向,马克思主义应该怎样做出辩证分析呢?
如何处理虚和实的关系,这个“薛定谔的猫”将长期困扰着我们。
三、马克思的视角
迪朗在前言中说,“金融化不是附带现象。它是一个触及当代资本主义组织方式核心的过程。”也就是说,金融化并非处于资本主义演进过程之外,而是一个内生于资本主义演化过程之中的事件。
迪朗在前言中还说,“虚拟资本代表着对尚未产生的财富的索取权。它的扩张意味着对未来生产的日益抢占。”窃以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为我们洞察金融化的本质,打开了一扇窗户。
我注意到,迪朗或许已经意识到了隐含在金融化背后的因果关系,因而他在前言中说,“本书的假设是:虚拟资本的繁荣也是悬而未决的社会和经济矛盾的产物。”
何谓“悬而未决”?其实就是马克思早就分析过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困境;何谓“社会和经济矛盾”?其实就是马克思早已揭示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由此引申出来的结论是:虚拟资本的繁荣不过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生产过剩的衍生物。
在这里,迪朗已经点到金融化的本质。然而不知为什么,迪朗到此也就戛然而止了。一直到该书结束,我也没看见他沿着马克思的这条逻辑展开旗帜鲜明的跟踪分析。
尽管如此,迪朗的方法论仍然是沿着唯物史观的进路展开的,由此得出的核心结论是:金融化并不是几个品行不好的投机商人搞出来的事情,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用迪朗的话说:
——“我们有理由认为,该职业(金融部门——引者注)对公共利益的贡献与它本身获得的天价报酬成反比。但诚如我们所见,用金融参与者的不道德行为来解释这场危机的任何做法都经不起分析。”
——“即使贪婪恶化不诚实在危机中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对复杂金融产品的狂热和金融泡沫也不能归结为个人道德或不负责任的问题。”
这是唯物史观的必然结论,而且可圈可点。
四、有点喜剧
有趣的是,迪朗观察到金融化的演进带来了一系列的深刻变化:“首先,它允许与资本所有权相关的收入(利息、股权、股息、股票市场的资本收益、房地产收入)增加;其次,它带来了金融部门薪酬的上涨。”
与此相应的变化则有点喜剧:“所有高收入国家的增长率都明显放缓。这一下降趋势与最富裕国家工业活动的下降以及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的下降同时发生。”
为什么说“有点喜剧”呢?这里我顺手举一个例子。拙文第一集《“再工业化”能拯救资本主义吗?》(首发于昆仑策,见【相关阅读】)被红歌会网转发后,有人在拙文下面跟帖:
——“唱衰资本主义没有70年也有50年了吧?人家衰弱了么?依然是世界主流,依然是世界老大。相反的唱衰者反而这种老调常谈像念经一样的文章写了几十年你们不累么?纯粹没事找事浪费时间,老百姓早就不相信你们这些人了。”
都老年妇女了,看看脸上风干的柚子皮,数数越来越多的老年斑,跟帖这位却非说资本主义是18岁的花季少女,还年轻得很呐——这不是恶心人吗?
就算涂脂抹粉又拉皮儿能聊以自慰,可是一上台面就露怯了。瞧瞧当今的“世界老大”输不起就直接掀桌子,坐在地上蹬腿儿耍赖,脸上的脂粉噗噗往下掉。这“世界老大”当的,还有脸说什么“世界主流”,就这怂样当什么老大,主什么流?主你个头去吧!
迪朗说“所有高收入国家的增长率都明显放缓”,这并非迪朗编造出来的趋势,而是有充分实证依据的客观事实。也就是说,迪朗观察到的相应变化是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
我建议,把迪朗概括的深刻变化与跟帖那位的“人家衰弱了么”做个比较,看看是不是“有点戏剧”?
五、凭啥欺负老实人
迪朗概括的深刻变化意味着,金融化允许与虚拟资本相关的收入增加,但却偏偏要欺负老实巴交的实体经济。怎么欺负实体经济?就是不允许与实体经济相关的收入增加。
这让我想起了马克思的名言:“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金融化偏偏要欺负老实巴交的实体经济,却不允许与实体经济相关的收入增加呢?
答曰:既然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那么不欺负你实体经济,又欺负谁呢?所以马克思说:“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
问题是,想欺负老实人是一回事,有没有实力欺负老实人又是另一回事。揭示虚拟资本欺负实体经济的实力,我想并不会出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预料,但却一定会出乎庸俗经济学的预料。
在《虚拟资本》的前言的末尾,迪朗给出了如下判断:“金融的日益复杂化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生产活力的枯竭与资本需求和民众愿望之间日益严重的脱节。”
迪朗的这个判断,其实已经很接近马政经预料中的答案了。至于如何理解这个答案,我将在后面给读者详细解读。
六、幸存者偏差
在书中,迪朗还提到了现代经济学最为常见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是:“危机更多是由错误的信念而非蓄意欺诈所致吗?各种基于经验的著作都支持这种观点。”
在我看来,危机究竟是错误信念惹的祸,还是蓄意欺诈惹的祸,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所谓“各种基于经验的著作都支持这种观点”,不过是“幸存者偏差”的结果而已。
迪朗虽然十分留意这个观点,却并未被这些错误信念绑架,所以他的问题导向始终聚焦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由此推论,金融的不稳定性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相反,问题在于允许和鼓励这种行为的自由化金融框架本身。”
(未完待续)
【注:拙文以《金融化的奥秘》为题,已发表于《天府新论》2025年第1期。如需核对相关论述,请以《金融化的奥秘》为准。】
【相关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