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望红:别让县乡的孩子“还没努力就已失败”

2015年初,正在华中科技大学读博的雷望红返乡过年,在和邻居家孩子的交谈中,她发现家乡的学校已不是当年的模样:学习环境变差、师生关系紧张、校园暴力问题严重,甚至出现了学生殴打老师的情况。
这些变化给了雷望红很大的刺激,也让从事乡村治理研究的她开始把目光聚焦在县域教育问题上。
中国的2000多个县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这些县乡的孩子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如何成长,关乎社会的未来。但是,县域在教育资源上远较地市、省城匮乏。这些年,在城镇化影响下,乡村学生不断进城,加速了乡村学校的衰落;作为县域教育“龙头”的县中,也在超级中学的挤压下黯然失色,优质乃至中上师资和生源不断流失……留在县乡的孩子们,或是被迫承受比之前更大的学习压力,或是不再相信“读书改变命运”。
雷望红如今已是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这些年,她和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杨华等学者领衔的华中村治研究团队,就县域教育问题在全国多个省份开展田野调查,在大量走访调研的基础上,合著了《县乡的孩子们》一书,聚焦县乡学子的困境与前途。
在这些学者看来,若县域教育全面溃败,多数无法走出县域的孩子将面临“还没有努力就已经注定失败”的局面。
近日,雷望红接受观察者网专访,就撤点并校、县中困境、县域职教、县乡学子和教师生存状态等问题分享她的观察和思考。
雷望红:
别让县域教育塌陷,要让底层家庭学生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命运
【采访/观察者网 王恺雯】
观察者网:《县乡的孩子们》一书提到,这些年国家不断向乡村学校投入资源,给予政策倾斜,努力弥合城乡学校之间的基础差距,但是,乡村学生仍在不断进城,乡村学校快速衰落。您认为问题出在哪儿?一些小规模的乡村学校学生人数跌至个位数,这种情况下是否有必要保留这些学校,还是应该集中资源办学?
雷望红:学校教育不只是资源投入,不只是硬件问题,更重要的还是软件。软件包含了学生、老师,还有这个学校的管理水平,以及师生的契洽程度。
现在的乡村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村庄空心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这其中至少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生育率下降,另一个是人口流动带来的,很多人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就业或在城市有定居能力之后,就会搬出村庄。村庄人口减少会导致生源减少,对于很多乡村学校而言,作为学校运行最基础因素的生源都没有办法保证。
很多人对乡村学校抱有“情怀”,认为要给留在村庄的学生最基本的教育公平,或者把乡村学校视为村庄的“文化之根”。但我们同样要思考的是,学生数量低于一定数值的学校,他们的学生没有几个同伴,无法接受正常的教育,连正常的社交都保证不了,这种“情怀”意义何在?对孩子来说,同辈群体是非常重要的,七八十个人的学校还有些生气,但有些学校只剩下七八个学生,班级都没有办法分。老师的积极性也没办法被激发起来,他们更多充当了“保姆”的角色。
乡村学校快速衰落,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老师留不住,大学毕业生不愿来。我们走访过很多乡村学校,校长跟我们说,一些特岗教师被分配到村小里,人家一看条件待遇太差,直接拎着铺盖走了。今年我在湖南某县访谈的一位乡镇初中老师,她每月基本工资不足2000块钱,加上每个月的班主任补贴、绩效和年终绩效,一年收入不到5万。小规模学校补贴相对多一点,但是生活不方便,这种情况是很难留住年轻人的,很多留在乡村小规模学校的都是年纪大的教师。
观察者网:《县乡的孩子们》对“县中塌陷”问题做了剖析,指出了超级中学跨区域“掐尖”的弊端。超级中学无疑给县中的生存带来了严峻挑战,但也有观点认为,县中的衰落是城市聚集效应的必然结果,超级中学只是加快了这个进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雷望红:超级中学的发展跟人口向城市集中有一定的关系,但除了客观的人口流动以外,超级中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使了很多“手腕”。
我在做调研的时候,发现很多县中是非常“痛恨”超级中学的。有老师对我介绍了湖北某重点高中在全省“掐尖”的细节:每年一到清明前后,这所学校就组织一次考试,考试时间不对外公布,而是一对一定点发消息。这所学校甚至会在乡镇中学(初中)安排一些老师做“眼线”,让他们和优秀学生对接。
其实对学生来说,能去超级中学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家长和老师也希望孩子去超级中学,但对于整个县域来说,原本要就读县中的优质学生被提前挖走,破坏了县中的生源结构,影响到学校发展的基础。学生内部往往会形成“比学赶帮超”的体系,这个体系一旦缺乏了最顶尖的力量,就会影响到下面的积极性。
超级中学还存在一个更大的隐患:“掐尖”之后,表面上我们看到学校对拔尖学生的培养越来越多,实际上却是“双输”。
我访谈过部分超级中学的学生,发现他们的压力特别大,这种压力主要是学业竞争带来的。因为他们原先都是各学校最顶尖的学生,聚集在一个高强度的环境下,大家只盯着成绩,把每个人都当做竞争对手,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对县中来说,这已经是县里最好的学校,不管是对县政府还是老百姓都要有交代,要有“业绩”。当地政府也会把压力传给学校,要求你每年必须培养出若干个上清北、985的学生,这就导致县中不断自我剥削、自我压迫,压迫老师和学生。老师要投入更多时间精力,把某些还不错的学生单独拎出来,进行专门培养,除了正常上课,还要另外补课。
很多高中都有等级化的分班制度,以前分两等三等,现在有些学校分四等五等,甚至还实施末位淘汰制,如果成绩在优等班里面是靠后的三名,就要淘汰到下一个等级的班级中,对学生来说压力很大。
家长的压力也大。现在县域高中的校外培训市场非常发达,因为孩子去不了超级中学,又想考上好大学,留在县中机会比较小,家长只能拼尽全力给孩子上补习班。一个班级只要有几个学生补课,其他人就会被带动起来。
高考是省内竞争,不管孩子是在超级中学培养,还是在县中培养,对全省来说,拔尖生的数量是一样的。现在的问题在于,因为超级中学的“掐尖”,使得超级中学本身和县中的压力都剧增,这对学生的成长是不利的,对创新人才的培养也是不利的。
所以国家不允许普通高中违规跨区域招生,还真是对县中的照顾。2021年我去江西某县调研时,当地已经禁止跨区域招生了,效果很明显。上面一禁止,下面其实也安心,因为很多家长是跟风送孩子出去的,这对家长的牵扯是非常大的,需要更多的经济投入,搞得家长学生都很紧张。
观察者网:现在很多人感叹“寒门难出贵子”,很多留在县中的孩子成绩和家庭条件可能没那么好。根据您的观察,县中的孩子大致是什么样的生活学习状态?近年来“小镇做题家”、“二本学生”等争论有没有对他们产生影响?
雷望红:学界对县中有不同的定义,有些认为县中就是县域社会里的高中,我心目中的县中是县里最好的高中。一般来说,能在高中阶段进入县中的学生,普遍成绩还不错,学习比较认真,心态也比较积极。我感觉“小镇做题家”、“二本学生”这种讨论对他们的影响不是特别大。
我在调研中观察过这些县中学子的状态,他们为了学习非常节约时间。比如在甘肃某个县中,学生在上体育课的间隙还拿着手抄稿背书。今年我在湖南某县调研,看到很多学生去食堂吃饭时带着“小抄”在背英语单词。
县中之间往往也存在很大的差距,有些地方县中办得很好,像甘肃某县是两个高中“分庭抗礼”竞争的关系,每所学校一年都能出1-2个上清华北大的学生。有些地方的县中就是整体“塌陷”,湖北某县中曾经20年没有招过一个教师,也没有进行过学校建设,非常薄弱。我和当地家长交谈,发现他们对县域教育都挺失望的。后来这所学校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有个学生考上了还不错的985大学。
观察者网:有评论认为,学校出一堆一本学生抵不上一个清北学生,这种观念在县域高中普遍吗?能否培养出清北学生是衡量一所县中的重要指标吗?
雷望红:确实存在这种观念。虽然也有一本率和本科上线率的考量,但很多地方更看重的是出了多少清北或其他985和211的学生。
学生考上清华北大,县里和学校对老师的奖励是非常多的,因为示范作用很明显。积极的一面在于,这能给县域民众信心,证明我这个地方有能力培养清北学生。这点很重要,如果你培养不了最拔尖的人才,老百姓包括教师本身都会对自己有所怀疑。
但这也会带来负面后果,因为培养清北学生意味着要把更多优秀资源和师资力量用在这些优秀的学生身上,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其他学生享受优质资源的权利。
观察者网:您认为振兴县中的关键是什么?
雷望红:首先是禁止跨地区招生,另一个就是给学校空间。
我对县中其实没有那么悲观,觉得县中还是有希望的,因为很多老师还在积极地做事,学生也很昂扬向上,就算机会比较少,大家还是在努力争取。要给孩子向上的光,他们看到了光,就会奋力拼搏。
观察者网:普职分流也是受到关注的话题。在县乡层面,这些年大家对职业教育的观念是否有所改变?您曾提到,中职学校中充满了失败主义的情绪,这种情绪有哪些体现?
雷望红:家长的观念我们没有专门调查过,我个人感觉,目前社会上对职校的看法没有什么转变。但作为研究者,我们自己的观念在发生改变,原因既有制度上的松动,也在于中职学校的探索让我们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职业教育其实在悄悄契合家长的诉求。
原先的职校普遍是培养职业人才,现在很多职校分成两块,一块叫技能部,一块叫高考部,高考部还是把学生作为普通高中的学生来培养,他们参加职教类高考,同样有机会上本科,学校也希望尽可能多的培养一些本科生。
但在技能教育这块,我们是比较悲观的。县域的技能教育其实很难办,第一是设施设备不齐全,也跟不上时代变化,有些学校用的还是上世纪8、90年代的机床,学生学这些有什么用?第二,很多学校缺乏技能方面的专业教师。老师都不够,又怎么能教好学生?不说学生想不想去对口企业就业,他的能力企业根本看不上。
我去过一些建设得还比较好的中职学校,即使在这些学校,技能班学生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学生的失败主义情绪体现在他们没有奋斗目标,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努力,整天无所事事,对未来没有什么期待,天天玩手机、谈恋爱,甚至打架、抽烟、喝酒。在普高,无论是县中还是其他高中,只要有高考目标,动力就会强很多。但在中职学校,尤其是技能班的学生,他就没有这种目标感,现在中职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的也非常多。
另一方面,很多中职学生不愿意去工厂,我们去调研时发现很多工厂根本招不到年轻学生,招来了也怕他们不安分。所以工厂宁可招中年人,虽然他们相较于年轻人没那么灵活,但更踏实。
观察者网:《县乡的孩子们》这本书还谈到了校园欺凌、青少年抑郁、网瘾等一系列县乡学子遇到的困境,您在调研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吗?很多城市孩子也会遇到这种问题,这些相似的难题,对县乡和城市来说有什么不同的含义?
雷望红:校园欺凌我在广西调研得最多,当地这种情况很普遍。我们从学生那里了解到很多校园欺凌事件,这种事要是和校长、班主任聊,一般是聊不出来的。
校园欺凌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比较极端、严重,带有残害性质,出现严重身体伤害的;另一种是小打小闹型,矛盾比较小。对于后者,我们的理解是:很多学生是闲得慌。
我访谈了很多学生,有的是被打过,有的经常打别人。你问他为什么要打人,他的理由是“我看别人不爽”。为什么看人不爽?因为别人戴眼镜、头发太长、说话难听、有点“娘”……总之各种理由,只要看人不爽,就去把他整一顿。当然,他打人也会看对象,处在班级边缘或者弱势的同学往往会成为受害者。
严重的校园欺凌则多数带有团伙的性质。过去一些学生在辍学之后变成社会青年,成为黑社会群体中的“后备力量”,这种情况现在少了,但在学生群体中还是会形成一定规模的团伙,对某些人进行欺凌。而且这种欺凌的隐秘性非常强,受害者一般来自弱势家庭,被欺凌后不敢告诉家长和老师,会默默承受。
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屡禁不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学校没有很好的震慑手段。过去处理校园欺凌是很粗暴的,老师甚至会直接打欺凌者,现在老师哪里敢打?以至于学校处理不了就去找派出所,但派出所又能怎么办?学生也没到触犯法律的程度。我们去派出所做访谈时,对方说我们不能拘留他们,只能吓唬,但这些学生也不怕吓唬,一般在派出所待几个小时就放了。
过去处理校园暴力还有一种方式,在国旗下做检讨,再严重点开除这个学生。但现在老师也不敢随便让学生公开检讨,更不敢开除学生。我在广西调研时,有个学生打架之后,被校领导批评了,这个学生就威胁学校,说要“带着兄弟们辍学”。这样老师哪里还敢严厉批评?学生一旦辍学,老师还要跑到他家里去求他回来上学。
现在校园“性欺凌”的情况也让我非常惊讶。我们去中西部乡镇调研时,发现当地有很多低端旅社,周末会有一些初中生去那里,其中一些女孩子是被迫的,我听说过的就有三起。也有对男孩的“性欺凌”。
关于青少年网瘾问题,县域社会可能比城市更加严重,这其中有着很大的城乡差别,就是家庭管理和介入能力不一样,其实校园欺凌也是如此。这些事如果发生在乡村,家长无论从意识上还是能力上,介入程度都比较小,有些事家长觉得无所谓,还有很多孩子是留守儿童,家长不在身边,无法感知到孩子面临的问题。
青少年抑郁方面,乡村的青少年抑郁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空虚,他们缺乏关爱。留守儿童中有一类群体特别容易出现抑郁,那就是家庭破碎的孩子,像父母离婚、“跑妈”家庭中的孩子或者孤儿。而城里孩子的抑郁往往是学业压力带来的,或是家长“窒息”的管理导致的。
我们一直强调县域社会的教育管理模式和城市社会是不一样的,县域社会缺乏家庭的支持,甚至有些家庭还会带来负面的作用。而城市的问题在于家长过度积极,家长本身就是竞争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搞得孩子压力很大,最后有可能被“反噬”。
观察者网:近期不少家长吐槽“课间圈养”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很多中小学要求学生课间不能下楼,“课间十分钟”被消失,这种情况在县域学校普遍吗?学校和老师在担心什么?
雷望红:这要看学校管理者的理念。我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有些学校确实不允许孩子下课出教室玩耍,主要是怕学生出现安全问题,一旦有这种情况,学校就会很麻烦。这其中也涉及到家校关系,学生在课间打闹出现安全问题,比如骨折之类的,明明可以通过保险来解决,但家长会来学校闹,就算有保险赔偿,学校依然要掏钱,还要牵扯很多精力。很多学校现在也不办运动会了。
玩耍是孩子的天性,但老师看到他们疯疯闹闹的就会批评,学生也不敢玩了。之前在湖北一所乡镇小学调研时,有一幕让我特别震惊,课间一排学生坐在墙角,不打闹也不说话。那所学校有大约100个学生,校园空间完全够他们玩,但那群学生就呆滞地坐着,都没有他们这个年纪该有的活力了。
观察者网:最近“为老师减负”的话题也引起广泛讨论。书中提到县域中小学非教学任务剧增,严重干扰了教学一线的工作,还提到“村干部有时候能力不行,老师对家长说话更有用”。教师在县域教育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是否因为传统文化赋予其的权威性,使其在非教学任务层面承担了更重的责任?
雷望红:全国范围内,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的教师,非教学任务越来越重是普遍的情况。县域学校教师任务重,是课程体系带来的,也和地区行政体系有关,和传统文化没有关系。
就县域学校来说,比较常见的非教学任务包括禁毒工作、防溺水任务、控辍保学等,还有一些迎检工作。
像是防溺水任务,原来是一日一提醒,假期变成一日三提醒,还有手抄报、看视频。看视频本来组织学生看就行了,现在专门搞一个软件,老师要一个个通知,统计家长的下载量,考核家长有没有看视频。考核方式有很多,既要拍照片或视频,又要在系统里检查,看完视频还要答题。我今年做调研的时候刚好看到一所学校在做“七不两会”的试卷,全校师生都要答题,但他们都是抄答案。这些工作已经背离了防溺水安全教育的初衷。
现在还有一些跟学校无关的工作,像督促村居民骑电动车带安全帽、医保缴纳等。很多县里要推广给老百姓的工作,都通过学校去做。
这些任务推到老师身上,部分原因在于老师文化水平高,动员能力强,关涉群体多,每个学生背后都有好几个家长。
我有个闺蜜在乡镇小学教书,在学校当中层干部兼班主任,她经常哭。年轻人承担得比较多,又不能拒绝,经常被搞到崩溃。
观察者网:有没有一种合适的方法为老师减负?例如负责教学的老师只教学,专门安排一些老师负责非教学任务?
雷望红:县域学校的师资力量普遍比较匮乏,另一方面,其实很多学校都存在忙闲不均的情况,压力主要集中在部分中青年教师身上。
我认为,为教师减负,需要强化教育管理,也要回归教育的纯粹性。对教育体制的设计要考虑社会诸多因素,但在教育运行方面要保证它纯粹性,要确保其核心目标是在进行人才培养,而不是去承担大量的社会性事务,不要把这些任务都压到学校身上。
观察者网:最后想请您总结一下,您理想中的县域教育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雷望红:我理想中的县域教育是具有自身独特的比较优势、能够与城市学校进行竞争的县域教育。
这里有一个竞争概念。教育一定是有竞争的,问题是在哪一层级进行竞争?目前来看,竞争的层级是在学生之间,因为县域学校已经没有办法和城市学校竞争了,各类学校之间形成了一种梯度结构,甚至是“鄙视链”,这就导致个体的压力非常大。越在中心地区,个体的机会就越多,越偏远的地区机会就越少。
我期待县域学校能够和城市学校竞争,这种竞争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尽管在资源上无法和城市相比,但县域学校有其他的长处,例如农村出来的孩子是不是能更勤奋一些?没有家庭力量的支持,能不能依靠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共同努力?没有极度竞争环境的压抑,是否可以保留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我们要保持县域学校培养人才的能力,如果这个能力没有了,县域教育就会塌陷。县域教育的核心功能是保证来自底层家庭的学生还有机会通过教育来改变命运,这一点始终没有发生变化。这也是我们写作出版《县乡的孩子们》的初心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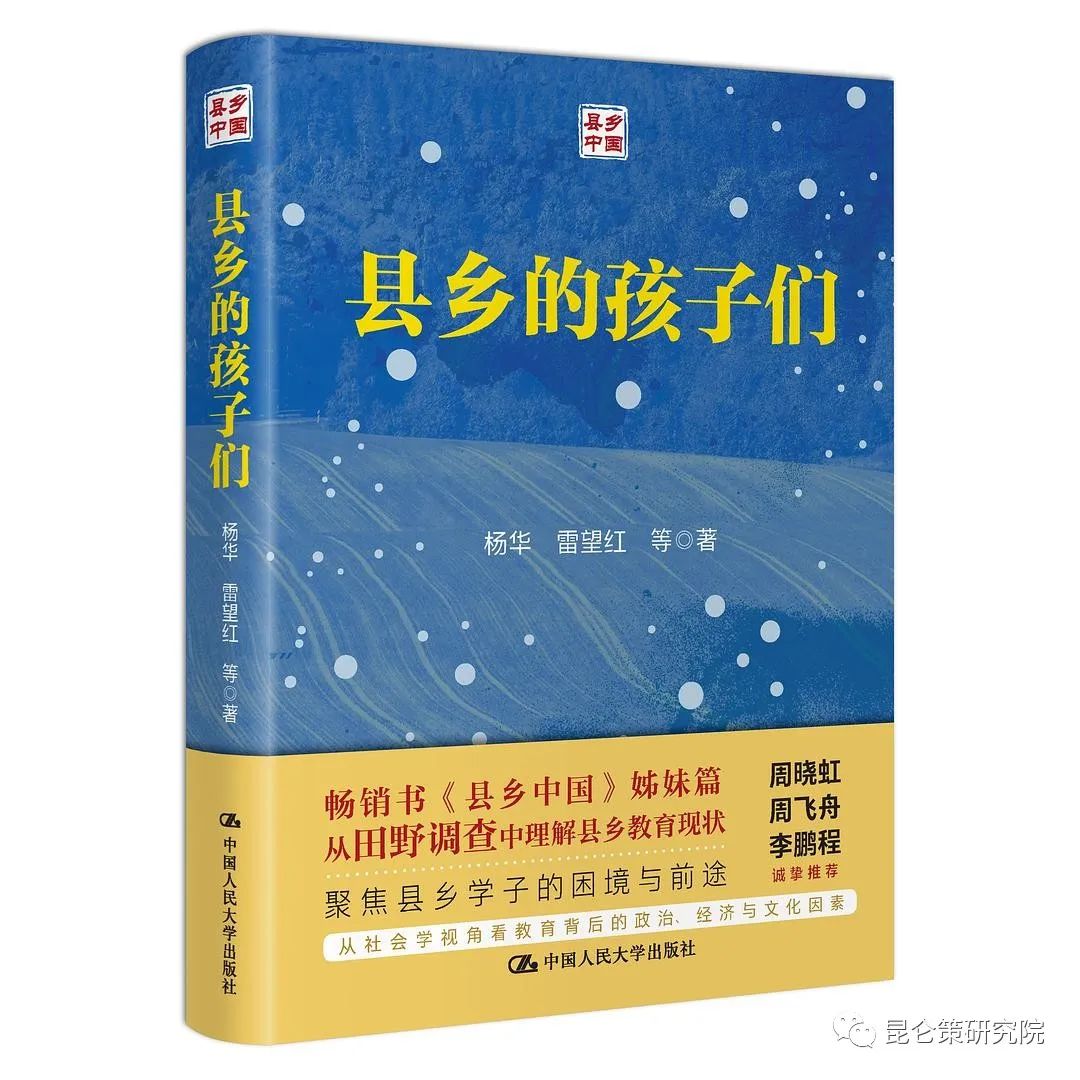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观察者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