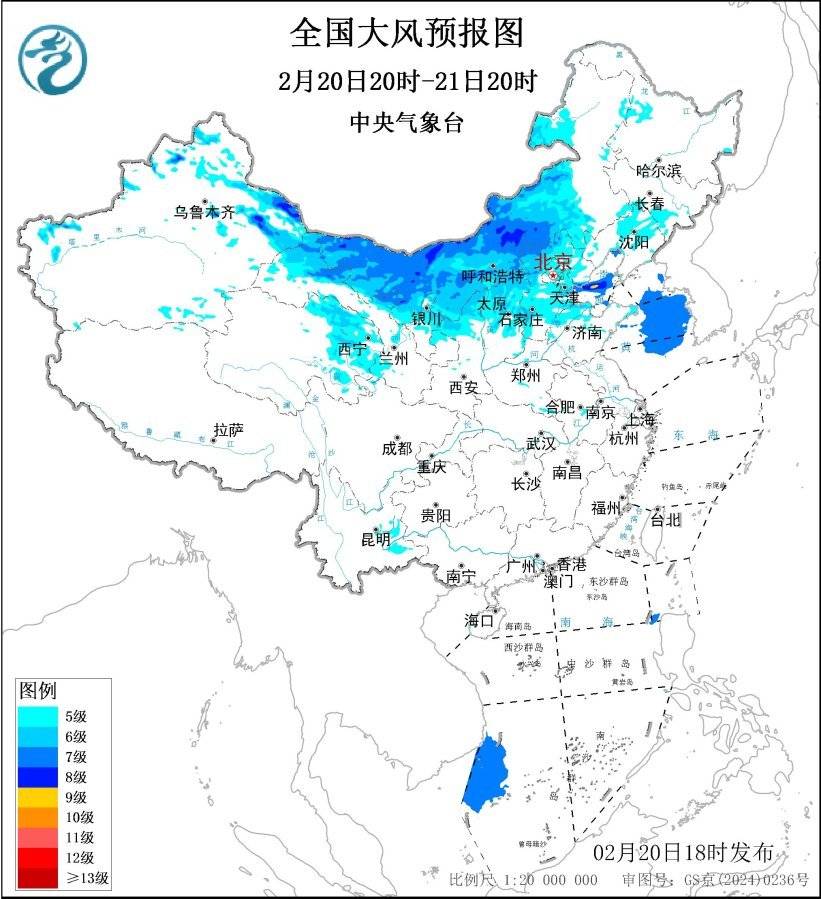对莫言文学的最后批判六 鼓吹莫言有辱斯文
尊敬是文人先生们,由于您对莫言的盲目鼓吹,已经造成了文化史上最大的笑话。对此您真的还浑然不觉吗?
比如,他关于“被秋田犬唤醒”的一段肉麻的描述:川端康成的秋田狗唤醒了我:原来狗也可以进入文学,原来热水也可以进入文学!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必为找不到小说素材而发愁了。从此以后,当我写着一篇小说的时候,新的小说就像急着回家产卵的母鸡一样,在我的身后咕咕乱叫。
从莫言的讲话看,似乎在《雪国》之前,狗从来就没有“进入文学”。亏得莫言还是蒲松龄的同乡,单单一部《聊斋》就有《野狗》、《义犬》2篇、《小猎犬》等专门写狗的小说。外国文学中写狗的小说不胜枚举,比如马克·吐温《狗的故事》、盖瑞·伯森的《雪橇犬之歌》、杰克·伦敦《野性的呼唤》等等,而《雪国》中的秋田犬只不过是个道具而已。
因为有了莫言的讲话,我们的文人们纷纷发言表示,“川端康成是我的老师。”纷纷赞美《雪国》却没有一句话说到点子上。秋田犬真的有那么神奇的魔力吗?为什么日本作家没有谁说过秋田犬对他文学创作的影响?为什么全世界也没有哪个作家说过秋田犬对他的影响?这只秋田犬单单影响、启蒙了一群中国当红作家,这究竟是个奇迹呢还是个笑话呢?
莫言的诗歌只不过是“亿万人民觉醒时,方知大侠善写诗”的水平。说他的诗歌笑话百出绝不过分。试问,莫言如此文学修养能够代表中国文化吗?
莫言小说充斥着对我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历史的仇恨,对我指战员的丑化、污蔑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请看,他是这样描写我党“大人物”的:
一乘双人小轿,抬来了一个大人物,十八个背着长短枪的士兵护卫着他……这个人是最有名望的土改专家,曾经在潍北地区提出过“打死一个富农,胜过打死一只野兔”的口号……神秘的大人物终于露面了,他坐在席棚中央,左手把玩着一块紫红色的砚台,右手玩弄着一支毛笔。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块雕刻着龙凤图案的大砚台。大人物尖溜溜的下巴,瘦长的鼻梁,戴一副黑边眼镜,两只黑色的小眼睛,在镜片后闪烁着。他那玩笔砚的手指又细又长,白森森的,像章鱼的腕足……人群周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岗哨都由县大队和区小队队员担任……大人物的十八个保镖,站在台子上,一个个面孔如铁,杀气逼人,好像传说中的十八罗汉。台下鸦雀无声,孩子们懂点人事的便不敢哭泣。不懂人事的刚一哭泣便被xx子堵住嘴……
大人物稳稳当当地坐着,他那两只黑眼睛一遍一遍地扫视着台下的百姓。人们把头扎在双腿之间,生怕被大人物看到自己的脸……大人物阴鸷的眼睛在母亲的脸上做了长时间的停留……大人物清清嗓子,慢条斯理地,把每个字都抻得很长。他的话像长长的纸条在阴凉的东北风中飞舞着。几十年当中,每当我看到那写满种种咒语、挂在死者灵前用白纸剪成的招魂幡时,便想起大人物的那次讲话。”
接下来,“大人物”指示枪毙了卖炉包的小买卖人赵六;在瞎子徐仙儿提出无理要求,无休止的胡搅蛮缠,且恶意编排、指控干部之时,“大人物摩挲着光滑的石砚,干瘦的脸上,露出了一股杀气”……“在土台子后边的空地上,大人物低沉地、快速地说着话,他的细长柔软的白手不时地举起,一下接一下地往下劈着,好像一把白亮的刀,砍着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就这样,“大人物”再次授意枪毙罪犯司马库(此人早已逃跑,不在会场)的三个无辜小孩。之后,“大人物的保镖们簇拥着大人物,呼呼隆隆地走了。”但司马库的小儿子突然逃走了,而两个女孩,因哑巴不忍,未杀成。(“大人物”竟下令其保镖蒙面枪杀了这两个女孩。——这是后文所述)
丑化人民武装的描写是莫言小说的主色调。一一摘录过于冗长,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灵药》一篇足矣。在莫言的笔下,八路军武工队长就是刽子手、强暴犯、滥杀无辜的恶魔。莫言的文风龌龊、猥琐,人物全是概念化的而没有任何内在的美学逻辑。
如此水准的小说可以代表中国文学吗?
想到了一句话:恋爱中的人智商为零。把这句话套用在鼓吹莫言的那群文人身上倒是非常贴切:偏见中的人智商为零。莫言严重限制了莫粉文人的智商。他们完全不明白,历史是无法因为几篇小说而发生任何改变的。后人再看莫言小说以及他关于小说言论时会笑掉大牙的!
2022年12月24日星期六
【文/颂明,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