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主义者失去话语权,苏联就开始坍塌了

一、“里应外合”:来自西方的信息战和心理战
1923年3月,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指出,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和党性,因此,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不妥协的进攻性斗争是共产党人的使命。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确保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全面传播,在列宁领导下,苏维埃政权在文化、科学、出版和教育等领域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查封了攻击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报纸,成立了一些传播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培养意识形态干部的科研和教学机构,如共产主义大学(1919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1921年)、党史研究会(1920年)、红色教授研究院(1921年)、列宁研究院(1923年)、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1年)等。
二战之前,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国外敌对势力始终保持着思想高压,在思想教育领域,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主流思潮占领了文化阵地。苏联人民相信社会公正,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面对二战前敌对势力的包围圈,思想理论上可谓“铁板一块”,坚不可摧。二战以后,硝烟未尽,冷战开始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积极进行军备竞赛的同时,也在准备心理战。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马当先,声称要“调动一切手段,包括精神手段,摧毁敌人意志”。他们广泛招募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利用宣传、互访、侦查、谍报等手段,进行大规模的心理战:通过援助,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利用民族主义矛盾,煽动社会不满情绪;散布政治谣言,丑化领导人的形象,制造对苏联制度仇恨,培养对西方的向往。
1948年8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20/1号指令——《美国对俄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这项指令揭开了一场本质为新型战争的序幕,信息成了武器,作战的目的是操纵和改变苏联的社会意识。战争的任务在于使苏联社会形成对周围世界虚假的认识,以利于进一步操纵并控制该国居民及其管理精英。
应当说,面对西方日益强烈的心理战,在战前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苏联组织了有效的反击。在军队系统,伏龙芝将政治工作视为“补充武器”。在军队总政治局下设进行心理战的机构和政治宣传委员会。贝利亚领导的安全情报部在对外侦查和反宣传方面也卓有成效。日丹诺夫在领导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思想方面,组织了宣传工作,有力整合了国内宣传机构,统一了思想,集中精神,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大量精力,也为后来的意识形态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美国当局认为,意识形态领域是与苏联进行战争的重要战场。为此而兴起的美国苏联学起了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先后成立了一些以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所,一些大学开设苏联东欧历史和政治专业的课程,美国外交政策的“智库”也将关注的重点转到苏联和华沙条约上。这些科研机构的研究活动形成了美国社会科学的一个特殊领域——“苏联学”,在西方也被称为“克里姆林宫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明显不同的是,美国苏联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无论是思想理论基础,还是研究对象和功能,均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总体说来,美国苏联学与美国政治紧密联系,在两种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斗争中发挥了以下三种主要功能:其一,在美苏对抗、两种制度的斗争中提供思想理论支持;其二,直接为美国对苏外交政策服务;其三,配合情报部门的反苏工作。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和西方的政策制定者和谋士们认为,思想战、信息战、心理战是美苏较量的有力武器。而欲取得效果,进而达到取胜的目的,必须“里应外合”。因此,西方专家非常关注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政治流派,并努力与之建立对话的渠道。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十分希望苏联社会出现一种“内部力量”,使这个国家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改革”。布热津斯基曾提醒人们注意多关注苏联的民族问题,认为民族主义在20世纪是强大的政治力量。如果克里姆林宫在非俄罗斯族群日益增强的民族自觉意识的压力下做出让步,那么通向和平演变的大门就打开了。为此,西方专家提出,必须破坏苏共对大众传媒的全面控制体系,在苏联提倡公开的政治竞争,保障选举的自由。共产主义的光环一旦褪色,它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俄罗斯学者谢·卡拉-穆尔扎在《论意识操纵》一书中指出,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败与其说是军事上、经济上的原因,不如说是思想上的原因。作者认为,正是由于西方对苏联社会的“文化核心”进行“分子入侵”,先是制造怀疑情绪,然后逐步否定社会制度的合法性,最后直至解体。他认为,这一过程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产生这种情况,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利西齐金等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一书中提出,苏联作为一个堪与美国匹敌的世界超级大国,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失败了,这是信息心理战的结果。信息心理战在内外力量的协同配合下,使苏联人民接受了假象,坠入空想,采取了大规模自我毁灭的行动,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

二、“放任自流”:舆论阵地拱手让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舆论历来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苏联解体首先发酵的就是舆论领域。当时苏联主要媒体脱离了党的领导,大面积出现丑化和否定党的历史的现象,把人心搞乱了。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戈尔巴乔夫有意纵容和雅科夫列夫背叛的情况下,苏共主动打开“闸门”,自愿放弃思想支柱,拱手让出舆论阵地,任凭反对派争抢。
1.报刊电视成为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阵地
1990年6月12日,《苏联出版法》正式颁布。该法规定,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合法化。该法明确提出,对大众传媒禁止进行书报检查;国家机构、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劳动集体,以及任何年满18周岁的苏联公民均可以获得出版登记资格。
在《苏联出版法》的鼓励下,一些报刊先后宣布“自主办报”,借机摆脱苏共和主管部门的束缚。一些苏共或国有的报刊纷纷“独立”,成为社会刊物或为编辑记者集体所有。例如,《论据与事实》周报是苏联“改革”以来至今在俄罗斯十分流行、发行量位居首位的报纸。它在1990年10月获得重新登记资格后,马上在头版声明:请读者注意,我们报头上原来标注的由全苏知识协会(相当于“科协”)主办,已经变为由记者集体自己主办。另外,1990年前后,《消息报》的编辑和记者为获得“财产和报纸的独立和自由”,和原所属的苏联最高苏维埃打得不可开交。最后结果却是掌握着权力和证据的最高立法机构惨遭失败,失去了70多年的报纸主管权。由此,《消息报》变成激进派、西化自由派的舆论阵地,而且一度为外资所控制。
此后,在办了登记手续的报纸中,苏共掌握的仅占1.5%。许多传播自由、激进思潮的出版物如《论据与事实》周报、《莫斯科新闻》周刊、《星火》画报的印数达到数百万份,而且常常是刚刚出版就被抢购一空。当时的苏联知识分子自嘲“虽然腹内空空如也,却贪婪、如饥似渴地呼吸这‘自由’的空气”。以《仇恨的面孔》批判美国而受到赏识的维·科罗季奇成为《星火》画报的主编,但这一时期笔锋一转,很快将刊物变成侮辱苏联军队、丑化历史、否定斯大林的阵地。苏联解体后,他“及时”移居美国,并受到隆重的接待和欢迎。
各种非正式出版物纷纷出台,苏共报刊舆论阵地逐渐被蚕食,反对派极力挤进电视台并且要求直播,以挣脱控制和剪辑,例如,几位年轻记者在苏联电视台创办政论性节目“视点”“第五车轮”,并要求现场直播。一时间,许多哗众取宠、造谣惑众的信息满天飞。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
包括一些学术刊物和书目在内,整个苏联历史都被冠以“极权主义”的帽子,被描述得一团漆黑。有人宣布,二战是苏联军队靠督战队才打赢的,因为士兵害怕背后的子弹。有人声称有确切的证据,说朱可夫曾经用尸体填平壕沟,让军队踩着通过。此外,宣扬色情、暴力的报刊纷纷出笼。一些本应保持严肃的报刊,包括莫斯科地区一些畅销的报纸如《莫斯科共青团员报》,也经常刊登色情、乱伦的内容,以吸引眼球。媒体和社会上要求开放妓院和卖淫合法化的呼声此起彼伏。有人甚至公开建议莫斯科市划出专门街道以成为“红灯区”。在市场和物欲的影响下,报刊、电视、电台以及出版社纷纷追求利润,忘却了政治责任,甚至失去了社会良心。苏联时期严肃的学术著作和科普队伍几乎销声匿迹,严肃的学术著作只能依靠内部印刷小范围交流。
苏共执政后期,苏共领导人一方面拱手出让思想舆论阵地,另一方面又巧妙地将苏共一些全苏性质的报刊和苏共中央级出版社变成传播自己背叛思想的工具。为配合“公开性”运动,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共中央决定出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由戈尔巴乔夫亲自出任主编。这样的刊物原本是向全党和全社会通报每次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的材料。然而,就是这样一份重要刊物,却有意回避现实生活问题,热衷于揭发斯大林问题,诋毁和所谓“反思”1917年以来的苏联历史的文章有时甚至占据2/3的篇幅。
2.苏共的党代会和人民代表大会也成为传播反对派思想的重要舞台
1988年以后,苏共领导人掀起了“民主化”浪潮,席卷苏联社会的政治选举热也强烈冲击着苏共思想根基和民众心理。例如,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通过了政治改革构想。苏联最高苏维埃根据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精神对1977年宪法中关于苏维埃体制和选举方法的条款作了重大修改,通过了《关于修改和补充苏联宪法(根本法)的法律》。1988年12月3日,《真理报》公布《关于修改和补充苏联宪法(根本法)的法律》。1989年春天,根据修改后的宪法,全苏上下进行人民代表差额选举。对于苏共反对派来说,此时的竞选活动可谓天赐良机:不仅有了染指权力的机会,而且可以合法地批判苏共,宣传自我。更重要的是将来有机会走上最高议会论坛,通过电视直播将自己的声音传遍全国。
在这期间,为了打败苏共,激进派人士周围聚集起强大的竞选班子,对竞选演说进行了精心设计。他们迎合民众心理,挑选民众最关心也是对苏共领导最不满意的问题,制定和阐述自己的“改革”主张。竞选开始以后,激进的自由民主派积极利用各种讲坛,一方面以富有鼓动性的演说,猛烈抨击苏共的错误;另一方面为激进的改革纲领勾画出一幅诱人的美好蓝图。他们高呼“反对苏共特权,实现‘社会公正’;进行激进经济改革、迅速提高生活水平;打击腐败、建立‘法治国家’等”。在这种情形下,谁“对当权者的批评愈多,讽刺指责愈激烈,谁选举成功的保障就愈大”; “谁许诺提高生活水平,人们就拥护谁”;“凡是共产党厌恶的人,无论是谁,都一定是英雄、是民主人士”。一些苏共异己分子乘机改换颜色,站至“自由化”的浪尖,振臂一呼,赢得了痴迷百姓近乎狂热的信任和崇拜。
竞选运动进一步加剧了苏共的信任危机,成为思想上和组织上否定苏共的开始。正如美国前驻苏大使、苏联问题专家马特洛克在其回忆录《苏联解体亲历记》中所说的,他看到苏共会议文件时“兴奋不已,新内容比比皆是……我从未在一份共产党官方文件中看到对诸如……权力分散、司法独立……等原则给予如此广泛的重视……有些提法似乎是从美国宪法中翻译过来的”。除了“社会主义”这个词外,文件与《共产党宣言》,甚至与《资本论》几乎没有一点儿联系。有关“社会主义”的那些苏联惯用提法也不见了。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些提法更接近欧洲的社会民主。
3.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舆论界的演变
积极的舆论能够为社会提供正能量,从而成为社会进步的推进器、民意晴雨表、社会的黏合剂、道德的风向标。相反,消极的舆论则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迷魂汤、分离器、软钉子甚至是社会冲突的催化剂。在苏联演变过程中,新闻舆论充当了马前卒和吹鼓手的角色,成了苏联社会分裂的迷魂汤和催化剂。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开始在报刊上攻击社会主义,神话西方。他们自傲于到过西方国家,认为西方国家完美无缺,西方街头的垃圾桶都那么漂亮。这些知识分子不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或社会学家,而往往是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报纸、杂志的编辑也很乐意发表这些人的文章。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苏联各级会议上差不多一半发言中都用过“文明国家”这个词。包括反对派代表在内,一再使用这个词,话里话外都是在断言自己的国家和第三世界各国不文明、有缺陷。争论问题时,只要不运用西方的材料,你的论据就不能被对方接受。神话西方使得苏联缺失了独立思维,丧失了自主评价能力,跟着西方亦步亦趋。
第二阶段,1988~1989年,报刊等舆论界的公开性运动进一步高涨。一些报刊积极宣扬重新评价苏联历史、否定十月革命,美化沙俄历史,间或流露出对西方露骨的崇拜。一些学者顶着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等头衔开始宣传:“苏联的道路不是文明发展的正路,‘西方文明国家’才是社会发展的榜样,应该在各方面都跟着它们走。”他们提出,美国芝加哥学派创始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说才是经济科学的基础。《文学报》、《莫斯科新闻》周刊、《共产党人》杂志等经常刊载一些专家的文章,号召抛弃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实现经济市场化;打碎苏共和苏联的官僚特权机构,搞政治民主化。
第三阶段,政治家来表演和实施。一些知识分子摇身一变,成为从政的“新贵”,也有部分原苏共的高级官员,他们看到了迅速市场化和快速私有化的好处,利用手中掌握的党和政府的权力,捞取了巨额的财富,实现了权力向资本的转变。结果是:在经济上,摧毁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行了私有化,造成了两极分化,用国家财富培育和扶植私人财团;在政治上,摧毁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推翻了苏维埃政权,推翻了共产党,建立起代表新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同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相对立的寡头“民主”政治。
苏共党内的叛徒故意拱手出让意识形态阵地,给反对派以宣传和传播自己观点的机会。看到苏共大势已去,苏共的异己分子则乘机扔掉自己的党证,违背自己的誓言,改旗易帜。自由改革派先锋人物、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授、人民代表加·波波夫,以及《共产党人》杂志编辑叶·盖达尔公开宣称:抛弃社会主义模式,移植资本主义,用最资本主义的方法改造俄罗斯。一度为叶利钦之后的俄罗斯第二号政治人物根·布尔布利斯宣称,“资本主义”是目前为止人类创造出来的虽不是最理想却是最好的制度。俄罗斯可以大胆采用,无需任何民族性的修饰。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后在就职演说中强调:“国家复兴有赖于人的精神解放、真正的信仰自由和完全的放弃任何意识形态的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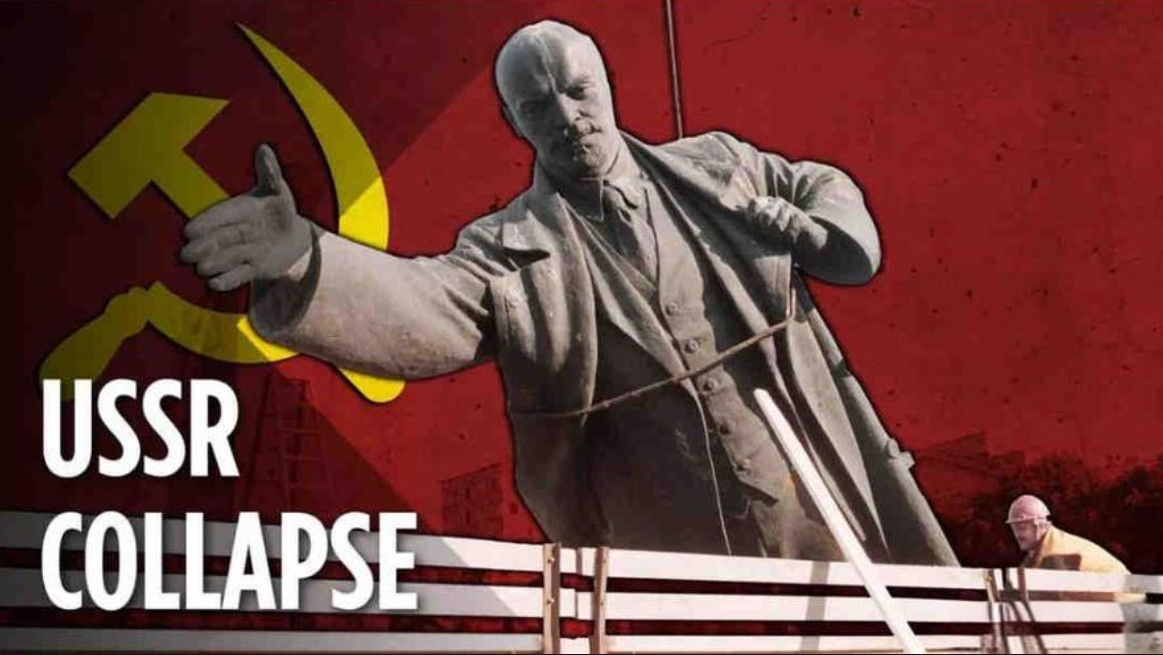
三、改旗易帜:舆论战下的全面崩塌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原则,主动放弃对新闻媒体的领导,取消报刊检查制度,在舆论导向上放任自流,任凭各种攻击、造谣和蛊惑人心的言论泛滥,导致苏共丧失了对主要媒体的控制权,苏共最终被淹没在反对派汹涌的声浪之中。苏共执政后期,在“公开性”运动的推动下,苏联的新闻舆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搞乱了社会的思想,瓦解了苏共的理论基础。
1.挖墙与凿船:“公开性”运动与“新思维”倡议
“公开性”一词在列宁时期便开始使用,初衷拓宽党同群众的联系渠道,更畅通地了解社会舆论和劳动人民的意见。1986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利用“公开性”的提法,将其与促进信息公开、民主化联系起来,视所谓信息公开、新闻公开为发扬民主、扩大批评的工具。
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对新闻媒体讲话时说:“造成党和国家思想和行动停滞不前的许多保守主义现象、错误和失误,与缺乏反对派、缺乏不同意见有关。在当今社会发展阶段,我们的报刊可以成为独特的反对派。”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又一次特别强调“公开性”问题。1988年初,戈尔巴乔夫对宣传舆论界提出,我们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此后,“公开性”运动一发而不可收。
在苏联“公开性”运动的指挥者和急先锋雅科夫列夫的支持下,一些作家、记者、政论编辑热衷于翻历史旧账,寻找污点,肆意放大。正是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公开性”成为瓦解苏联社会思想的突破口。“公开性”的矛头直接对准苏共要害和软弱之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扩大“公开性”成为暴露苏共和苏联社会消极面、阴暗面,以及宣扬西方样板的富足、民主和自由的思想运动。苏联舆论界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狂欢时节”。一些文人自由地抒发着感情,以解多年积藏在内心的压抑。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回忆,某些知识分子贪婪地呼吸着一股股自由新鲜的空气,反而暂时忘却了空空的货架和腹中的饥饿。雅科夫列夫对此十分满意,他写道:“公开性唤醒了社会,使它变得政治化。起初,就想不仅要把公开性用在出版自由上,而且把它看作是打开监督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活动的钥匙。我个人赋予它特殊的意义。实现这项任务,就能炸毁作为现行制度最重要支柱的官僚机关的保密系统。”
戈尔巴乔夫时期推崇的新闻和社会生活的公开化也被美国苏联问题专家视为赢得思想战的绝好机会。对此,俄共领导人根·久加诺夫深有感触,他在《全球化与人类命运》中写道:“在‘公开性’这一阴险狡诈的口号下对舆论进行密集加工,这一切在加速苏联和国际社会主义大家庭解体过程中起了首要的作用。巧妙地把我国人民和国家制造成虚拟的‘敌人形象’,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消亡和苏联的瓦解。”
在国内积极推行“公开性”的同时,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境内外积极宣传对外政策的“新思维”。1987年,戈尔巴乔夫所著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苏联和美国同时出版。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倡导“革命性的思维方式”,倡导以所谓全人类的价值代替“阶级观点”。戈尔巴乔夫一方面鼓吹“文明社会价值”和“核时代的文明”,一方面单方面主动对西方让步,这为他在西方赢得了奖赏,也从根本上颠覆了苏联舆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戈尔巴乔夫的“良好愿望”最后没能换来西方真正的回应,但他那些国际关系“新思维”的主张却有效解除了苏共思想武装,使西方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冷战、打赢了多年的攻心战。
2.从“历史翻案”到“社会复辟”
在“民主化”“公开性”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社会掀起了一股“反思历史”的热潮。这股反思浪潮延误了改革时机,使社会分裂,使苏共丧失了威望、失去了凝聚力,苏共被视为“历史罪人”,苏联制度成了“万恶之源”。
自1987年开始,到1991年苏共下台前后,苏联社会中的激进势力利用各种“历史问题”大做文章,有些做法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他们疯狂地揭批斯大林,提出“十月革命是一场少数人制造的超恐怖的革命”。列宁也成为被讥讽和批评的对象。例如,经济学家瓦西里·谢留宁在自由派杂志《新世界》上撰文说,苏联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并非是从斯大林时期开始的。斯大林的压迫早就有其方法论的先声,而这个粗糙的方法论,始作俑者正是列宁。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争论。后来思想舆论界开始认为,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从一开始就把俄国引向了悲惨的命运。自由派媒体则开始鼓吹,宣扬革命前的俄国已经在朝着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发展,之后人为地被布尔什维克掌权势力所阻止,随后的社会主义试验更是把它导向了错误的路径。这里的潜台词就是:如果能够推翻苏联共产党的统治,俄罗斯就会重新回到它革命前的所谓“常态文明”中,意即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
1991年“8·19”事件过后,莫斯科等地矗立着的各种各样的列宁塑像,除莫斯科十月广场上矗立的等少数外,一夜间,或被推倒,或被打碎。其他与苏共和社会主义有关的历史象征也遭此厄运,博物馆中陈列的展品也被搬出。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改名”风潮。城市地名、街道、刊物纷纷改头换面,竞相丢弃和原苏联、苏共或社会主义有联系的名称或象征。一些原苏共领导人急忙扔掉“党证”,以示“洗心革面”。一些旧势力纷纷回国,末代沙皇遗骸问题被媒体追踪,后来叶利钦亲自主持国葬。同时,自由激进势力大肆叫嚷“把列宁的遗体从红场迁走”。历史沧桑,星移斗转。苏联人民的理想破灭,人们心中的“偶像”坍塌,社会思潮极度情绪化。否定历史引起社会思想的混乱,社会犹如失去了“路标”,加速了苏共意识形态崩溃的进程。
3.文学的解禁与舆论的狂欢
1987~1988年是苏联社会思潮和舆论导向发生剧烈转变的一年。据戈尔巴乔夫自称,“公开性”不仅意味着打破禁区,“公开性也意味着重新放映‘束之高阁’的被禁影片,公开发表尖锐批判现实的作品,在国内再版几乎所有‘持不同政见者’和侨民文学著作”。
1987年是“解禁文学”最为流行的一年,这一年发表的这类文学作品比重大、数量多、反响强烈。其中包括作家布尔加科夫1925年创作的《狗心》,普拉东诺夫1930年创作的《地基坑》,伊萨科夫斯基40年代创作的长诗《关于真理的童话》,雷巴科夫1966~1983年完成的《阿尔巴特大街的孩子们》,等等。1987年苏联作协代表大会还决定为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彻底平反,并决定出版他的作品全集。不仅是文学,电影戏剧也如此,几十部被禁影片得以放映。1987年7月,莫斯科电影节闭幕式上放映了长期被禁的影片《政委》,影片呈现了情绪激愤的群众与红军发生严重冲突的经过。此后,一些电视台开始放映描写阿富汗战争苏军伤亡和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的纪录片,在社会上引起震动。苏联国家电视台开设的一些政论专栏如“第五车轮”“午夜前后”“视点”等言辞激烈,思想激进。由几位年轻的记者创办的“视点”节目为争取摆脱约束还积极争取直播。“视点”节目内容充满叛逆色彩,善于煽风点火,蛊惑人心,一时间社会影响巨大。
4.从“反特权、反官僚机构”的口号到瓦解苏联、摧毁国家制度
在许多改革和经济问题争论过程中,苏共“特权”问题和“官僚管理”成为众矢之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进行了3年多时间,经济方面丝毫不见成效,各项事业日渐衰败。社会舆论认为,“特权阶层”与群众对立、官僚主义是苏联落后的“罪魁祸首”,官僚机构是阻碍改革和前进的最大绊脚石。按这种思路,戈尔巴乔夫认定,“改革”政策之所以难以推进,是官僚机构“从中作梗”。他认为,“改革”触及各级官员的切身利益,而官员们害怕失去手中的权力,所以暗中极力地抵制“改革”。苏联社会上上下下的官僚机构形成了一层层网,一堵堵墙。“改革”大船被一种特殊的“阻碍机制”所缠绕,航行困难。于是戈尔巴乔夫提出,苏共“当务之急”就是要自下而上地广泛发动群众,在开明的“改革派”领导人的带领下,向官僚机构施压。
当时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波波夫在宣传打碎经济管理机构方面最为出力,也出尽风头。他撰文提出,要彻底摧毁部门和地方上层的官僚管理机构,为改革开道。2010年波波夫在接受俄罗斯《独立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当时萨哈罗夫是如何说服他,希望他们与叶利钦等人联合起来,一起在政治选举中打败苏共。1988年6月,苏共召开了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全面拉开了政治变革的大幕。从此,苏联社会的政治热潮更为高涨,经济问题仿佛被遗忘在一旁。1989年的差额选举、苏维埃大会的辩论,引发了苏联社会从未有过的“政治高烧热潮”,电视直播党代会使之变成了“全民的政治节日”。苏联各阶层中涌动着从未经历过的政治兴奋。全社会仿佛融入滚滚的政治“改革”洪流之中。一方面是社会情绪逐步升温,政治领域“高烧不退”,另一方面则是中央权威丧失殆尽,各地纷纷抗缴税款,经济割据现象严重,地方分离、民族分裂的危险步步逼近,苏联已危在旦夕。
5.由“争自主”到“搞分裂、闹独立”
80年代末期,由于改革迟迟不见成效,中央权威日渐衰落,苏联和苏共成为“众矢之的”。“经互会”组织中的一些东欧国家认为过去是被“强拉硬配”,是“站错了队”,言语中对与苏联为伍极尽埋怨、后悔之意。在苏联内部,政治松动和经济困境促使民族区域的离心倾向愈发明显。
几经试探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率先打出“主权和独立”的大旗。最开始是三个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戈尔巴乔夫发难,要求在“民主集中”的原则下,扩大党内民主。接着,一些名为“人民阵线”的社会组织在各地纷纷成立,声势日益浩大。“人民阵线”直言“独立于苏联”。一些共和国的党组织对此暗地支持。
除了政治气候的转变以外,许多民族官员开始涂抹“民族主义的色彩”,撇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借以吸引选民的注意。其中,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起了领头羊的作用。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边远共和国发出的“脱离”呼声,在首都得到苏共内部“民主派”和反共势力的积极响应。他们以“俄罗斯”作后盾,反苏共、反中央,竖起了“独立”“自由”的大旗,形成了反对苏共的统一战线。以盖达尔为代表的俄罗斯自由派人士公开提出,俄罗斯应“甩掉原落后的加盟共和国这些包袱”,首先“自救”,然后轻松上路,投入西方发达国家的怀抱。
“俄罗斯民主、独立”的大旗下,聚集了苏联社会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在普通群众的眼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连同“苏共”“社会主义”等已失去了旧日的光彩。俄罗斯才真正是民族、国家及传统的象征。俄罗斯人很不情愿听到自己被称为“苏联人”。他们在对“苏联”的象征反感的同时,为自己将重新作为“俄罗斯人”而欢欣鼓舞,充满自豪。这样,戈尔巴乔夫所代表的苏联和苏共“腹背受敌”, “民族独立”和“民主化”像两把利刃直逼而来。在猛烈的社会情绪的裹挟下,戈尔巴乔夫像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忽左忽右,节节败退。他倡导的“改革”已失去控制,最后“革”到自己头上来了。
不讲政治原则、不坚持苏共领导、不顾复杂的国内外客观实际的“民主化”和“公开性”,造成了苏联社会舆论的严重失控和社会不满情绪的大肆发泄。苏共历史和苏联体制受到质疑。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层面临空前的“信任危机”。大部分人开始认为,苏共将苏联领进了“死胡同”,苏共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失败了。在这种社会气氛中,“民族主义、分离主义成为苏联许多地方都吸食的麻醉剂”。作为苏联最大支柱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宣布,只有“独立”,实现“主权”,才能办好自己的事,必须选择走一条激烈的社会变革之路。
6.理想信念的背离
俄罗斯历史学家指出,在戈尔巴乔夫当政后期,苏共领导人费尽心机,在“道路”、“模式”和“理论”之间摇摆不定。苏共先是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后又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倡导“西欧共产主义”思想,主张吸收全人类的文明成果,提倡新思维。在改革“模式”的选择上,先是学习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经验,转而寻找北欧模式。戈尔巴乔夫当政后期,苏共领导层尤其对瑞典的“福利社会模式”大为推崇。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高层干部纷纷前去访问、取经。1989年以后,戈尔巴乔夫曾打出政治上走“中间路线”的旗号,试图改变颓势,避免苏联解体,但已是力不从心。
1989~1990年,“社会主义”开始在苏联知识分子当中失去吸引力。戈尔巴乔夫给社会主义加上各种前缀如“民主的、人道面孔的”等的企图也宣告失败。例如,戈尔巴乔夫崇信的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社会学会会长塔·扎斯拉夫斯卡娅也停止了她“社会主义是可以改革”的研究方向。1990年,她在苏联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的“大型研讨会”上公开宣称,与会者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根本区别,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成熟的资本主义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而这种观点也得到戈尔巴乔夫另一法学顾问、主管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的副院长弗·库德里亚采夫的赞同。一位西方苏联专家曾这样描述当时苏联知识界的情绪和期盼:“社会主义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不会取代资本主义,更不会提供另一番图景。”
1989年,一些东欧国家风波骤起,苏联社会的激进派受到了强烈的启发。“向西方看齐”的口号极为诱人,反社会主义的旗帜深得人心。1990年前后,转向西方、抛弃社会主义的思潮在苏联社会“盛极一时”。一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在回答“苏联选择什么样的前进之路”时,有32%的被调查者认为要效仿美国;17%选择了德国;11%的人看好瑞典;只有4%的问卷选择了中国方式。不少政治势力决定走一条“彻底革命”之路,逃离社会主义的“此岸”,一步跨入资本主义的“彼岸”。当时的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领导人亚·尼·雅科夫列夫写道:“如果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条死胡同,那么要从死胡同走出来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退回去,退到由于暴力革命而离开的那条大路上去。”
7.自由谎言和市场神话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使一种逻辑越来越鲜明地浮现在激进派和西方派的头脑中。这个逻辑推理简单而明了:苏联70多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与西方的比赛中败北,苏共改革和完善这种制度的努力也未奏效,那么最后只有完全抛弃这种制度,全面照搬和推行在西方社会行之有效的体制。这就是当时苏联社会主流思潮的真实写照。1991年8月事件以后,“激进化”“空想化”倾向在苏联社会思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激进派领导人眼里,“告别社会主义”,选择一条新的、西方式的发展道路,苏联会在一两年的时间内踏上文明、复兴之路。
1992年初夏,叶利钦第二次访问了美国。与上一次出访不同,他已不再是落难的苏共反对派,而是新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在美国的一次演说中,叶利钦宣称,他代表世界上最年轻的“民主国家”,来到了民主传统悠久的“圣地”。自此,共产主义的试验在俄罗斯大地“一去不复返”。所有文明世界具有的东西将会在俄罗斯“开花结果”。在经济生活中,他主张“完全自由的市场”,停止国家对经济工作的干预,认为市场与计划“水火不相容”;让市场的“自然法则”充分发挥作用,“物竞天择”;打破国家所有制,实行私有化,推行纯粹意义上的私有制……
在“胜利情绪”的驱使下,俄罗斯一些知识分子和艺术界人士也摇旗呐喊。他们坚信,市场经济能够带来俄罗斯文艺的复兴。他们认为,在自由和市场的条件下,通过市场“优胜劣汰”,可以筛选出优秀的成果或文艺作品。
新一轮激进改革派以西方社会为样板,制造了一系列市场和自由的“神话”,并借此蒙骗急欲摆脱困境的苏联百姓。当时一位自由派的女经济学家、时任莫斯科市政府经济顾问、经济学博士阿·彼娅舍娃的言论,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社会的舆论思潮和社会心态。她写道:“社会主义与市场、民主‘水火不相容’。俄罗斯应在最短的时间内,以革命的速度实现经济自由化。取消并禁止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将历史的罪人推上‘审判台’。俄罗斯社会要‘忏悔’,将列宁的遗体迁出埋葬。把所有共产主义的象征物搬进博物馆。俄罗斯人蕴藏的商业意识全部释放出来之时,正是俄罗斯社会的复兴之日。”
(本文节选自张树华著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的《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教训》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