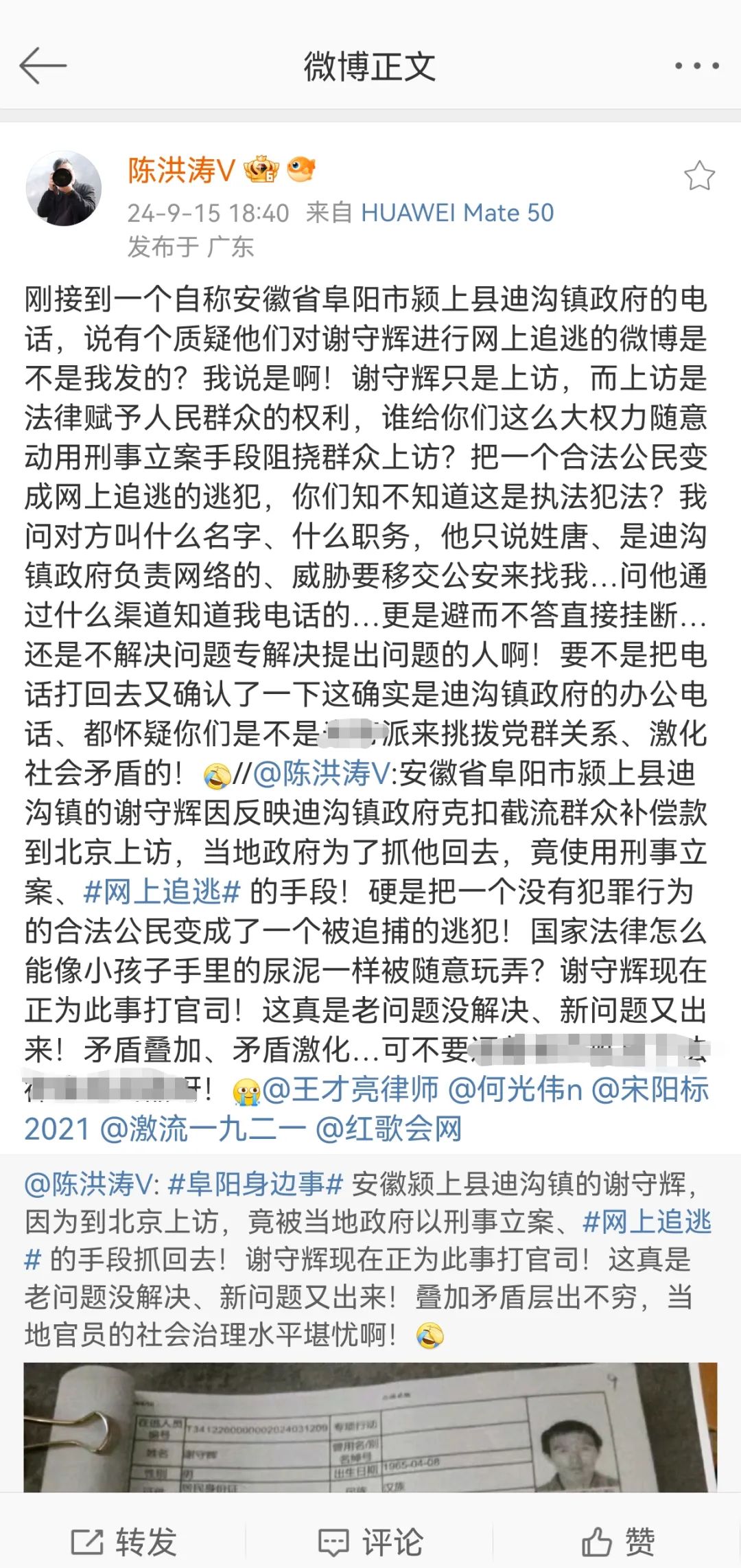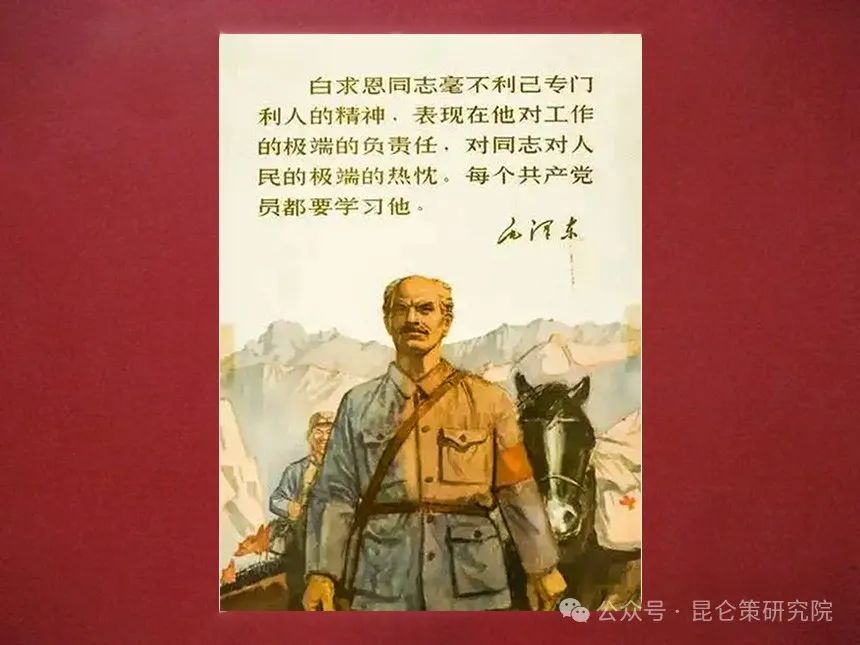好书连载| 刘继明新著《黑与白》第一部·卷一·第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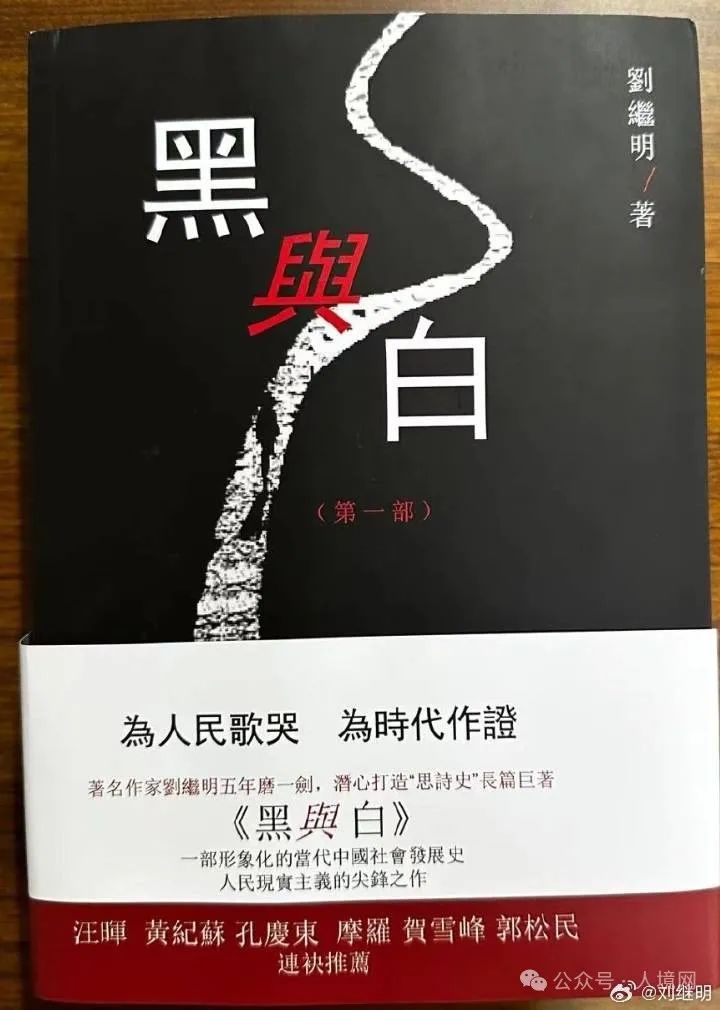
1.睡莲、蝌蚪与古筝
小时候,顾筝经常跟妈妈一起到街上散步。妈妈在家里憋久了,总是喜欢往街上跑。哥哥宗天一见了,赶紧吩咐她:“小妹,快点跟上妈妈,别让她在街上乱跑……”小妹是顾筝的乳名。于是,顾筝放下手中的作业,急忙跟上去,牵着妈妈的手,往街上走去。妈妈一走到街上,就兴奋得东张西望,对街上的一切都充满了新奇。如果是春天,街两旁的香椿树上长满了嫩嫩的香椿芽,妈妈像小孩子一样兴奋地嚷着:“小妹,咱们摘香椿芽回去吃吧,可香呢!”这时,便有人围拢过来,朝妈妈指指点点,小声议论:“她是个疯子,当年可漂亮啦……”
顾筝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说妈妈是疯子。连哥哥跟妈妈吵嘴,也冷不丁冒出一句“你这个疯子!”这时,原本哭哭啼啼的妈妈就会突然停下来,像挨了大人呵斥的小孩子那样,用手背揩一下脸上的泪痕,默默回到卧室,或走到紫瓦屋门口,痴痴地望着池塘出神。哥哥最烦妈妈哭泣了,每次一听见妈妈哭泣,他就用两个指头堵住耳朵,跺着脚喊道:“妈,求你别哭了,我的脑壳都快要炸裂啦!”说完,怒气冲冲地跑出去,半天不回家。哥哥那时刚上初中,可他说话的口气像个大人,对她和妈妈总是发号施令。实际上,他在家里扮演的就是一个大人的角色,妈妈跟顾筝一样,倒成了个小孩似的,家里的一切事都听他的。连妈妈的工资都是他去中学财务室代领的。
哥哥平时对顾筝照顾得很细心,每次替妈妈领工资后,总要在街上给她买几根棒棒糖回来,同时没忘了买一束花送给妈妈。每次见到花儿,妈妈高兴得像小孩似的手舞足蹈,捧着花儿嗅个不停。在顾筝印象中,妈妈特别爱美。妈妈是一个美丽的女人。
那时,顾筝已经上小学,开始懂事了。但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只有妈妈,没有爸爸。她问过妈妈,妈妈神情呆滞地看着她,一脸茫然的样子,喃喃自语道:“……好好地一个大活人,怎么说失踪就失踪了呢?”说完,吃吃地笑。
妈妈一个人时,经常念叨这句话。顾筝曾不止一次地问哥哥,但他总是很不耐烦,像大人那样双手叉腰,一连串地反问道:“妈妈说的是疯话,你信吗?咱妈是个疯子,你不知道吗?”
“那……为什么别人都有爸爸,咱们没有呢?爸爸去哪儿啦?”
哥哥气咻咻地说:“这话你问了多少遍了,咱爸早死啦!”
顾筝似信非信。“妈妈不是疯子,爸爸没有死,他还活着!”她大声说。
哥哥被她惹火了,翻了翻白眼,“你真烦,我出去玩儿,不理你啦!”
哥哥一有空就溜到街上去玩儿,把顾筝和妈妈撂在家里。妈妈从来不管哥哥去了哪儿,只是到吃饭时才想起来,问顾筝一句:“宗天一呢?”
妈妈经常一个人在屋子里,望着藤木箱发呆,那只箱子上了锁,从没见人打开过,不知装的什么。顾筝问过哥哥,他也说不知道。有时,妈妈对着床前那面长方形的镜子,呆呆地看着里面的自己,一看就是好半天。一次,顾筝发现妈妈头发上有一根白发,就拔了下来,交给她说,“妈妈,你头上都有白发啦!”
妈妈盯着那根白发,伸出手来一把抢了过去,放在眼前死死地盯着,忽然双手蒙住脸,呜呜哭起来。顾筝不知所措。但没过一会儿,妈妈就忘了这件事,牵起她的手说:“小妹,走,跟妈妈去喂蝌蚪吧!”
妈妈从来只叫顾筝的乳名,很少叫她的学名。其实,“顾筝”这个名字是妈妈给她取的。上小学一年级时,她还没有一个学名,填报名表时,老师便照着户口簿给她写了个“宗小妹”。但她觉得这个名字很难听,每次老师点名,她都不回答。老师没办法,只好对她说:“宗小妹,回去让家长给你取个正式的学名吧,否则就别来上课了。”在回家的路上,她把老师的话告诉哥哥,说:“哥,报名表上填的你是家长,你给我取个学名吧!”
哥哥挠着脑袋,想了半晌也想不出来,就说:“咱们还是回家让妈给你取好不好?”
顾筝说:“你不是说妈妈疯了吗,哪有疯子给孩子取名字的!”
哥哥被呛住了,“也许……妈没有完全疯呢,再说妈当过老师,哪有当老师的不会取名字的!”顾筝觉得哥哥有点狡辩,但也只好同意了。
兄妹俩回到家时,妈妈正在用一块干净的抹布擦拭古筝,她每天都要将那古筝擦拭两遍,黝黑的琴身在暗淡的光线下熠熠发光,照得出人的影子来。兄妹俩围上去,争先抢着帮妈妈擦拭古筝,擦完后,哥哥就对妈妈说:“你给小妹取个学名吧!”
哥哥像往常那样,用的是命令的口气,妈妈一向很听哥哥的,仿佛哥哥不是她的孩子,她是哥哥的孩子似的。“古筝。”她犹豫片刻后,嘴里轻轻吐出了两个字。那会儿,妈妈的目光正落在那只古筝上,兄妹俩还以为她说的是琴呢。
“让你给小妹取学名,说这个破琴干啥!”哥哥又不耐烦了。
“古筝。”妈妈嘴里又吐出这两个字。这会儿,她把目光转到了顾筝身上。顾筝忽然明白了,“哥哥,妈妈是给我取名呢。顾——筝!”她拍着手欣喜地说,“听见了吗,我的学名是顾筝,我跟妈妈一样,也姓顾……”妈妈听见顾筝的话,脸上露出一缕笑意,双手把她搂进了怀里。
那一刻,顾筝觉得妈妈的怀里真温暖。
妈妈最喜欢的就是喂蝌蚪。每年春天,紫瓦屋门前的池塘碧波荡漾,清澈得像一块晶莹剔透的碧玉,塘里的荷叶亭亭玉立,长满了青青的睡莲,一只只小蝌蚪在水里摇着尾巴,成群结队地游弋着,寂静的夜晚,顾筝听见池塘里传来一阵阵嗤嗤的响声,妈妈说小蝌蚪肚饿了,在吃荷叶和睡莲叶儿呢!妈妈每天都要把没吃完的剩饭和馒头留着,去池塘里喂蝌蚪。他们平时都在小学的食堂打饭回来吃,周末食堂不开饭,才自己做。每次顾筝去食堂打饭,妈妈总要小声叮嘱一句:“小妹,多打一点饭,给小蝌蚪吃。”生怕哥哥听见了。哥哥反对妈妈喂蝌蚪,说她浪费粮食。但在这件事上,顾筝坚决跟妈妈站在一起。她也喜欢蝌蚪。每次喂蝌蚪,妈妈都很投入,蹲在池塘边,一边把碗里的剩饭或馒头屑揉碎,慢慢撒到池塘里,嘴里一边念叨:“别抢,都有的吃,吃饱了好长身子哦……”,满脸慈爱,仿佛一个正在给孩子喂奶的母亲。
春天过去后,小蝌蚪长成了青蛙,池塘里每天响着此起彼伏的蛙鸣。顾筝放学回来,经常看见妈妈站在门前那棵海棠树下,若有所失地自言自语:“小蝌蚪去哪儿了呢?”
那棵海棠树有一丈来高,挺直粗壮的树干,黑得像上了一层厚厚的油漆,枝叶繁茂浓密,婆娑遒劲,像手臂一样伸到屋檐下。每到春天,树上便开满了粉红色的海棠花儿,一朵朵,一簇簇,映在镜面般的池塘里,宛如一片片妍丽的彩霞。秋天来临时,海棠果熟了,哥哥用竹竿朝树枝上轻轻一挑,便像下雨似的落下一串串浑圆的海棠果。顾筝和妈妈将海棠果捡起来,在池塘里清洗过一遍后,放进嘴里用牙齿一咬,又酸又甜,满口生津。妈妈高兴得像个孩子,欢天喜地,眼角逐渐增多的鱼尾纹似乎也较少了,看上去比过去年轻好几岁。妈妈一高兴,就从屋里拿出那只古筝,坐在海棠树下,认真地弹奏起来。妈妈最喜欢弹奏的是一首外国乐曲,非常优美,顾筝后来才知道,那首乐曲叫《红莓花儿开》。弹到投入时,妈妈还情不自禁地低声哼唱几句:
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
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喜爱
可是我不能对他表白
满腹的心腹话儿没法讲出来……
妈妈唱得真好听。那一刻,顾筝觉得妈妈是世界上最美丽最优雅的女人。这样的妈妈怎么会是疯子呢?顾筝只要一想到这儿,心里就很沮丧。特别是有人当着她说“你妈是个疯子”时,她难过极了。
2.举起手来
宗天一跟妹妹顾筝一样,最讨厌有人说妈妈是疯子,尽管他生气时也这么说。但这是两回事儿。当他说妈妈是个疯子时,心里其实想说的是“妈妈不是疯子”。他希望妈妈还像从前那样细心温柔地照顾呵护自己,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还要自己照顾她。而这一切,都因为爸爸不在了,爸爸失踪了,爸爸死了——他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是真实的,但唯一的真实是爸爸从家里,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
宗天一一直不愿意承认这个残酷的事实,但镇上人总是以各种方式提醒他,甚至指着他的鼻子说:“宗天一,你爸爸是个大流氓!”他一听,浑身的血液往上涌,真想冲上去把对方的嘴巴撕烂,但说这话的不只一个人,镇上许多人都这么说,有的不敢当面说,就背后偷偷议论。他能撕烂一个人的嘴巴,但不能撕烂镇上所有人的嘴巴。那一刻,宗天一感到了深深的羞耻,同时为不能保护自己以及妈妈和妹妹而屈辱。宗天一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有这个责任。有一阵子,他恨透了邳镇上那些当众和背后羞辱自己的人,暗暗发誓,总要一天要让他们付出代价。但渐渐的,他将这种“恨”转向了“那个人”——从家里消失已久的爸爸。他在内心里总是称爸爸为“那个人”。他觉得自己现在承受的一切屈辱和痛苦都是源于“那个人”。他为什么要不明不白地失踪呢?他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镇上人为什么要说他是“大流氓”?他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
无数的疑问在宗天一脑子里像蝗虫一样飞来飞去,使他头痛欲裂。这时,他就会在家里冲妈妈和妹妹发脾气,发完脾气又后悔。于是,他就从家里出来,跑到街上,漫无目的地溜达。邳镇只有一横一竖两条街,一根烟的工夫就溜达完了。
宗天一就是那会儿学会抽烟的。起初他只是为了摆脱心头的烦恼,捡别人扔在地上的烟蒂吸。吸着吸着就有点儿离不开了。宗天一开始买烟。但他不是用妈妈工资里的钱买烟。那是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费,无论如何不能动。自从妈妈生病后,学校每个月就只给她发一半的工资。妹妹上学后,妈妈的那点工资越来越不够全家的开销了,宗天一只好利用课余时间去捡废铜烂铁,到镇上的废品收购站卖点钱,补贴家用。他吸烟的钱就是从自己卖废铜烂铁的钱里开支的。有一天,他想在家里找出一点废铜烂铁拿到收购站去卖。他打起了爸爸留下来的那只藤木箱的主意。
藤木箱上了一把大铜锁,自从爸爸失踪后,这只藤木箱就一直锁着,从来不曾打开过。那把大铜锁黄澄澄,沉甸甸的,拿到收购站也许能卖不少钱。宗天一用一根铁丝在锁孔里鼓捣了几下,铜锁就给打开了。他原以为藤木箱里装着什么珍奇玩意儿,好奇地掀开一看,见里面除了一盘写着外文的唱片和一摞信封,还有一本用牛皮纸包的书,比砖头还要厚。家里还有一只大皮箱,那是妈妈下乡插队时从城里带来的,里面装满了书,如《红与黑》《包法利夫人》《呼啸山庄》《简爱》《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等。小时候,宗天一看见妈妈经常捧着这些书读得津津有味,上小学后,他曾好奇地翻阅过几本,但书里都是一些外国的地名和人名,他总记不住,看几页就头晕脑胀、昏昏欲睡。但现在的这本书有些特别,里面有不少插图,画中的男男女女一个个赤身裸体,宗天一见了顿时脸皮发烫,身上的血液像被烧着了似的一阵燥热。他像做小偷一样回头四顾,屋里除了他没有别的人。于是,他鬼使神差一般将那本书揣到怀里,将藤木箱用大铜锁锁好,悄悄放回了原处……
后来,宗天一才知道这本书叫《金瓶梅》,是一本禁书。
从那天开始,宗天一每天晚上都躲在房间里看那本带插图的《金瓶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开始注重打扮,除了抽烟,还给自己买了两件邳镇上许多青年常穿的T恤或夹克衫,还有皮鞋,有时还花一毛钱去看一场电影。那时候,邳谷人民公社刚改为邳镇,以前专门用来召开群众大会和举办各种文艺汇演的大礼堂也改成了电影院,邳镇人以前经常看的京剧样板戏和战斗故事片渐渐少下来,开始放映一些香港台湾和外国片,如《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巴士奇遇结良缘》《追捕》《望乡》。看完《望乡》《追捕》的那天夜里,宗天一做了一大堆梦,一会儿梦见年轻时的“阿崎婆”,美艳的日本影星栗原小卷,还有那本《金瓶梅》插图中的西门庆,从书页上跳下来……
那天夜里,宗天一手淫了。
宗天一的个人开销日渐增多,手里越来越拮据。一天下午,学校刚放学,宗天一就迫不及待地离开教室,来到邳镇砖瓦厂,砖瓦厂位于镇西头的江边,占了好大一片地,从外面就能看到厂区中央一排排红色的厂房,非常气派,砖瓦厂的工人工作时间一律头戴安全帽,身穿蓝色劳动布工装,很威风的样子,有的年轻工人下了班去邳镇逛街,也照样穿工装戴安全帽,引来不少姑娘小伙子艳羡的目光。但更威风气派的是矗立在厂区中央的烟囱。那根烟囱据说有几百米高,下粗上细,越往上越细,像一根没有剥皮的竹笋,也有人说像男人的物件,几十里外都能看到。从建成那天开始,砖瓦厂就是邳镇人的骄傲,这多半与那根高耸入云的烟囱有关。
砖瓦厂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建起来的,是邳镇最大的一家“社办企业”,不仅有厂办医院,还有子弟学校,改称“乡镇企业”以后,砖瓦厂虽然还像从前一样红火,却没有了过去那股威风劲儿,比如以前没有人敢跑进厂区拿走哪怕是一块砖瓦或一根铁丝,现在却经常有人溜进厂里,偷走一些零零碎碎的铁器残片,其中有一些还是制砖机上拆除后随手扔在地上等待维修的零部件,然后拿到镇上的废品收购站卖掉。人们尝到了甜头,去砖瓦厂“捡破烂”的越来越多。
现在,宗天一也到砖瓦厂碰运气来了。砖瓦厂实行的是三班倒工作制,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上班,快到下班时间了,厂区里仍然一片繁忙的景象,工人们用鸡公车将砖坯从露天的制砖工地运往烧制砖瓦的“大窑洞”——那根巨大的烟囱就是从这儿竖立起来的。
砖瓦厂没有围墙,从哪儿都能进到厂区。宗天一在靠近厂区的公路边的一块蓖麻地里躲藏了一会儿,他点燃一支烟,一边吸,一边耐心地等待天黑。蓖麻地里散落着不少烟蒂,显然有不少人在这儿躲藏过。大约过了两支烟的工夫,天就黑下来了。
宗天一走出蓖麻地,不慌不忙地朝厂区走去。
那会儿,正是轮班工人们的交接班时间,制砖工地通往“大窑洞”的大道上灯火通明,人来人往,但没有人注意到宗天一。他就是趁这个机会钻进制砖工地的。工地上,制好的砖坯一堆堆、一排排,码得整整齐齐,像一支严阵以待的军队。宗天一是第一次到这里来。看见果然像传说的那样,各种废弃或等待维修的零部件随处可见,沾满了机油和柴油,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他像找到了宝藏似的,兴奋得两眼发亮,他从腰上解开一条裹成长条的蛇皮袋抖开,猫着腰将地上的那些黢黑物件飞快地装进袋子。
没多一会儿,袋子就快装满了,再装就背不动了,宗天一才背起沉甸甸的袋子,往外面走去。但他刚迈出两步,耳边突然响起一声断喝:“站住,不许动,举起手来!”
宗天一吓了一跳,转过脸,看见两个戴着红领巾的少年从砖坯后面跳了出来,一个握一把弹壳做的小手枪,另一个持一支明晃晃的红缨枪。
宗天一不由自主地放下袋子,举起了双手。
3.坦白从宽两个少年威风凛凛地押着宗天一,穿过两边都是砖坯的厂区大道,向厂部走去。大道两边堆满了碎砖瓦,在惨白的电灯照射下,斑斑驳驳,像一片片废墟。不时有交接班的工人从旁边经过,投过来诧异的目光。有人问:“王成,你抓的这是谁啊?”
“他偷厂里的东西,被我捉住啦!”叫王成的少年仰起脖子高声答道,那副得意的神气,像电影里抓了俘虏的小八路。仿佛为了显示威风,他故意用弹壳手枪顶住宗天一的腰,大声命令:“走快点,别给我耍花招,想逃跑!”
宗天一辩解道:“我没想逃跑。”
“老实一点,不许狡辩!”宗天一的后腰又被弹壳手枪顶了一下,这回用力更大,他感到一阵疼痛,哎哟叫唤了一声。
这当儿,另一个少年说:“王成,你这是虐待俘虏,我要向你爸爸报告!”
“巴东,你要是打小报告,下次考试我就不给你抄,厂里执行任务也不让你参加了!”王成警告道。
叫巴东的少年一听,立刻怂了,但还是不甘心地顶了一句:“你就会威胁人,你比你爸还霸道……”
王成听了这句话,警惕地追问:“这话谁说的,是你爸说的吗?”
巴东支吾道:“不是我爸,是我说的。”
王成盯着巴东,满脸不相信的神情,撇撇嘴:“我知道你爸经常在厂里说我爸的坏话!”
“哼,你这是污蔑,我爸从来没说过你爸的坏话!”巴东大声抗议道。
王成见巴东急红眼的样子,就嘻嘻一笑,“我爸说,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我不跟你争啦!”
“这是毛主席语录!你敢说是你爸说的?”
……
王成的脸微黑,大大的脑门,两只眼睛黑亮黑亮的,总是在思考什么问题似的;巴东呢,皮肤白皙,长得十分英俊,眼珠子总是滴溜溜转个不停,透出一股精明和狡黠劲儿。
两个少年你一言我一语地争吵着,将宗天一押到了厂部办公室。办公室不大,中间有一张大桌子,四周摆放着几把藤椅和条凳。正面墙壁中央有两幅领袖像,一幅是毛主席,一幅是华主席,领袖像上面是一行大字标语:“继承毛主席遗志,抓纲治国,大干快上,为建设四个现代化努力奋斗!”
宗天一被推进了办公室,王成用命令的口气对他说:“你先写好交代,不许撒谎。我爸说过,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说着,从桌子上拿过一张纸和一支圆珠笔递给了他,接着又吩咐巴东道:“你在门口站岗,别让他跑了,我去叫我爸来。”
“是,中队长同志!”巴东握着红缨枪,站在门口昂首挺胸地应道,还学着电影里的小八路向王成打了个立正。王成满意地伸出小拳头朝巴东胸前轻轻捶了一下,飞也似地跑出了厂部办公室。
宗天一盯着那张白纸,不知写什么。其实他在学校语文成绩一直很好,每次老师布置作文,他总是第一个交卷,但现在,他脑子一片空白,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不知道自己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理。听说被砖瓦厂抓住后轻则要接受劳动处罚,情节严重的还要扭送派出所,说不定还要游街。以前有人盗窃集体财产被抓住后,总要在邳镇上游街批斗的。他仿佛看见自己五花大绑,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被人押着在街上游街,许多人指着他的脊梁骨愤怒地斥骂:“宗天一,你这个小偷!你爸爸是大流氓,你是小流氓!……”他仰起头,望着墙上的毛主席和华主席像在白炽灯的照射下显得很慈祥。他暗暗祷告:“毛主席华主席啊,我错了,我不该偷集体的财产,你们原谅我吧,千万不要让我去游街,那样我在邳镇上就抬不起头来啦!”他在心里喊了两遍“毛主席万岁!”他忘记毛主席已经去世了。后来,他把目光投向站在门口的巴东身上,眼珠子滴溜溜转了几下,灵机一动,忽然放下圆珠笔,捂着肚子哎哟哎哟地叫起来。
巴东瞪了他一眼说:“你叫唤什么?”
“我肚子痛,我要去拉屎……”宗天一装出一副痛苦的样子说,“快点,要不我就拉到裤子里啦!”
“电影里的汉奸被八路军抓住后,总爱用这招逃跑。”巴东瞅着他“扑哧”笑了,“你想骗我?门儿都没有!”
宗天一见自己的计谋这么快就被识破,有些不甘心,又心生一计:“刚才那小子,论个儿也不比你高——他叫啥来着?王成……他干嘛总是欺负你?你是不是怕他?”
“谁怕他?你说我怕他?”巴东梗着脖子,将手里的红缨枪对着宗天一,“你再说,我可对你不客气啦!”
那杆红缨枪的枪尖是木头做的,涂了一层白漆,一看就是假的。宗天一觉得更有信心了,“你要是真不怕,就把我放了!”
巴东听了,放下红缨枪,像泄了气的皮球。“这我可不敢,要是让他爸知道了,那可不得了。”
“他爸是啥人,你这么怕他?”
“他爸是厂长。厂里的所有人都归他管,我爸是副厂长也要归他管……”
宗天一知道自己的激将法落空了。他沮丧地埋下头,握住圆珠笔,盯着面前的白纸出神。
就在宗天一苦思冥想写交代的时候,外面传来一阵重重的脚步声。脚步声由远而近,突然停住了。宗天一抬起头,看见一个满脸络腮胡、古铜色脸庞,长着一双豹子眼的人出现在门口,他穿着一件褪色的旧军装,衣领敞开着,裤脚挽到膝盖上,一双解放鞋沾满了泥灰, 左手满是油污,还拿着一把同样沾满油污的扳手,右手——袖筒空荡荡的,原来是个“一把手”。那个叫王成的少年像个小保镖似的紧跟在他身后。
“报告厂长伯伯……”巴东给“一把手”行了个不太标准的军礼。
“你小子今天立大功了,明天我就跟你们校长说,让他给你和王成发一张大奖状!”“一把手”摸了一下巴东的脑袋,笑哈哈地说,“你的任务完成了,赶紧回去吧,记住,让你妈包饺子慰劳你一下,就说是我说的!”
巴东得令一般跑开了。“一把手”这才大步走进办公室,双目炯炯地打量耷拉着脑袋的宗天一,口气严肃地问:“你就是偷厂里东西的小家伙?叫啥名字,说!”
宗天一仍然低着头,不吭声。王成在一旁帮腔似地说:“爸,这家伙态度可顽固了,叫他写交代,才写这么几个字……”他把宗天一写的那张纸递给“一把手”。“一把手”接过去,看了一眼,目光忽然在纸上停着不动了,半晌,才把目光离开,转向宗天一,从上到下认认真真地端详着,“你叫宗天一?”
“嗯呐。”
“你爸叫宗……小天?”
“嗯呐。”
“你妈叫顾……影?”
“嗯……呐。”
“他们都是中学的老师?”
“嗯……”宗天一疑惑地抬起头,见“一把手”的目光有点儿异样。他将那把油渍渍的扳手放到桌子上,一屁股坐下来。沉默了一会儿,才对宗天一说:“小子,你爸爸妈妈我都认识,嗯,两个有才华的青年!他们刚从省城到邳镇安家落户时,我还曾到楚州去欢迎呢,那会儿,我还是公社人武部长兼革委会副主任嘛……”他一边说,一边从上衣兜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大前门香烟,用嘴巴叼出一支,又从抽屉里找出一盒同样皱巴巴的火柴盒,动作显得很笨拙却又熟练地点燃,深深吸了一口。“你爸失踪后,是我带领基干民兵进山搜索,找了一个多月,把邳谷山都找遍了也没找到,现在连是死是活都没有一个正式结论……当然,你爸爸在生活作风上是犯了错误,而且失踪的也不明不白,可人这一辈子谁不犯点儿错误呢?说到底,他们毕竟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咱们邳镇安家落户的知识青年呀……你妈妈的病现在还没有好吗?”
宗天一惊异地发现,“一把手”跟刚才那副威严的样子判若两人,说话的语气和神情变得和蔼可亲。他惶然地“嗯呐”着,不知怎的,眼眶里渐渐盈满了泪水。
“小子,我没记错的话,你还有个妹妹吧?孤儿寡母的,日子肯定难过嘛。”“一把手”皱着眉头说,“这样,以后星期天和放假,你来砖瓦厂当临时工吧,挣点钱回去补贴一下家里。不过,你做了损害集体财产的事情还是要关禁闭的,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他将烟屁股扔到地上,“小子,你叫什么来着?哦,宗天一!你长得挺像你爸的,不过没他个儿高。你还小嘛!”他想起什么似的,又问,“你饿不饿?我让食堂师傅给你下碗面条吧?”他没等宗天一回答,就对站在旁边的王成吩咐道:“儿子,去让食堂值夜班的师傅下一碗面来,账记在我名下……”
王成噘着嘴巴“嗯”了一声,把弹壳手枪插在腰上,显得很不情愿地朝外面走去。
宗天一觉得,王成的眼睛跟一般人不一样,但究竟怎么不一样,他又说不清楚,琢磨了好一会儿,他才明白过来:王成的右眼是单眼皮,左眼是双眼皮。
4.一家之主
宗天一被关了两天禁闭之后,才从砖瓦厂出来。回到家时,已经是下午了。他刚走近紫瓦屋,妹妹顾筝便像一只小鸟那样奔过来,一头扑进了他的怀里。“哥哥,你这两天跑哪去啦?我和妈都快急死了!”
宗天一见顾筝眼泪汪汪的,心里有些内疚,不知道怎么把这两天的经历告诉妹妹,正犹豫着,就听妹妹在她耳边小声说:“哥,咱家里来了一个陌生人,我和妈妈好害怕……”
“陌生人……他人呢?”宗天一赶忙问。
“在家坐着呢,一大早就来了,他说是咱外公。可妈说不认识他,躲在房里不肯出来。哥,他会不会是冒充外公的狼外婆呢?……”妹妹颠三倒四地说着,宗天一越听越糊涂,三步并作两步走进家门,果然看见一个头戴鸭舌帽,身穿灰布工装的老头儿坐在大门边的一把椅子上,正在看报纸。见宗天一进去,老头儿赶紧放下报纸,站起身来,一边打量他,一边操着外地口音说:“你是天……一吧?”
宗天一嗯呐着,打量着老头儿,他觉得面前的这张面孔好像在哪儿见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
“当然,你……们兄妹都不认识我。我是你们的外公啊!”老头儿眼圈有些泛红,隐约闪动着一丝泪光。“连你妈也不认识我了……”他说着从身上的挎包里拿出一张泛黄的照片,宗天一接过照片,见是一张三人合影,他一眼认出中间那个扎马尾辫的姑娘是小时候的妈妈,紧挨着妈妈的那两个人……“这个是我,这个是你外婆呢!”老头儿在旁边用手指点着。
宗天一这才记起来,这张照片他以前在家里的相册里见过,爸爸失踪以后,那个相册就不见了。他怀疑是被妈妈撕掉了。自从她病以后,经常在家里撕东西。有时候连他们兄妹俩的课本也撕。
“孩子,我和你外婆对不住你妈,也对不住你们兄妹,这么多年没来看你们,也不知道你妈病成这样了。”老头儿说着,布满皱纹的眼眶里涌出了泪水。“这次,我到楚州出差,你外婆让我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你们,见一面……”
宗天一不知如何面对这样一个泪流满面的外公。不管怎么说,这是自己的外公。他想,就对旁边的顾筝说,“小妹,妈妈呢?叫妈妈来见外公呀!”
顾筝正睁着一双好奇的大眼睛看着外公。她对宗天一说:“妈妈说不认识外公,她说她害怕,跑到街上去了……”
“你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她是怎么变成这样子的呢?”外公难过地说,又掏出手帕揩眼睛。
后来,外公要走了。外公说他要赶今天最后的一趟班车去楚州,然后再回省城。他说他下次要跟外婆一起来看他们,他说孩子你这么小的年纪,一家人的日子就压到你肩上了,要是碰上啥困难就给外公外婆写信。外公像个老娘们儿那样絮絮叨叨地说,从挎包里掏出一叠钱要给宗天一。
宗天一试图推开那叠钞票,尽量像个大人似地说:“我不……要!我就要在砖瓦厂上班了,我能挣钱了,我能养活妈妈和妹妹……”
但外公不由分说地将钞票塞进了他怀里。临走时,他还把顾筝拉到身边,亲了一下她的额头。
那一刻,宗天一忽然觉得自己长大了。作为一家之主,他应该担负起养活妈妈和妹妹的责任啦。
从那以后,每个周末与节假日,宗天一便开始在砖瓦厂做临时工。砖瓦厂的临时工大都是从附近农村招来的农民,也有宗天一这样的半大小子。活儿主要是用手推车将砖坯从制砖工地运到烧制车间——就是烟囱下的那个大窑洞。手推车只有一个轮子,邳镇人叫鸡公车,是砖瓦厂统一发的。由于只有一个轮子,鸡公车的平衡很不容易把握,主要靠臂力掌控把手,宗天一年纪小,臂力不够,第一次就翻车了,车上的砖坯稀里哗啦倾落在地上,摔成了碎片。砖坯的损失是要从他的工钱里扣掉的。接连翻了几次车,宗天一心里更加紧张,每次推车时都如临大敌,但越是紧张越容易出差错,车子照样翻。
那天,宗天一将装满砖坯的鸡公车刚刚推出制砖工地,车子就歪歪斜斜,砖块从车子上掉落下来,眼看就要整个儿倾翻了,突然从后面跑过来两个戴红领巾的少年,一左一右从两旁把车子稳稳地扶住了。
宗天一抬头一看,见是王成和巴东。有了他们的帮助,车子一路平稳地驶进了大窑洞。卸车时,王成和巴东又帮宗天一把砖坯从鸡公车上搬下来。已经是夏天了,大窑洞里的气温本来就比外面高,卸完砖坯,几个人都是一身的大汗,像从水里爬上来似的。
“你们为啥要帮我?”宗天一将脖子上的毛巾递给他们,问了一句。
“学雷锋呗!”王成扬起一张红扑扑、汗津津的脸蛋,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
“他爸要求子弟学校的学生周末和节假日都要来工地上参加劳动呢!”巴东补充说,“每参加一次劳动,厂里都要发一根大冰棍……”
“你就知道吃,不发冰棍就不参加劳动啦?”王成白了巴东一眼,“就你这觉悟,离少先队员的要求还远着呢!”
看着王成和巴东又互相掐起来,宗天一乐了,“你们俩真逗,平时就喜欢斗嘴吗?”
听宗天一这么说,他们倒不好意思了。
“我们两家隔壁挨隔壁,他放个屁我都听得见!”王成瞅着宗天一,眨巴眨巴眼皮,做了个鬼脸:“上次把你给拿住,你还恨我们吗?”
“恨啥呀,感谢还来不及呢!要不是你俩,我今儿能有机会到砖瓦厂做临时工?”宗天一真诚地说,“等领了工钱,我请你俩去上馆子!”
“真的?说话算话哦!”巴东伸出食指,要跟他拉钩。
“说话不算话是王八!”宗天一拍着胸脯说。
三个少年越说越投机,俨然成了要好的朋友。
半年后,宗天一在砖瓦厂领到了第一笔工钱。扣除翻车摔碎砖坯的损失费,他拿到手的钱有二百零一元。在宗天一眼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差不多相当于全家一年的生活费呢。
宗天一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领工钱后第一件事就是请王成和巴东上馆子。那天,宗天一在砖瓦厂子弟学校门口等了好一会儿才等到他俩。
巴东听宗天一真要请他俩上馆子,高兴得差点儿蹦起来,冲他连连竖大拇指:“说话算话,你真够爷们儿,以后我就认你是老大了!”
王成却犹豫地说:“你真的要请我们呀?我爸爸要是知道了,会不会说我搞特权……”
“你不去?我可要去了。”巴东故意咂巴着嘴,对宗天一挤了挤眼,拉着他的胳膊就走。
王成犹豫了一下,还是跟上了他们。
长这么大,宗天一是第一次请客,心里升起一股从未有过的自豪感。腰包里的钞票鼓鼓的,他的心里也鼓鼓的,腰板挺得笔直,颇有几分财大气粗的神气。在去镇上的途中,他大声大气地问王成和巴东:“说吧!你们想吃啥?”
“我要吃肉!”巴东抢先说,“我已经三天没吃肉啦!”
“你撒谎!”王成马上揭露道,“昨天你爸带你去食堂吃饭,还给你买了一盘青椒炒肉丝呢!
巴东脸顿时红了。
宗天一见他两又要开掐,就岔开话问王成,“你想吃啥呢?”
“来一碗肉丝面就行了。”王成说,“我爸最讨厌贪吃贪喝的人,说那是资产阶级生活习气。”
巴东脸红红的,没做声。
“放心吧,今儿保证让你吃到肉。我有的是钱呢!”宗天一拍了拍鼓鼓的荷包,安慰巴东,但他心里有数,花钱绝不能大手大脚。他早想好啦,请王成和巴东去供销社的小餐馆,每人一碗肉丝面,再加上两个肉包子,三个人加起来不到一块钱,刚好花掉工钱的一个零头。这样既满足了巴东“吃肉”的愿望,又算不上王成所说的“贪吃贪喝”,岂不两全其美?
许多年后,当宗天一成了一名企业家,经常出入高档餐馆和酒店,吃遍各种山珍海味时,他偶尔还会想起在邳镇供销社请王成和巴东吃肉丝面的情景。他记得巴东吃完面条外加一个大肉包子,还舔着舌头,望着飘了一层油星子和葱花的面汤,一副没有吃饱的神情。宗天一只好又给他要了一个大肉包子。巴东的脸上笑开了花,对他竖起大拇指说:“哥们,你真大方!等我有了钱也请你吃肉丝面,不,我请你吃炒菜,加倍还你!”
王成的单眼皮和双眼皮不屑地眨了两下,讥诮道:“你就吹牛吧,你爸给你的零用钱还少,你请过我一次吗?”
巴东揩了揩油渍渍的嘴巴说:“你没请我,我凭啥要请你呢?”
王成说:“我爸从来不给我零花钱!”
巴东说:“你爸太小气了!”
“不许你讲我爸的坏话!”王成生气地说,“我爸是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
眼看两个人又吵起来了,宗天一只好将两个大肉包子分别塞进了他们的嘴里,才算平息一场嘴巴仗。
结账时,宗天一又买了一笼肉包子,带回家给妈妈和妹妹吃。他寻思,哪天带妹妹去镇上新开的一家个体户服装店买两件衣服,妈妈那双鞋子早就破了,也该给她买双新的了。
这样盘算着,宗天一真的有了几分当家人的感觉。
不知什么时候,宗天一脖子上出现了一个显眼的喉结,说话时嗓音也变得低沉了一些,褐色的头发凌乱地耷拉在额头,目光阴郁,看上去有点儿桀骜不驯。邳镇上一些认识宗小天和顾影的人说,这小子相貌俊朗,酷似他那个失踪的爸爸,不过,宗天一的眼睛像他妈妈。他妈妈当年可是一个美人儿,知道这小子的爸爸妈妈是谁吗?当年从省城来到咱们镇上安家落户的知青中,那可真是才貌双全的一对儿啊,可惜后来失踪的失踪,发疯的发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