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好哭”就是好电影吗?
01
今天的战争电影,有一种非常奇怪的倾向,即把“好哭”与否作为衡量影片好坏的主要标准。
比如,几乎所有的影片宣发,都在说“观众直呼‘好哭’”、“太‘好哭’了”、“泪奔”、“破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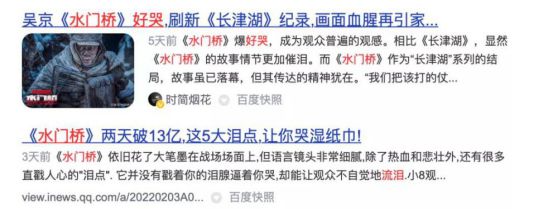
记得抗美援朝经典电影《英雄儿女》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王成牺牲后,在文工团工作的妹妹王芳连夜为他创作了一首“好哭”的歌。她带着这首歌向军政治部王主任请教,并强调说,“我是流着眼泪写完的。”
王芳满以为首长会肯定她的工作,不料却受到了批评:“你是想让全军战士都和你一起抹眼泪吗?”
王芳毕竟经过战火考验,她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很快调整了创作思路,写出了令人热血沸腾的《英雄赞歌》。
“好哭”说到底是一种相对消沉的情绪,并不利于激励部队奋勇杀敌,所以王主任才会不满意。

如果说,王芳在第一次创作时强调“好哭”,还是出于对英雄、对哥哥一种真挚感情的话,那么,今天,突出“好哭”,更多的就是一种对票房和市场的考虑了——这从他们非常冷静地把“好哭”作为一种市场噱头来宣传就能看得出来。
“好哭”成为战争电影的标准,还有另外的效果。
最近上映的《水门桥》中,七连全部牺牲,只有易烊千玺饰演的新兵伍万里一人幸存。媒体说,这很“好哭”;《狙击手》中,五班全部牺牲,只有大永一人幸存。媒体也说,这很“好哭”。
在《狙击手》中,几位战士的牺牲,都至为惨烈——
班长刘文武,身绑手榴弹与美军同归于尽,“只找到一顶帽子”;胖墩先是被美军击碎双手,再击中要害;亮亮身负重伤后倒在雪地上,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躺了整整一夜(这其实是一个漏洞,从常识来说,亮亮很难幸存到天亮),最后用注射强心剂的针头刺进心脏,向其中注射空气而牺牲……
唯一幸存的大永,被坦克上的重机枪子弹击中腹部,他爬过的雪地上,留下一道宽宽、长长的血痕!
有人上传一段在《狙击手》放映厅里拍摄的视频,其中都是年轻的电影观众紧张地闭上眼睛或惊慌地用手捂住眼睛的画面,视频标题是“为战争的残酷感到触目惊心”、“看都不忍,何况亲历”。
观众真的被吓坏了!

如此追求“好哭”效果,自然主义地表现战场残酷,已经使影片具有了一种隐秘的、但绝不是不可感触的反战倾向。
抗美援朝战争是正义战争,没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就没有此后70多年的和平,我们要永远歌颂伟大抗美援朝战争!
02
前两天,写了一篇关于《狙击手》的影评,有人说我对这部影片做了“全盘否定”,这是不对的。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都同时包含着肯定和否定两种因素,正如不朽的马克思所言,“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反过来也是一样,在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
因此,“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不正确的,都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我不会对任何一部电影或其他文艺作品做出这样绝对化的评价。

关于《狙击手》,我的上一篇文章仅仅是对其中的一些军事细节进行了分析,就事论事地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逻辑与事实错误,不是对影片的整体性评价,更谈不上“全盘否定”了。
具体到张艺谋导演,如果以他过去的作品,如《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金陵十三钗》《三枪》《归来》《一秒钟》等建立一个参照系的话,我们会发现,《狙击手》的出现意味着他的创作出现了明显变化,甚至进步,至于这种变化是策略性的还是根本性的,又何必急于下结论呢?张导虽年逾古稀,但创作力依然旺盛,我们不妨继续跟进、继续研究。
还有一些人,质问我“为什么总是批评中国电影,不批评外国电影?”
这真是奇怪的问题。
我是中国人,最关心中国电影,最希望中国电影能够振衰起敝,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软实力,但我同时认为,没有批评就没有进步,中国电影存在的种种问题,正是严肃的电影批评长期缺位的结果,我也欢迎有理有据的反批评。
我对中国电影爱深责切,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希望中国电影越拍越好!

至于外国电影,主要是作为研究中国电影时的参照,并不是我研究的重点。我对外国电影的关心程度,远不如对中国电影,所以影评自然很少。
还有一些人,因为我批评一部电影,就认为我主张抵制这部电影,这也是一种误解。
我不主张抵制任何电影(当然我也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就我个人而言,我的体会是,多看才能提高鉴别能力,才不会被人带到沟里。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高度一万五千米”,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