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三评《解密》:精英主义及其他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作者|郭松民
01
《解密》,当然不是一无是处。
陈思诚试图在银幕上表现“梦境-潜意识”,不妨被视为一种值得鼓励的尝试,因为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确实比文字更适合探索这一领域。
但陈思诚的问题在于,他在表现梦境时,过于写实,失去了亦真亦幻的神秘感,并且也用得过多过滥。
也就是说,他把现实拍得像梦境,把梦境拍得像现实,最后,产生了不伦不类的效果。

不过,《解密》最令人难以忍受的,不是梦境拍得不像梦,而是从头至尾都散发着精英主义的刺鼻气味,如果不用“恶臭”这个词的话。
中国革命,是一场彻底的人民革命。亿万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百折不挠,前仆后继的奋斗,终于推翻了压在他们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
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理所当然地也应该是国家的主人。
然而,《解密》改变了这一历史叙述。
“老郑”在解放前夕像无头苍蝇一样去找希伊斯帮忙,以及解放后完全依赖容金珍破译密码,营救“中央首长”、保护“核试验基地”等核心情节,传递的暗示是很清晰的:革命成功了又如何?没有天才精英的介入,你们照样不能成事。
至于人民,他们不过是批判大会上的暴民,以及“封站”时茫然不知所措的庸众罢了。
在《解密》中,希伊斯和容金珍,是外在于历史、外在于政治的超凡存在。
希伊斯是犹太人,是没有祖国的“世界公民”。希来自欧洲,后来到了中国,再后来又去了美国。但无论是中共地下党,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都离不开他。
容金珍则是超越时代的。他本是世家大族浪荡子的私生子,释梦能力来自奥地利的“洋先生”,数学能力则是一种天分,后来得到希伊斯的培植,他的自闭倾向使他始终和现实政治保持着隔膜,他的天才也使他获得了凌驾于政治之上的特权。
而无论是希伊斯还是容金珍,都在不知不觉中创造了历史,取得了令“庸众”望尘莫及的成就。
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谁应该是国家的主人?一个社会的话语权、主导权应该属于谁?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问题始终存在。
1951年,著名演员石挥执导并主演了电影《关连长》,这部上映之后获得媒体喝彩的影片,把解放军塑造成了淳朴、善良,但没有文化的形象。战斗英雄关连长,看到文化教员带的一箱子书,就像没有见过世面的山里娃看到城里人的新玩具似的,充满了艳羡与自卑。

所以,毫不奇怪,影片很快就受到了批判,因为石挥无意中触碰到了一个尖锐的时代命题:谁才有资格主导这个刚刚诞生的年轻共和国?是创建了新中国的人民,还是那些呆在大城市里等待大军进城的“有文化的人”?
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清醒、坚定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是艰苦的、卓有成效的。
但八十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一个突出标志,就是那种沉着坚毅,能文能武,“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革命军人形象(如《东进序曲》中的黄主任、《英雄儿女》中的王政委、《年轻的一代》中的林厂长等)从影视作品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没有文化,满口粗话的“泥腿子将军”,从《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到《亮剑》中的李云龙,莫不如此。

“泥腿子将军”成为主流形象,本身就为“文化精英才应该是国家的主导者”预留了空间。
《解密》不过是把这种唱了近四十年的老调子用特别尖利的声音重新吟唱一遍罢了。
斗争远没有结束,只是在目前这个阶段,精英占据了绝对优势。
所以,还是毛主席的话一针见血:“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02
前两天,《评《解密》:陈思诚如何讲述新中国往事?》【点击阅读】发出之后,有同学提了一些问题。这里,对文章涉及到的几个观点,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是,有同学说,“将解放表现为沦陷恐怕并无此意”。
这位同学可能太善良了,或者有点不太熟悉电影语言,我之所以在文章中得出如此结论,主要是根据陈思诚在电影中的呈现,而非对他做诛心之论。
一个最简单的区别是:“沦陷”是普遍的恐慌,各个阶层都恐慌,而“解放”则是只有那些即将被推翻的剥削者、压迫者恐慌,广大的人民却欢欣鼓舞。

以中国早期电影《乌鸦与麻雀》为例。这部电影拍摄于1949年1月,刚好是上海将要解放但还没有解放的时刻,所以相当生动地反映了上海市民的真实心态。
在影片中,一方面,是国民党国防部的小官僚侯义伯和他的老婆惶惶不可终日,企图榨取最后一根金条,然后逃亡台湾;另一面,小商贩萧老板、中学教员华洁之、报馆小职员孔有文等普通市民,却对解放军的到来满怀期待,他们并非革命者,甚至也不算进步群众,但凭着基本的生活经验和直觉(如看到侯义伯的恐惧)就意识到一个更加美好的“新的时代要来了,新的社会要来了”,因而欢欣鼓舞。
在《解密》中,有什么人为即将到来的解放而欢欣鼓舞吗?没有!所有的人都是一副大难临头的样子。并且,就连过渡性、交代性的市民欢迎大军进城的镜头也没有。
如此表现南京解放,不是把解放表现成沦陷,又是什么呢?
二是,有同学说,“所谓被绑架、被圈禁我也看不出来,电影中加入701完全是容金珍个人的选择。”
“绑架”、“圈禁”,当然不是在刑事意义上说,而是在“个人是历史的人质”意义上说的。
“个人是历史的人质”是意大利著名导演贝托鲁奇在谈他的电影《末代皇帝》时说过的话,意思是人无力左右自己的命运,无法摆脱荒诞与无力的状态,自以为逃出一个藩篱,却又进入了另一个藩篱。
贝托鲁奇的这句话,不无替溥仪洗白投敌责任的用意,但却被一些中国电影导演接过来,用来表现文化精英在中国革命的洪流中无力左右自己命运的状态,他们事实上把这句话偷换成了“个人是革命的人质”,比如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张艺谋的《活着》、田壮壮的《蓝风筝》等等。

与这句话相对应的是,他们借用冷战时代好莱坞抹黑社会主义阵营的手法(如《日瓦戈医生》(1965)),把革命胜利后形成的新秩序,表现为一种“被占领状态”,人与人之间充满戒备与猜疑,处处都潜伏着危险,每个人人都没有安全感,所有的人都没有保障。
无论是在早期的伤痕电影《小街》《巴山夜雨》中,还是在新世纪出现的新伤痕电影《归来》《一秒钟》中,“被占领状态”都是一种基本的时代氛围。区别仅在于,早期的伤痕电影,“被占领状态”还仅仅是“十年”,在新世纪之后的电影中,“被占领状态”则渐渐变成了整个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因为“伤痕文艺”(不仅是电影),已经从“用文革前十七年来否定文革”的旧伤痕文艺,合乎逻辑地发展到了“用旧中国否定新中国”的新伤痕文艺了。

在《解密》中,南京解放后的气氛,正是这样一种“被占领状态”,陈思诚生怕观众会误解,还特意用“南京被XX党占领”的字幕来提醒一下大家。
且看“老郑”(陈道明 饰)探访小黎黎(吴彦祖 饰)一家的桥段:“老郑”的态度是和蔼可亲的,但小黎黎一家的态度却是小心翼翼的、惴惴不安的、甚至带有讨好与巴结的神情,全无胜利重逢后的轻松与欢喜。
正是小黎黎一家的态度,暴露了他们的真实处境以及他们与“老郑”之间的真实关系。
所以,当“老郑”在去厕所的路上看到了容金珍,轻描淡写地对他说,“明天到我那里去一趟”,容金珍回来后简单地对养父说“那个人让我跟他走”,都没有任何多余的废话,拒绝是不可想象的,占领者的话就是绝对命令。

三是,有同学说,“……的形象并非黑暗组织。这是一部秘密战线题材的片子,因此围绕容金珍(包括老郑)的相关呈现都是高度保密化的。”
“秘密战线”是个很方便的理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组织表现得很冷酷、很黑暗,但这是不对的。
秘密工作,很多时候都是靠一个人在敌人的内部单独作战,上级无法监督,周围没有战友,如果没有高度的政治认同、情感认同,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所以,秘密战线更需要上级的关怀、同志的友爱与支持,需要坚定的政治信仰以及对祖国和人民深厚的情感,绝不是一切都冷酷无情,只有死亡和算计。

那些经得起时间检验,得到观众认同的优秀“谍战剧”,如苏联的《春天的十七个瞬间》,朝鲜的《无名英雄》,中国的《永不消逝的电波》《羊城暗哨》乃至《保密局的枪声》等,都用点睛之笔揭示了这样的道理:一个温暖、光明的组织才是“谍战英雄”们出生入死,建立功勋的根本保障。
遗憾的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谍战剧”的画风为之一变,在《暗算》《东风雨》《风筝》,甚至口碑不错的《潜伏》中,“组织”都成了一个黑暗的“麻烦制造者”,在《解密》中,更成了令人窒息与恐惧的压迫性力量了。
03
最后,顺便谈一下“统一战线”的问题,因为有同学认为,我对《解密》的批判“恐怕有违我党统一战线的工作方式”。
这里我要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是一个政治斗争范畴内的概念,是一个政策和策略问题。而在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所进行的斗争中,并不存在统一战线的问题,也不适用“统一战线”的概念。
为什么呢?
因为思想、文化斗争,根本特征是尖锐性和原则性,在这些斗争中,追求真理才是最重要的,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没有妥协、让步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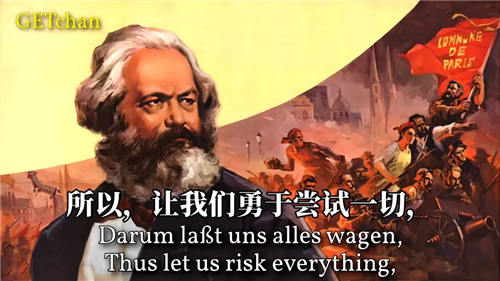
熟悉《共产党宣言》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宗明义,用了很大篇幅,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因为两位革命导师不懂统一战线吗?
当然不是!统一战线的概念,就是恩格斯最早提出来的。
历史证明,革命导师批判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是绝对必要的,非如此,就不能划清与这些机会主义思潮的界限,就不能阐明共产党人自身的立场和主张!
与其用所谓“统一战线”作为逃避尖锐的思想、文化斗争的借口,还不如重温一遍马克思恩格斯的教导吧——“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