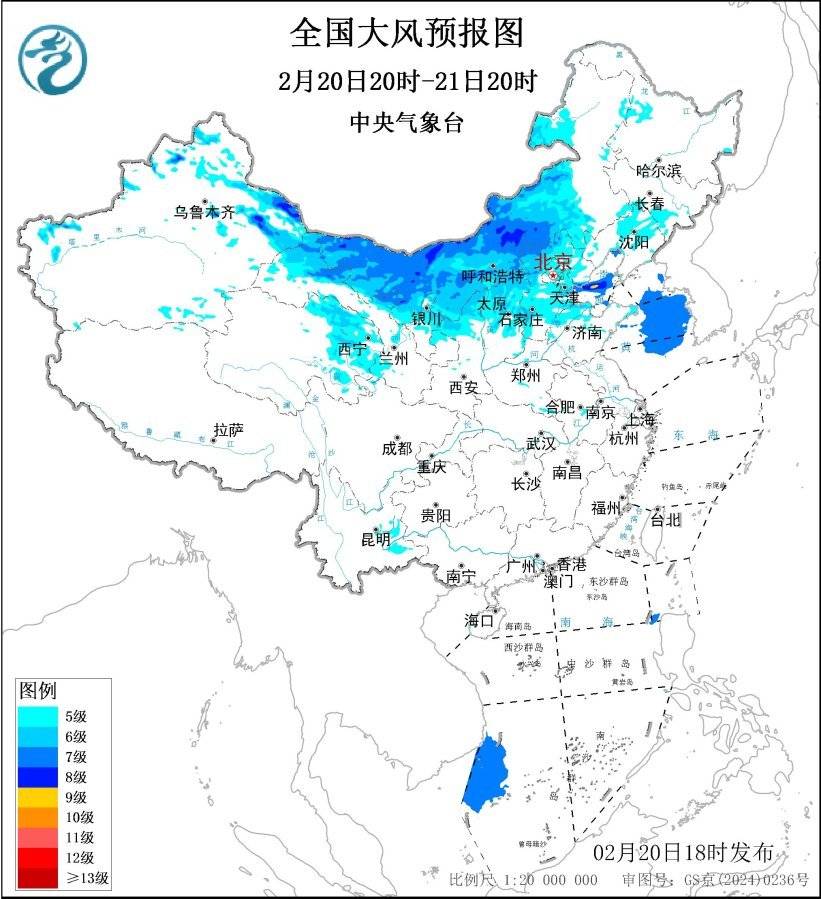一个教书匠凭什么把黄埔精英打得满地找牙?
为什么一个师范生能战胜一众黄埔精英?
渡金沙、过赤水、驱日寇、平美帝,为什么教员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艾跃进教授曾经分析过,教员的战胜率高达99%。虽然,经学界考证,教员的战胜率是90%,但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要知道,教员面对的都是当时蓝星上的头号玩家。
离谱程度好比,一个中专生冲进北大期末考场,然后考了年级第一。
教员到底是怎么学会打仗的?
教员自己是这么说的:
“我这个人是不会打仗的,我的职业是教小学生的小学教师。谁人教会我打仗呢?第一个是蒋介石,第二个是日本皇军,第三个是美帝国主义。”
教员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但这样一个答案似乎还没有触及到灵魂,蒋介石、日军、美帝,谁又不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呢?为什么还是成了教员的手下败将?
或者说,教员作为一个普通人,不靠背景、不靠天赋、不靠阴谋手段,赢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我想,答案只在一个字——无。
1
兵无定势
水无常形
我们从小被教育要成为坚定不移的人,但教员却相反,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善变”的人。
这种善变在教员年青时便初现端倪。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而十五岁的教员书读的断断续续,时不时就要听从父亲召唤回家种地,快三十岁的教员还在北漂,思想也飘忽不定。
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教员也往往是第一个作出改变的人:
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里,写道: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率。和众多革命者一样,此时的教员更倾向于温和的改良派。
但是,仅仅一年后,教员的暴力革命思想就觉醒了。
1920年,毛泽东在蔡和森、萧子升的信中写道:
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
直到7年后,大革命失败后的八七会议上喊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强音。
我们从上帝视角看,这样的转变似乎没什么难的,服软不行就来硬的嘛。
但要知道当时全党乃至陈独秀同志都对国民党政府抱有幻想:
6月,当时党的领导层和共产国际代表开会商讨对策,决定:武汉的工人纠察队自动缴械。
7月,中央通过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
“为了减少冲突,共产党的部长可以暂时离开政府”;“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受国民党的领导”......
我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在我们的研究领域中一直有一片空白,那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萨特,等等,无论是存在主义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人人都想改变世界,但无一人提出暴力革命,甚至连思辨都不曾思辨。
秋收起义攻打大城市失败,便立即转向农村,建立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便“放弃”中央根据地,战略转移,北上长征;教员是第一批觉醒要拿起枪杆子夺取政权的人,也是第一批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人......
教员的思想仿佛一辆疾驰的马车,在前方遇到障碍时,总能迅速调转方向。
在宏观的战略上,教员是最擅长“变化”的那个,到了具体的战术上,教员的“善变”便集中体现为10个字“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就像我们现在年轻人经常挂在嘴上的那句“不行就算了”。
但是教员的“算了”不是大方向上的“算了”,面对国民党四面围剿、日军的精兵锐器、联合国军的来势汹汹,教员想的从来不是投降算了,而是PlanA不行,就上PlanB,PlanB再不行,就来PlanC嘛。
正所谓“兵无定势,水无常形”。
为什么教员的“马车”在蒋介石、陈独秀、王明等一众“高头大马”间,总能最快最精巧的转向正确的方向呢?
正是因为教员的“无”,教员思想中的“无”让他的马车载重最轻,相比香车宝马,成了机动性最强的那辆。
“无”不是说教员没有思想,而是教员“不执”,不执著于任何固有思想、已有之物,方能因时而变、随事而制。
当兵当了一半可以放弃,儿时当老师的梦想可以放弃,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可以放弃,苏联攻打大城市的成功经验可以放弃,好不容易建设的中央根据地可以放弃,就连延安也可以放弃,“无”了既有之物,才能迎来新生之物。
这样“无”的特质不是上天的恩赐,而是教员的客观条件决定的。
相比国共一众领导人,教员的学历、出身都不算好,尤其是在军事方面。
在土地革命时期,曾有人批评教员“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但据教员自己回忆,当年他还甚至没看过《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看是看过,但指挥作战时统统忘了。
正是因为没有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教员的思维反而不容易掉入教条主义的陷阱,而是能够根据客观形势,采取最合适的战略战术。世界局势发展永远是瞬息万变,相对应的,我们的思维也应当是不断调整的,战争有战略战术,人生亦有战略战术。
很多时候,我们受到的教育太系统、太根深蒂格,反而像王明一般陷入了教条主义的窠臼。
如果教员是一个出生在六十年代的青年,他大概率不会挤破头扎进国企,而是会投身改革开放的创业浪潮;
如果教员是一个出生在八十年代的青年,他大概率不会再固守原籍,而是会大胆走出国门闯荡;
如果教员是一个出生在九十年代的青年,他概率不会高分冲击985的土木工程,而是乘上互联网的春风;
如果教员是当代的青年,即使面对经济下行、学历贬值、创业艰难,我相信他也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当下的困境,而是旧有的思维,只有对于旧的事物不执,才能把握住未来的事物,才能克服现在的困境。
2
无产阶级
无惧无畏
我们都听过“无产阶级的力量是伟大的”,那大家有没有想过,最贫穷、最无知、最底层的无产阶级哪儿来开天辟地的洪荒之力?
解开无产阶级力量的钥匙就在这个“无”字。
因为财富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具有辩证性,钱也不是越多越好。
最典型的就是两车对撞的游戏,一辆法拉利和一辆五菱宏光对撞,谁先让开谁就输了。
最后赢的一定是那辆连安全气囊都没有的五菱宏光,因为在死亡面前,资产只会成为人的负累,因为拥有富足美好的生活,所以畏惧死亡。
在这种直面死亡的游戏中,法拉利一定会输给五菱宏光。
不是输在装备,而是输在人。
而战争恰恰就是人类最宏大的死亡游戏。
相信玩过棋牌对弈游戏的朋友都知道,先手优势有多重要。
主动进攻、先发制人,几乎是古今中外所有兵书都强调的作战原则。
人类世界有很多游戏规则,有时我们要谦让、温和,但在战争这种只有一个赢家的游戏中,主动进攻是绝对法则。
无产阶级因为无资产、无财富,无现实世界中一切幸福,所以不留恋美好、不珍惜此生,无惧生死。在生面前,他们事事赢不过资产阶级;但在死面前,他们拥有毁天灭地的力量。
此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奉行的“弱民之道”便是将搜刮财富的界限保持在民众刚好吃饱的状态,决不能多进一步,若是民众手中一点余粮没有,伸头也是死,缩头也是死,此时潘多拉的魔盒就要打开了——对生的强烈渴望转化成的巨大的革命力量。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在总结志愿军胜利之道时,教员是这么说的:
敌人是钢多气少,我们是钢少气多。
这个气就是无产阶级挣脱枷锁、解放全人类的勇气。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教员就指出:
“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由于他们集中和经济地位低下,又受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特别能战斗,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农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特别是贫农和其他半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由于他们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剥削最深,都要求革命,是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
越是被压迫,就越是具有反抗压迫的力量,这就是无产阶级战争制胜的辩证法。
教员一生为无产阶级、为贫苦大众的解放而奋斗,但教员的出身却称不上“无产”。
1936年,教员与斯诺谈话时是这么说的:
“我家有15亩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60担谷。一家5口一年共吃35担——即每人7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25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7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
教员出生于富农的家庭,但他满怀着对无产阶级的同情,放弃了优良的家境,选择成为一名无产者。
1920年,教员的父亲毛顺生病逝,教员安排弟弟处理了家中所有资产,他是这么说的:
“家里的房子可以让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
除了主动散尽家财外,教员还是一个天生的无产阶级斗士,或者说老师和家长眼中的“刺头”。
教员曾回忆说,
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
反抗的基因似乎是与生俱来的,随着教员年龄和父亲资产的增长,教员越来越激烈地与父亲抗争起来,直到十三岁时,矛盾爆发。
有天,毛顺生当着宾客面骂教员懒惰无用,教员便负气离开了家。
这种事我们小时候也都发生过,过个小半天,被父母抓回家后,抗争便结束了。但教员的画风却异于常人......
教员冲到池塘边生,威胁父亲再靠近就跳河,以此争得了与父亲平等谈判的机会,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父亲要向儿子赔不是,并且答应不打人,儿子则要屈一膝下跪。
这样一件小事,让年幼的教员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
若你公开反抗来保卫自己的权利,敌人就客气一点;当你怯懦屈服时,敌人只会打骂得更厉害。
四十多年后,在中方多次警告后,麦克阿瑟仍判定中国不敢出兵与美国对抗,骄傲地向鸭绿江开进时,他不会想到,他们的敌人是十三岁时便能以死争平等、争尊严的教员,和四万万无惧无畏的无产阶级战士,他更不会想到自己将会被这帮“穷鬼”打得怀疑人生。
3
无为之为
大道为公
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教员第一次提出了“政治建军”思想。而与教员相比,旅日精英、黄埔校长蒋介石就输在了“政治”二字上。
首先,什么是政治?
《新华字典》的解释是指阶级、政党、民族、国家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大家常识中的政治,是中学课本上背的体制制度,是大学里最浪费时间的思政课,也是大多数学生最不感兴趣的学科。
教员是这么解释政治的:
政治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
所谓政治,就是交朋友,就是家庭和睦,就是同事关系融洽,往大了说就是阶级、政党、民族、国家之间关系都处处好。
所谓政治建军就是,大家关系好了,军队也就好了,也就能打胜仗了。
大家都知道,蒋介石有个“微操大师”的称号。
蒋介石的手下个个是黄埔精英,不少还经历了北伐和抗日的洗礼,带兵打仗的能力都很强,且当时的指挥信息传递速度手段都不行,蒋介石不傻,他的“微操”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
土地革命时期,蒋介石的“驱虎吞狼”之计便昭然若揭,追击红军的同时搞掉王家烈。看似一箭双雕,实则因小失大。王家烈被搞,刘湘、龙云、刘文辉等人便开始了集体划水。
解放战争也是如此,一开始老蒋坐视阎锡山和刘邓大军缠斗,后又逼马法武强攻平汉路。看似算计了晋军、西北军,但却让国军内部更加离心离德。“小诸葛”白崇禧看清形式后,手握重兵却仍是全场打酱油,就是典型。
在旧军阀军队基础上组建起来的国军,内部自然是各怀鬼胎、暗潮涌动。如果自己的手下都不值得信任,那事事就只能亲自“微操”了。
而战争的关键之一便是作战指挥体系,不熟悉前线、不熟悉部队的将领越级指挥,只会让部队错失良机、军心涣散。
淮海战役中,被困徐州的杜聿明,制定了从西面突围的作战计划,并成功突围向西南撤退。
可就在此时,蒋介石竟然派出飞机向杜聿明快递了一封亲笔信,要求杜聿明不准撤,马上转头去救黄维兵团,此时杜聿明就知道“完了”。
果不其然,在蒋介石的精准微操下,黄维兵团和杜聿明兵团谁也没跑了,数十万人全部被歼。
与之相反的便是教员的指挥,大开大合,只把大方向,让将领们放手去干。
因为教员与将帅间充分信任,将帅与士兵间充分民主,所以同样的一道命令下下来,在国军和共军内部执行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我不大赞同现在的政治教育,只背体制、制度是完全不够的,哪怕就是一样的政党、一样的制度、一样的指挥体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事情的结果也会完全不同。
我们的政治教育缺乏了最关键的一课——如何争取人心,或者说如何团结更多人?
很多人都知道教员读书时一战成名的战绩:
1918年,教员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2000名溃败的士兵即将涌入长沙城。长沙城人心惶惶,还是学生的教员挺身而出,把长沙两百名学生组织起来,并争取到了几十名警察和城里财主们的支持。教员带着这两百多人,埋伏在城外,借助鸣放鞭炮,吹鼓呐喊,运用心理战,让2000名武装士兵缴械投降。
每每读到这个故事,都不由感叹教员的勇气和智慧,但中间还有关键一点,却常常被人忽视。
一个中专生,凭什么能说动全校师生,乃至警察和财主呢?
哪怕现在大学社团想搞个内部活动都不容易,更何况是让几百人陪自己去送死,让素不相识的豪绅为自己慷慨解囊呢?
这是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但教员却做到了,而且未来,他将团结几亿人,乃至几十亿人,踏上革命之路。
这才叫政治,这才叫政治家,而蒋介石之流只能称为政客。
蒋介石不可谓不聪明,为了得到美国的支持,能够立马翻脸,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所谓道义,在权利面前只是手段,合则用、不合则废。
我在体制里混了多年,看过不少蒋介石之流,白天看《资本论》,晚上看《厚黑学》,攘权夺利、无所不为。
在他们眼中,人心复杂,人性黑暗,唯有金钱和权力可靠,自以为靠着圆滑世故便能步步高升。
却不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权力和地位从来不是算计来的,而是党和人民的选择。阴谋算计或许能得意一时,却绝对经不起历史的考验。
蒋介石能用金钱和官位收买人心,二十多岁的穷小子教员靠的什么“收买人心”?
靠的是道义。
不是教员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就能忽悠到几百号人,那叫传销洗脑。是教员长久以来的人品让师生们信赖他,信赖他的师生们又将人脉拓展到了校外的警察和富绅。
这才叫关系网,品德高尚的人,吸引着众人与他交往,就像众星拱月般,星光又反射开照亮了更多的星星围在月亮周围。而不是吃吃喝喝、钻营取巧、权力交换的庸俗关系网。
可能有人觉得,你现在说教员人品道德高尚,是春秋笔法。
有的键盘侠在网上挥斥方遒,你让他上前线他是不敢的,你让他捐款他怕都是要嘚瑟几下。
而面对金钱和权力拷问时,教员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无私与伟大。
教员一家捐出的不仅仅是钱财,从1929年,小妹毛泽建牺牲开始,到1950年,毛泽东同志的儿子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毛家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六位亲属——毛泽建、毛岸英、教员的妻子杨开慧、大弟毛泽民、幼弟毛泽覃、侄子毛楚雄。
教员,即使是在1932年被架空,几乎失去了一切权力,也没有选择躺平或是变格,依然一刻不停息地思考中国革命的未来,看了很多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教员团结人心靠的从不是权术,而是大道。
所谓大道至简,无为而为。
大道为公,当一个人心怀天下,达到忘我、无我的境界时,他的行为便于大道相合,领袖之位不是教员谋求来的,
当教员选择了天下时,天下也便选择了教员。
而当蒋公在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蒋公。
与其说蒋介石摆在战略战术上,不如说败在政治上,败在人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