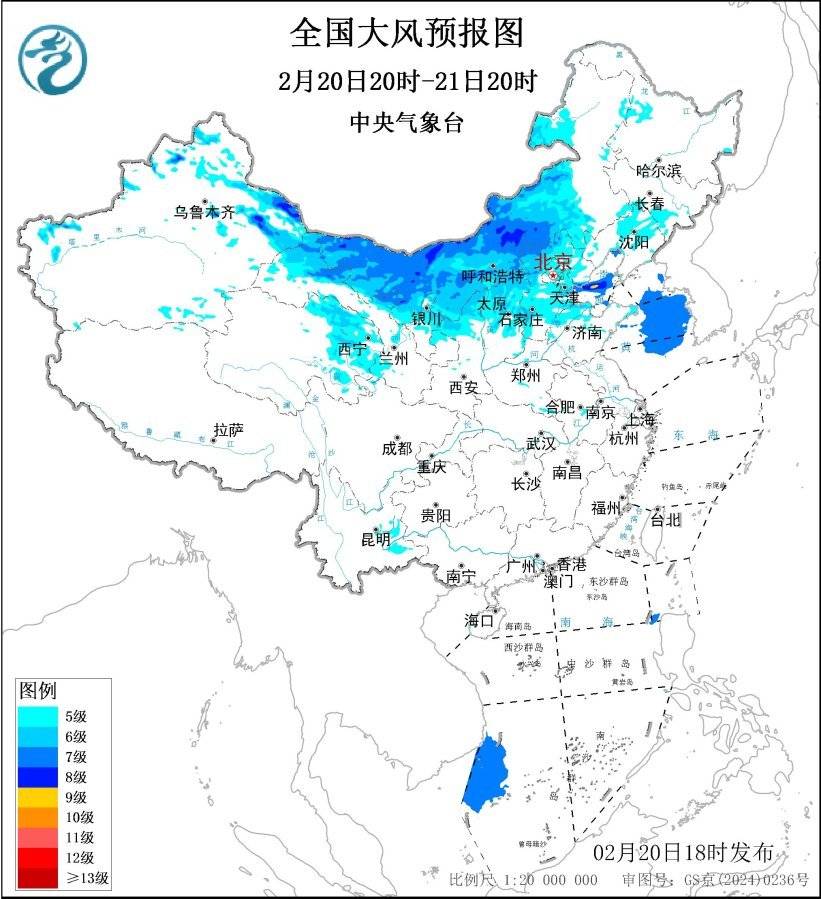读《杂食者的两难》:食物中的政治经济学
食物主权按
时下,如何健康饮食成为困扰许多人的问题。我们到底该吃什么?这也是《杂食者的两难》这本书要探索的中心问题。作者迈克·波伦认为,杂食者的两难其实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一直都存在,只是对于原始人来说,杂食者意味着人们在自然界有更多选择,但也面临着诸多风险;而对现代人来说,这个两难似乎是,在超市中购买食物的两难抉择:有机食品还是一般食品,本地产品还是进口食品,野生的还是养殖的,吃素还是吃肉等等。随着食物体系越来越产业化,人们该如何解决吃什么和怎么吃的问题?本书通过对食物链的追本溯源,为这个问题的解答提供思路。
作者在书中追溯了三条主要的食物链:产业食物链,有机食物链以及采猎食物链。作者关注的重点是产业食物链,这一部分主要追溯了以玉米这一食材为基础的产业食物链的发展历程;在有机食物链部分,作者讨论了“工业有机”这个概念,包括什么是“有机”,“工业”与“有机”的矛盾;而对采猎食物链的探索,作者更突出的是哲学性的思辨和方向性的启发,认为人们吃什么怎么吃,既是一种农业行为,也是一项生态和政治活动。
作者|9527报道
责编 |丁卯
排版|童话

迈克·波伦Michael Pollan
迈克·波伦 Michael Pollan,美国饮食作家,新闻学教授。代表作《杂食者的两难》《烹》《为食物辩护》《吃的法则》被奉为饮食写作的典范。他更像是一位热爱田野调查的美食侦探,从农场到超市,再到制作出各种美食的厨房,研究食物从产地到餐桌的过程,同时对饮食文化背后的人类社会困境进行思考,为工业化食物链下的人类指出一条古朴、美好且真实可行的路。
1
产业食物链:以玉米为例
玉米的产业食物链充分展现了现代资本主义农业为寻求资本增值而形成的“占取主义”。所谓“占取主义”,即农业生产中的不同环节被工业资本改造并纳入为工业体系的下游产业,又以农业投入品的形式,被重新整合进入农业生产的必要环节中去。通过这种整合,资本形成了对农业不同生产环节的经济剩余的占取,不断提高农业活动中的资本化程度。
玉米是少有的在进行光合作用时产生4个碳原子的物种,这种“四碳植物”固定碳的效率比其他植物更高。也就是说它能固定更多的能量,代表了更高的经济效益,让它在同其他生物竞争时具备更多的生存优势(比如一颗玉米种下去,可以产出150-300颗玉米粒,而一颗小麦顶多产出50颗小麦),又因为自身演化的突变,如果不被剥开外壳就难以播撒种子,从而更易于被人类所控制。回溯种子的历史,种子由于其生物性,在知识产权制度诞生早期的工业化时代,曾长期被排斥在知识产权的认定范畴之外。但自80年代至90年代,资本通过一系列游说和司法途径完成了对农用种子的私有化。20世纪初期,美国的玉米育种者就想出了严格控制玉米生殖的办法,避免种子被复制。自交系杂交后子二代产量的杂交优势使得产量比亲代高很多,但到第三代产量却一落千丈,这既保证了玉米生殖和性状的稳定性,又避免了种子被复制,从而催生了种子专利,农民不得不每年买新种子,不得不依赖商业机构。
在生产过程中,农民进一步发现杂交玉米要高产,就需要密集种植。玉米在生长期,为了竞争阳光,茎会变得细长,容易被风刮倒。为了培育出茎更粗壮稳固的杂交玉米,就需要施加更多的化肥。二战结束后,美国囤积了大量过剩的氮类化合物,它们本被用于生产炸药,如今美国政府将它们转化为化肥。但是产量提高了,农民却愈发贫困。因为产量虽然高了,政府却没有保证农民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的保护政策,原有的以抵押和贷款方式进行平仓的方式被调整为直接补贴差额。同时,一旦官方以“让美国谷物在世界市场上更具竞争力”之类的口号人为调低目标价格,农民为了维持生活水平、支付账单、偿还债务,就只能通过密集地投入化肥等工业投入品来提高玉米产量以减少损失。
通过占取生产农业投入品的农业上游产业,资本完成了对农业生产者劳动报酬的压榨,资本社会因此在造就了一批投资回报率极高的垄断巨头的同时,也催生了背负巨额生产性债务和破产风险的广大农民。
由此,玉米充当低廉的原材料在农业补助政策下流入各个下游产业,有的成为工业能源原料,还有的进入现代工业化管理的饲养场,成为牲畜的标准化口粮。自“二战”以来,人类食用的动物进入了与以往农场及牧场的差异极大的地方——集中型动物饲养场(Concentrated Animal Feeding Operation,简写为CAFO),这种模式直接由美国政府补助生产的廉价玉米催生。表面上看,集中型动物饲养场把动物集中起来用便宜玉米喂养的经济逻辑非常难以争辩,因为这让原本只有特殊场合才能出现的肉类,变得非常便宜而且丰富,使美国人三餐都有肉吃。但集中型动物饲养场在短暂的历史中产生了太多的环境与健康问题,包括水污染、空气污染、有毒废弃物排放、新型的致命病菌。
在传统的农庄中,农作物的残余可以用来饲养牲畜,而牲畜的排泄物可以作为农作物的肥料,基本不存在“废弃物”。但在动物饲养场,工业化生产衍生出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农场的肥料从哪来(现在必须用化学肥料补救),以及饲养场产生的污染问题如何解决(目前几乎没有补救措施)。今日,在与养牛业相关的环境破坏中,最严重的事件大都发生在工业化饲养场。现代工业追求的“速度”或者说“效率”,用更高热量的饲料——玉米来喂养,缩短肉牛的生命周期。同时,由于反刍动物进食玉米容易患胀气,并诱发大量其他疾病,有些牛甚至会因此死亡,并在饲养场传染各种疾病,因此又不得不使用抗生素。数十年来,美国政府一直想方设法地消化过剩的玉米,方法就是将这些玉米送入动物的消化道,将玉米转换成蛋白质。但这种用玉米喂养的肉类却并不十分健康,因为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ω-3脂肪酸含量较低。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吃牛肉所引起的健康问题,事实上是来自被“玉米喂养的牛肉”。
除去牛肉,人们还消费了大量以玉米为原材料的合成食物。食品科学的力量就在于能够把食物分解成其中的养分,然后用特殊方式再次组合,如此启动了人类演化的开关,愚弄了杂食人类天生的食物筛选系统。“湿磨坊”就充分展现了现代资本主义农业的这一面——“替代主义”(所谓“替代主义”,指在农产品加工阶段,工业活动所带来的附加值比例陡增,同时农产品作为工业投入品的一部分逐渐被“非农成分”所取代。),它将玉米分解成各种碳水化合物,并且重组成上百种诸如酸类、糖类、淀粉类和醇类等有机化合物。
当食品工业界掌握了分解玉米并合成有机化合物的技术后,人类的食物终于可以摆脱自然的限制:如果某种作物歉收,很容易就能找到其他替代品合成相应的化合物;人们甚至可以突破胃容量的限制,发明出了人类无法消化的抗性淀粉,提高了胃纳的上限。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食品加工者把玉米转变成高果糖玉米糖浆,它不仅存在于饮料和点心中,还存在于西红柿酱、芥末酱、面包、谷物片、调味料中。在精明商人们的筹划中,原本苗条的250毫升玻璃瓶装可乐,换成了600毫升的圆胖瓶;薯条和爆米花都有超大份选项。
于是,农业资本主义的“替代主义”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见证了美国人肥胖率的攀升和高耗能农业生产体系的发展,这些必要的因素为工业食品巨头奠定了财富繁荣的基础。
一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糖和脂肪中单位热量的价格下跌,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阶层中,肥胖和糖尿病的现象越发普遍起来,产业化食物链让高能量的食物成为市场上最便宜的食物(以同样数量的金钱购得的热量来计算)。同时,被机械所拼装而成的“湿磨”能够日均处理上万吨玉米,但亦如其他现代工业巨兽,其生产过程却异常耗能,如需制作出含1卡路里热量的加工食品,就得消耗10卡路里的化石燃料。
另一方面,在加工食品产业链里,处在农业生产一线的种植者只能获取非常微薄的利润。食品加工界的共识是越复杂的工序意味着越多的产业附加值。未经处理的食物如鸡蛋,花1美元会有0.4美元返给养鸡业者;相较之下,农民只能从1美元的玉米甜味剂中得到0.04美元,而剩下的钱大部分要进到企业的腰包里。
2
有机食物链:
从牧草和精细管理放牧说起
与集中式畜牧业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是精细管理式的放牧,它呈现出动物与牧草和土壤之间复杂和开放的互动关系。反刍动物在排泄时散播并滋养草籽,在夏季最干燥的时候,反刍动物承担了制造土壤养分的工作,在瘤胃中把干燥的植物分解成基本的养分与有机物质散播出去。“短暂的停留可让动物凭着本能找寻新鲜草地,而不会被自己的排泄物污染。在相同面积下,适当管理的牧草甚至比玉米饲料能够提供更多营养(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又由于多样性高的草地,有多种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植物,所以善加运用每寸土地上每年生长季节中的每一刻,就可吸收更多阳光,产生的生物质也能超越单一种植的玉米田。
但即便牧草有这些潜在优势,却仍不敌玉米田。因为玉米能够融入工业化生产,而牧草则不能。玉米等谷物可以储存、便于携带、能够交易。由于谷物能够累积与交易,因此也是一种财富形式。谷物也可以被当做武器,供给过剩的国家,总是能制裁谷物短缺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中,政府长期鼓励农民种植比实际所需更多的谷物,以备饥荒时所需、将劳动力转移到其他工作中、促进贸易平衡,以及整体而言为了增加国力。在产业化经济中,种植谷物支持了其他更大的经济行业:化学与生物科技产业、石油产业、汽车产业、制药业(没有药物就无法让集中型动物饲养场中的动物保持健康)、农业综合企业以及贸易平衡。种植玉米有助于驱动让玉米产量增长的产业体系,难怪政府会进行大手笔资助。
相比之下,牧草不是产业化商品,牧草的质量也易随着地区和季节发生变化,甚至农场本身也是变因之一,精细管理式的放牧主要仰赖的是农夫对农业生态系统的观察和经验基础,而非密集的资金(或能源)。正是由于种植牧草的技术中牵涉到许多变因,还有许多区域性的知识,因此难以系统化。悉心管理的放牧草地会忠实依循生物逻辑运作,因此难以与产业化逻辑配合。政府也通常不会给牧草农夫签支票,因为作为一个能够充分自给自足的系统,精细管理的生态农业也很少购买农药和肥料等生产投入,因此对于支持农业综合企业、制药行业和大型石油公司自然毫无贡献。
那么,“是谁正在从事所谓的知识经济?是那些真正观察农场而获得知识的人,还是从魔鬼的柜子中拿出神秘药水的人?”产业食物链与有机食物链的对立,表现为两种农业生产知识体系的对立,表现为产业化农业的“闭合性”与生态农业的“开放性”。
所谓“闭合性”,即把农业生产看作是简单的成本和利润的计算,等式的一端是所有的农业资本(种子、肥料、饲料等)所构成的各类生产投入(input)的原子,等式的另一端得出农产品产出,从起点到终点,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手段服务于目的,因果分明,层次清晰,所有的生物在这个等式中不被视为有机,“鸡是生产鸡蛋的机器”,“牛是生产蛋白质的机器”。在这个基本的工业逻辑下,所谓的效率就是利润最大化,衡量效率的指标在于每单位土地或每单位劳动力的产出。而当“闭合性”产业化成为农业发展的范式时,外部于生产等式的要素就成为了所谓的废弃物。
“开放性”的生产理念则指出农业生产所涉及的每一个生命过程和生物都构成一个有机完整的“子整体”(“holon”),每个“子整体”之间又相互耦合联结。作者在造访有机农场时观察到,家禽、牛猪、牧草和森林共同构成一个内在有机的整体,家禽啄食牛粪中的蛆,在清理虫害的同时,又补充孵化鸡蛋所需的蛋白质,通过移动鸡圈,鸡粪散布在整个草场,成为重要的氮肥来源。在这个模式中,像“闭合性”产业化的那种分明的主次关系和因果逻辑开始变得模糊,“如果草地是生产鸡蛋的系统,那么牛粪和牛就应该是服务于这一目的的手段,但同时家禽对草地的清理滋养又是维持牛健康生长这一目的的手段”,鸡是产品的同时又是副产品,动物粪便也不再是废弃物。按照农场主的话说,人们可以通过仿效自然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相关性,善用生物的生理特征。在生态农业的逻辑下,将生物的粪便转化为鸡蛋本身就是效率,在一片土地上同时经营数个生产系统同样也是效率。
为有机农业打下哲学基础的霍华德爵士(1873—1947)曾批评支持农业工业化发展中产生的技术还原论和科学实在论,即把土壤肥沃还原成一份植物生长所需的氮、磷、钾。
问题在于,一旦科学把某个现象简化成一些变量,不论这些变量多么重要,人类都会把变量以外的事情忽略,然后假定所有要考虑(或至少是重要的)的东西都在这些变量中。
从历史的角度看,以这套工业化农业知识体系为基础的西方现代农业(一个农民养活129个人的生产模式)建构于西方新旧殖民主义的食物体系之中。自1870年至一战前夕,由英国主导的殖民运动将大批本国边缘化的城市工人群体和农民向美洲转移,欧洲人通过驱逐原住民以获得巨量的农业土地资源。面对地广人稀的现状和廉价的生产以及运输成本,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单一种植模式孕育而生,被主流所广泛接受的农业效率标准(单位劳动力的产出)就诞生于这一背景之中。第三次技术革命为这一“封闭性”产业化模式进一步赋权,农业技术的进步和推广实际上最终服务于资本对农业上游产业的控制,使得农民只能使用“他人”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从而方便资本对农民生产的经济剩余的剥夺。
因此,作者再三强调有机农业的反体制和反资本的政治意义。有机农业不应只是一项农业计划,也应是一项社会革新计划。这些观点在早期有机运动中得到反映,譬如由于道斯化工、孟山都两家公司除了制造杀虫剂之外,也制造凝固汽油弹,以及美军在东南亚战争所使用的“橙”剂,有机农业反对使用农业化学药剂的同时,也拒斥战争武器。
同时,作者也对所谓的“工业化有机农业”做出评价。对于现代人而言,在“有机全食”超市中购物往往能够萌生出一种田园牧歌的幻想,食物的标签和包装激发了消费者的幻想,将寻常的食物提升到一种混合了美学,情感甚至政治的经验。但是这些标签本身就是工业化的人造物,在该食物链的分销体系下,价格继续是生产者与消费者食物链之间所传递的信息,消费者只在乎价格,农民在意的只有产量,廉价食品经济继续自我强化。食品杂货业界为有机“全食”创制了区域性配销系统,但这些系统无法支持小型农场。大型仓库为几十家连锁店统一进货,迫使他们只能和大型机械化农场做生意。
当作者造访生态农场时,农场主也反映政府所制定的公共政策,并不检测农产品的细菌残存,而是要求一套昂贵的高标准设施,这些规定恰恰更有利于大资本。在作者的观点中,“有机”的原意是要让人的饮食方式能更符合自然运作的逻辑,建立一条适合生态系统的食物链,由此衍生的基本准则包括:无化学药剂的农业,反资本主义食物合作社和反精致烹饪,这种自然逻辑与“将廉价能源视作理所当然的前提”的资本主义逻辑无法兼容。在这个意义上,“全食”超市是一个将“工业化生产”与“有机”概念相缝合的产物,它的底色仍是为资本逻辑服务的现代农业。
3
现代杂食者的辩证法
在最后一部分,作者尝试在不利用工业化的食品供应体系的情况下,以个体的经营和智慧做一顿饭,为此他给自己设置了诸多限制,譬如:所有食材都需自己亲自狩猎、采集或是种植得来;所有食材必须是当季新鲜的食材;自己亲自下厨等等。接着作者呈现了自己如何收集和制作食盐、捕捞鲍鱼、料理蚕豆、采集野生酵母菌和狩猎野猪等经历,可以说这是一套微观的从食物到餐桌的简短食物链。事实上,迈克·波伦无意于给出一个可复制的现实方案以对抗产业化食物体系,但是纵观全书的脉络,结合他个人的实践,我们仍然可以给出一个思考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杂食者的辩证法。
“人要面对杂食者的两难”,这是现代人思考食物体系的正题。
人毋庸置疑是杂食性动物,区别于专一食性,对于自然界中的事物是否可食本身就是进化要解决的巨大难题。除了表面的颜色、气味、感觉等表观特点,自然界的事物是否可食是一个后验的体验,是一个需要辨别、记忆、回溯、反思的能力才能完成的动作。更重要的是,作为群居的杂食者,人类对于食物的选取也需要知识的传递,通过这种传递,个体也被活动和社群所建构并逐步社会化,这是一种食物所带来的人类的演化适应,换言之,饮食自身必然带有社会性。在这方面,作者的采猎经验,无论是采集菌类还是狩猎野猪,其实已经例证了通过实践获得的食物知识能够内化于个体,形成某种“身体知识”。
“人不必面对杂食者的两难”,这是现代人所遭遇的反题。
应该意识到现代人在超市中陷入的所谓食物选择障碍(选有机食物还是一般食物,选进口还是国产),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虚假的选择障碍,是消费主义炮制的幻想。因为“吃什么”的问题,最终是由一个社群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人在食物体系中的地位来决定的,这些处在关键节点上的问题向来是在现代人做出消费选择之前就已经被私人领域内的一小撮农业综合企业和加工业所选择好了的。这一点,在本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种植玉米还是饲养牲口,商人必须从利润最大化的角度来思考和决定我们的食物体系,多数人作为食物体系的边缘只能承担资本做决定所产生的社会成本。正因如此,现代人的所谓选择障碍与作者所描述的原始社会的食物选择障碍是根本不同的。在作者的叙述中,原始社会的人类虽然承担着各种采集食物的风险,但同时人通过这些活动,在客观上与食物的生产、采集、运输、保存和烹调等等食物链保持着密切的社会联系,但现代个体面对食物体系背后的原料问题、生产问题和分销问题却几乎是无力的。
“人要面对杂食者的两难”,这是现代人思考食物体系的合题,它的重点全在一个“要”字上,凸显的是人对食物体系进行主体性改造。
迈克·波伦近乎是以一种个人行动的姿态完成了他反资本主义的“完美一餐”,但是他的个人行动显然不是重点所在,有意义的是人一旦脱离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供给体系,才开始真正作为一个现代杂食者面对和化解实际的食物选择障碍,并在这个过程中重建主体性。这不代表人人要效法迈克·波伦成本高昂的个人行为。它只表明“杂食者的两难”这个问题,只有当现代人真正意识到少数人不可以代替自己决定食物体系并有权力行动起来重建食物体系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时,才会褪去虚假并自己浮现出来。因此,主要的问题不是避免“杂食者的两难”,而是积极创造出让“杂食者的两难”这个问题真正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的条件,让社会集体参与并民主决定一个食物体系的原料采集活动、生产活动和分销活动应该如何组织,从而真正回答“吃什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