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读诗笔记:禅与儒,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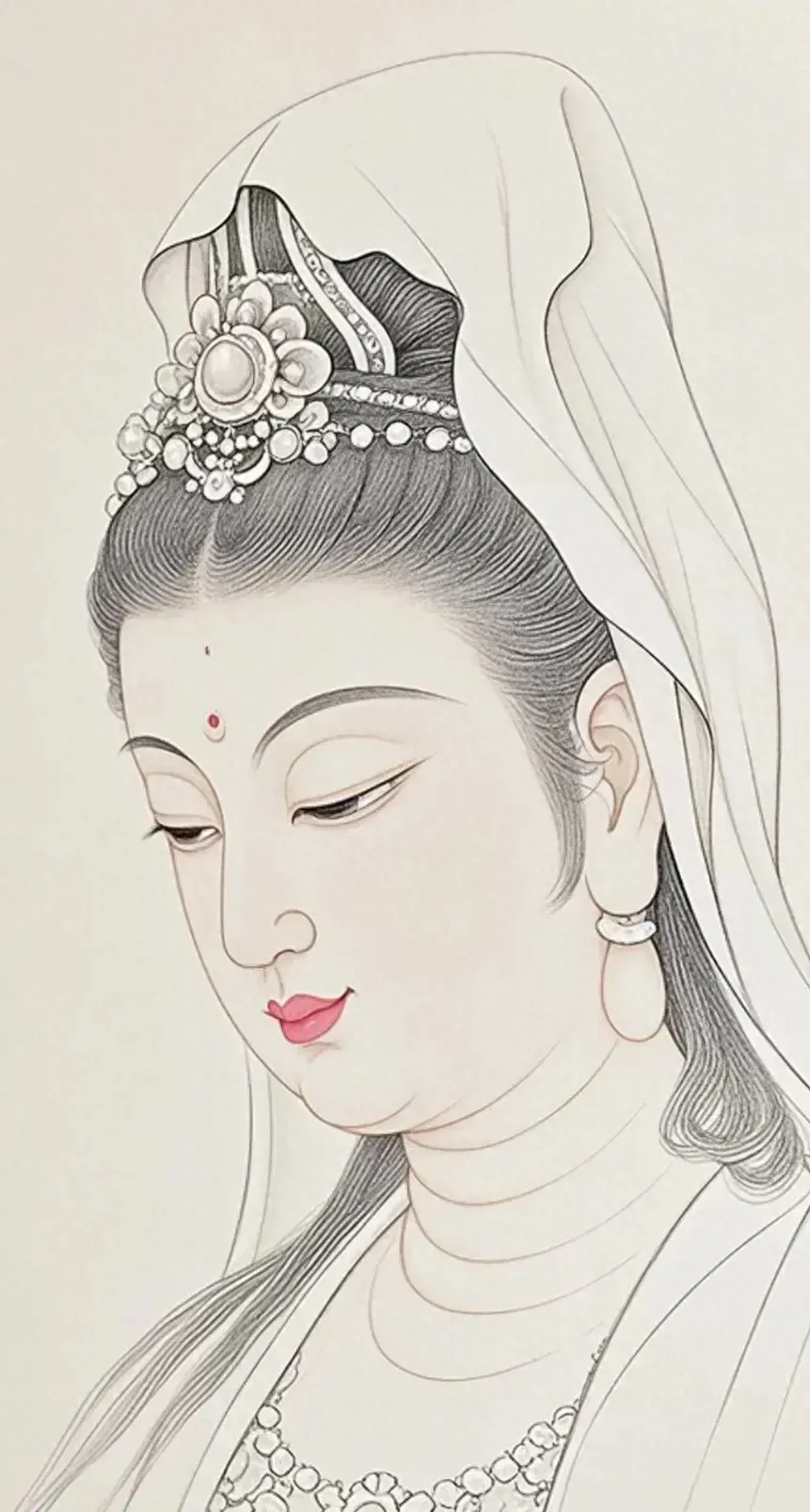
尽管唐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高光时刻,但并非无可挑剔,相反却大有重新总结的地方。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刻在马克思墓志铭上的名言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总结唐诗。
唐诗读多了就会发现,其领军人物杜甫和李白代表两种认识路线。
李白的认识论的基础是佛学中的禅宗,禅宗是魏晋玄学与西传佛学结合的产物,禅宗本质是以私念为核心的虚无,其特点是着眼于无关痛痒的解释世界,而不着眼于需要牺牲的改变世界。禅宗因此在晚期也走向堕落。“中唐至北宋,禅宗进入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它在北宋被推向高潮并弥漫于知识分子中。北宋文人多以“横看成岭侧成峰”“也无风雨也无晴”——实则是“游移于两端的毫无定见”或曰“不担当”——的玩世或曰“躺平”心态对待国家和政治问题,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毛泽东与康生、吴江等谈哲学问题,他说:“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禅宗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
明末清初大学问家顾炎武说得更绝:“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他甚至认为北宋理学完全与孔孟儒学无关,他说:“‘《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学者认为,这“一方面是提示这种这种‘禅学化的理学’的根源可以追溯至程门高第,另一方面则是强调儒学之‘本’是孔子,应当根据孔子的学说来衡量后世学术理论的正误与价值,而不能本末倒置。”
杜甫、陈子昂与韩愈是积极的儒家路线。韩愈是反佛的,唐朝反佛是北魏崔浩反佛路线的继续。北魏的崛起,崔浩反佛立了大功;北宋的灭亡,禅风泛滥当为首因。 如果说玄学在东汉之后还有解放思想的作用,那么到唐时与它禅宗合流并与禅宗一道滴水穿石瓦解着中华文化中的斗争意识。鲁迅笔下的“阿Q”,可以说是禅宗的极端堕落表现。可喜的是,就在鲁迅先生发表《阿Q正传》的同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此后,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禅诗多出于知识分子中那些在社会实践中失败并因此向往自然山水、逃避实践的失意“隐士”。这类诗歌的特点是回避中国传统文化中“格物致知”“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些在确定的时空中确定具体真理的科学方法,用多元或相对时空来否定或淡化乃至“空化”人的实践探索真理的可能性、必要性、必然性。比如李白在《古风》一诗开篇盛赞“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可到结尾处一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又否定了秦王的实践意义。李白入朝前高呼“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赐金放还”后就萌生“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消极退意。
毛泽东知道李白禅心可以作诗但不能成事,说:“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就说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
杜甫青年时也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其诗贯穿着很强的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仕途受挫后,杜甫并没有采取李白那种自暴自弃的人生态度,而是积极总结经验,探索条适合自己特点的实现抱负的人生道路。仕途受挫、离开凤翔入川后,书载杜甫“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其诗歌日臻高峰,更接地气的作品如《羌村三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春夜喜雨》及“三吏”“三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名诗,就是杜甫离开凤翔到四川后写的。
至北宋,从唐以来的“主观唯心论”发展为“客观唯心论”。以苏轼为重要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遁世心态更是登峰造极。苏轼那种“游移于两端的毫无定见”的学风使北宋的意识形态深陷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逝世。真是国家不幸诗人幸,26年后即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南下攻取北宋首都东京,掳徽、钦二帝,诗词歌赋“大文豪”扎堆的北宋,在靖康国耻中君妃的凄惨呼号中灭亡。
毛泽东说:“知识分子一遇麻烦,就爱标榜退隐,其实,历史上有许多所谓的隐士,原是假的,是沽名钓誉,即使真隐了,也不值得提倡。像陶渊明,就过分抬高了他的退隐。”
郭沫若说苏轼是“游移于两端的毫无定见的浪漫文人”。陆游对知识分子的这些缺点认识是清楚的,他说“堪笑书生轻性命,每逢险处更徘徊”,将陆游这句自嘲诗用于评价苏轼之类的文人也是贴切的。
笔者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主张“诗以载道”的路线,并不认为人类实践是一场“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历史虚无,相反它是“历史是非石不动”即不容颠覆的唯物主义存在。在本诗集收录的诗歌多贯穿着这样的认识。我在《鸿毛泰山话不闲——读蜀汉史有感》一诗中表达了这样的创作观:
武侯西去昭烈远,格局泥云事后看。
历史是非石不动,鸿毛泰山话不闲。
【文/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