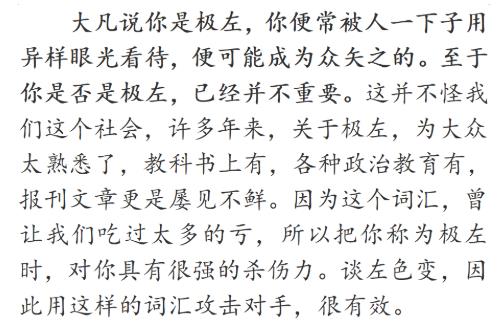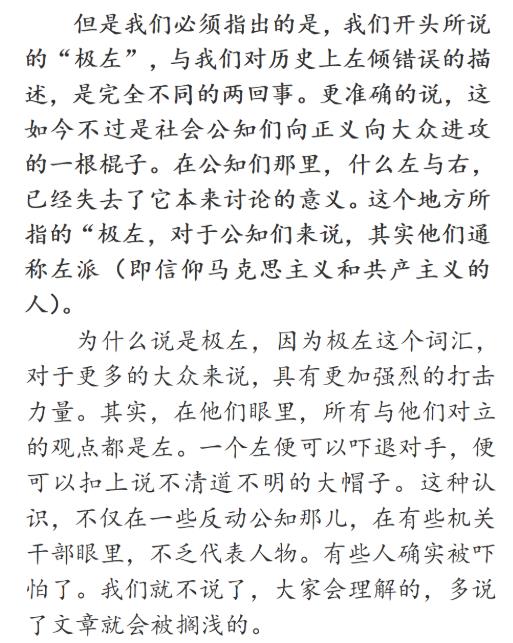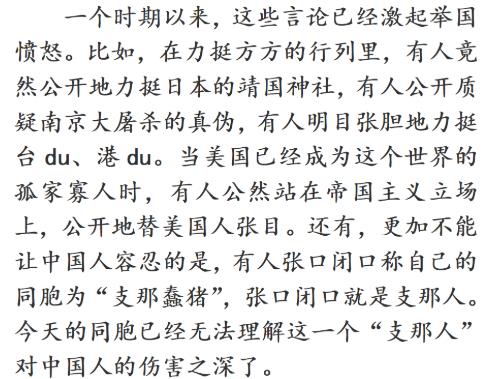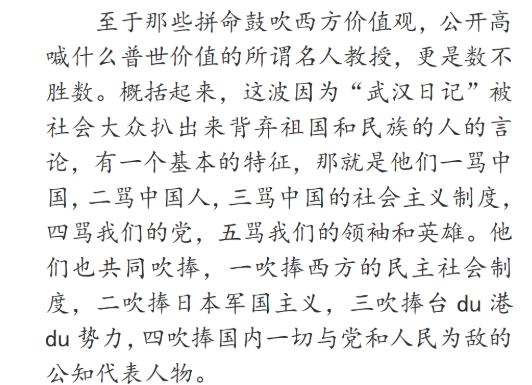陈先义:岂能用一句所谓的“极左”绑架一个伟大民族的灵魂
最近,一个词汇在公知们的话语里频频出现,这几乎成了一种向社会大众进攻的最有效的武器,成了恐吓社会正义言论的一根毒棍。这就是常被一些公知们用来咒骂群众的两个字——“极左”。
历史上,我们党确实犯过多次“左”的错误。左,无外乎三种情况,一种是时机不到的急躁冒进。二是四面出击、到处树敌,使自己陷入孤立。三是动辄上纲上线,对人一棍子打死。党史上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直到解放后的多次政治运动,都曾与“左”关联。我们确实都吃过“左”的亏,上过“左”的当,特别近些年出现的极左这样一个词汇,让社会确实深恶痛绝。
如果说这些意见还可以视为泼妇骂街的话,有些著名公知的言论,那可不是骂街了,那是歇斯底里地在咒骂我们的共产党、咒骂我们的民族、侮辱我们的国家、在发泄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大仇恨了。
一位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老者愤怒指出,一听到支那这样两个字,立即便怒火中烧,便浑身发抖,简直像挖心一样疼痛,谁才称我们是支那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啊。他是见证者之一,一听到这样两个字,立即想到当年日本侵略者挥着屠刀,高喊着“支那猪”,把屠刀砍向中国同胞的凄惨境况。那个“支那”是日本强盗对我们所有中国人的专称啊。可如今,这样的称谓,不是出自日本人之口,而是出自中国学者、中国名人、中国大学教授之口。还有更甚者,有人公开的在文章中骂我们人民军队的英雄都是一个虚荣心,都是一种狂热,这样的公开言论,居然在媒体上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其实每一个中国人回顾一下,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只要你说我们的党几句好话、公道话,便很可能有人嘲讽说你“左”;只要你说些从内心怀念尊崇毛泽东等领袖的话,同样也有人会说你“左”;只要你说些歌颂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在文章中引用党的当代领导人的经典之论,便会有人讥讽你,说你这是你老保守、不开窍、不识时务。什么叫开窍?什么叫赶潮流?那就是像前边那些人一样,发牢骚,说些对党和国家不满的话,弄些似是而非的花边新闻,嘲弄一下党的领导,便立即会被当作有思想,深沉,独立思考。甚至有些骂领袖的言论,也没有受到任何阻挠和制止。等等,每一个当今社会的人恐怕都有深刻体验。
怕人说自己“左”,不仅一般群众这样,就是我们负责意识形态的领导和机关干部,也同样如此。对这样的现象,北京大学老教授钱理群非常反感,他有一段著名的讲话,称这样的人为当今社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是一个极其精妙的概括,什么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就是只考虑个人利益,精于算计,利用自己的权力捞好处,而对集体对国家对他人毫不负责。为什么有人说,刚毕业的三十来岁的人不像前边的贪腐者,有什么过渡期,他们一上来便开始利用公权力大捞好处。国家机关反腐败中抓获的那些小处长们就是明证。这是这些年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这种现象正在危害着我们的国家。
钱理群先生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钱先生的这个概括,我认为入木三分。
比如当下社会对于“武汉日记”和大学右翼思潮的泛滥,社会千呼万唤,就不见主流媒体表态,真是沉得住气。说穿了,就是有些人不作为,就怕别人说自己“左”。
一个左字,竟能混淆人们的是非判断?竟能绑架一个民族的灵魂和思想?竟能在恶潮翻滚时出现主流“万马齐喑”的局面吗?这个事仔细想来让人有几分可怕。一个民族的正义精神,不能让一个莫非有的污蔑之词给绑架了、吓退了。
敌人是谁?就是这些公开站在帝国主义、买办垄断资产阶级一边,为被打倒和推翻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招魂的人。就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时刻希望变天的人。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是《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阶级斗争做出过明确的定义:说急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阶级斗争依然存在,有时甚至是非常激烈。遗憾的是,这些年,我们相当一部分同志只记得“急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却忘记了“在一定时候还是相当激烈”这句关键性的表述。今天,我们面对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局面,只有用马克思那句《共产党宣言》中的论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来解释,否者,我们无法对当下的复杂局面做出理论表述。
说到这个话题,也许有人会问,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不是已经定性为扩大化的政治运动吗?不错,那是一场扩大化的政治运动,但是,历史也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去分析。扩大化是错误的,但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党的猖狂进攻,当时也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我们不能在批评扩大化的同时,也把那些对党猖狂进攻的言论和行动一并从历史勾销,那是勾销不了的。
在此,为了对历史进行有效说明,我们有必要对这段历史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1957年4月27日,针对党内领导干部出现大量的贪腐现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保持党不变色和防止和平演变的目的出发,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号召党外人士对党政干部的错误进行批评。欢迎各界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开展整风。这个运动总的是好的,但当时也有一些领导干部抵触情绪很大,认为革命一辈子,现在享受一点特权,便受到严厉的批评,对这样的批评非常不理解。但总的来说对党的队伍建设是一次非常大的促进,是为了防止出现李自成的悲剧。但是,历史就在这个期间却出现了异常,苏共赫鲁晓夫集团由于否定了斯大林,国际上迅速爆发“波匈事件”,于此同时,一股向社会主义进攻的高潮兴起。
但是,包括毛泽东主席本人在内,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做了比较严重的估计,加上在前期整风运动中挨整的党的一些干部,本来怨气很大,对此前提意见的人也开始进行打击报复。毛主席本人也没有想到,这场运动被扩大化了。客观讲,毛泽东对扩大化的问题觉察后,是非常担心的也是坚决不同意的。就连邓小平后来复出后也坦率承认:“1956年起自己就担任党的总书记,是在领导核心之中。那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我也有份。”这个话非常坦诚,也是实事求是的。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反右派斗争做出了明确的界定:1957年党中止整风,被迫进行反右派斗争,对资产阶级的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成右派,造成了不幸后果。”《决议》这个论断是正确的。但是遗憾的是,许多年来,我们的舆论只记住了“扩大化”这个概念表述,却忘记了右派分子要党交权、向党进攻这样一个载入史册的历史事实。
毛主席本来想通过整风整肃党内官僚主义,是党内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没想到反右使一部分人的官僚主义继续增长。于是才有了后来以防变不变质为目的许多运动。
反右的历史,使我们想到今天,同样以知识分子为主要人员,同样也是发泄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满,但是,今天的公知言论,比之1957年要露骨的多,要直接的多,那时候,尽管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但还没有直接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招魂,即使有,也是有所收敛的。但是今天却不同,有些右翼居然公开地咒骂国人,咒骂我们的党,咒骂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实事求是地说,在这次各种右翼出卖国家和民族尊严的狂吠中,面对一顶又一顶的右翼帽子,如“极左”、文革余孽等等,我们的年轻人的表现让我们倍感欣慰。这是完全崭新的一代,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和各种运动,他们甚至不理解极左、极右这些词汇是怎样的一种政治含义。但他们知道,那些公知们对他们曾经教诲的普世价值、那些外国月亮圆的振振有词的训诫,那些动辄让他们去外国接受民主自由的教导,在一场重大灾疫面前,他们忽然发现,他们在学校曾经奉为灵丹妙药的言论,那些不断用各种机会丑化国家民族的语言,如今看来都是骗人的鬼话。
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向这样的青年学习,少一点“精致利己主义思维”,人人都来关心国际风云,人人都来关注国家发展,人人都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绑在一起,而不要被什么极左这样两个字绑架,那样我们的国家将大有希望。
【作者介绍:陈先义,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国家重大题材影视作品审查专家组成员。原籍河南兰考,北师大毕业,曾任后勤学院教员、解放军报文化部主编,2011年退休,现从事重大题材文艺研究。著有《为英雄主义辩护》《走出象牙之塔》《捍卫我们的英雄》《追寻丢失的精神》等十余部,另有报告文学、散文集《横槊东海》《战神之恋》《在统帅部当参谋》《中国军人看世界》等作品。其作品曾多次获中国新闻奖政府一等奖,全军文学创作一等奖。曾获全军具有突出贡献拔尖人才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