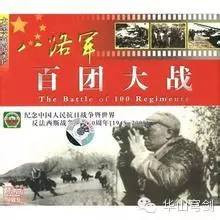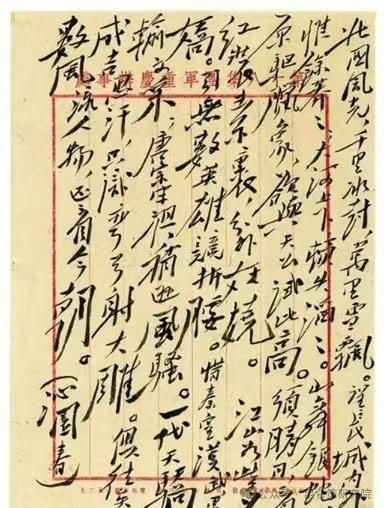三人谈|为人民赋形,为时代作证——《黑与白》的主题分析

主持人:乔麦(某大学学报编辑、社会学讲师)
与谈人:朱亚芳(文学硕士)
小卓(在读研究生、曹征路-刘继明研究中心兼职秘书)
学术指导:孔庆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曹征路-刘继明研究中心主任)
时间:2023年4月20日
乔麦:著名作家刘继明的长篇新作《黑与白》还未问世,我看到网上不少人就在关注期待,新书海报也出来了,著名学者汪晖、黄纪苏、孔庆东、摩罗、贺雪峰、郭松民“联袂推荐”,有一种未出先热的节奏。很多地方都在转载滠水农夫那篇《人间正道是沧桑——读长篇小说<黑与白>》,滠水农夫是网络上比较活跃的一位左翼文化批评家,可以说是《黑与白》的第一读者,也是最早写文章评论这部小说的人。咱们读作品晚一点,搞这个“三人谈”也不是为了蹭热度,主要还是想对作品进行一些解读,算是义务为读者充当“导读员”吧。
小说我已读完一段时间了,还写了几千字的笔记。两位都是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正好借这个“三人谈”检验一下在学校里学的理论知识。为了避免讨论过于松散,咱们每次确定一个中心议题,尽量不要跑题太远,今天的话题是:“为人民赋形,为时代作证——《黑与白》的主题分析”。
之所以首选这个话题,是因为看到滠水农夫《人间正道是沧桑》里一段话:“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为人民而歌哭,发出人民的心声,是先进知识分子的天然职责。尤其是当今的条件下,有抱负的作家艺术家如何坚持人民的主体性,为人民而创作,为时代证言;如何坚守和捍卫属于人民大众话语权,无疑都是事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大课题。正是从这个角度讲,刘继明老师的《黑与白》为此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不到二百字,“人民”这个概念就提了七次;另外,刘继明在《黑与白》的后记中谈到:“我忠实地记录下了自己看到,经历和思考的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份时间的证词。”因此,我认为,用“为人民赋形,为时代作证”来概括《黑与白》的主题是比较恰当的。
开场白就到这儿,下面谁先说?
朱亚芳:我先说两句吧。刚到一个新单位不久,很难有整块时间看书,这么长篇幅,又是在电脑上读的,断断续续,前后花了差不多三个月时间。总的感觉是这部小说人物众多,结构复杂,扑朔迷离,让人仿佛进入了一座迷宫,一时半刻很难理出头绪来。以前读《平凡的世界》,《金光大道》,都是鸿篇巨制,也没有《黑与白》这样复杂。
总的感觉有两点:一是《黑与白》的容量超大,无论从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刻画人物的复杂性,还是叙述时间的长度,都远远超过了刘继明的另一部长篇《人境》。评论家曾经把《人境》比喻为小说的“大象”,其实,《黑与白》才是真正的大象,跟它相比,《人境》最多是一只老虎。这不仅从体量上讲,而且是从主题、生活和人物来讲的。我刚才说仿佛进入了一座迷宫,就是这个意思;二是在艺术和思想取向上,《黑与白》比《人境》走得更远。如果说《人境》只是略略偏离了主流文学的轨道,尽管也有“后撤”,但后撤的幅度并不太大,许多方面仍然保持了新时期文学的叙述框架和美学范式,《黑与白》呢,则完全逸出这种框架和范式,走上了一条迥然相异的道路。曾经有评论家认为,《人境》有一个很大的野心,就是重新书写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对这段历史做一个总体的评价。但《黑与白》不仅重新书写了“新时期以来的历史”,而且书写了从辛亥革命到21世纪初叶整整100年的中国历史。所以,我觉得《黑与白》不仅是为时代作证,还是为历史作证。
我先说这些。
小卓:我接着亚芳姐的话讲。其实,为时代作证,就是为历史作证,因为时代是进行中的历史,历史是过去的现实。主持人将“为人民赋形”作为今天的议题,切中了《黑与白》的一个重大主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人民”是一个跨越两个时期的中心词,但仔细辨别可以发现,相对于“前三十年”的阶级政治概念,“后四十年”主流语境中的人民早已蜕变为一种超阶级的概念。
前不久,刘继明在《人民文艺、文革文艺和“纯文学”》的讲座中指出,“在月入不足一千的穷人和年收入动辄以亿计如马云、柳传志这些富豪同属于人民范畴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业已废止,人民概念越来越像一块被人嚼过无数次的口香糖那样空洞暧昧和失效。”从这个意义上说,刘继明的“野心”不仅是要为时代作证,还要重新厘定人民的含义。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咱们在后面结合作品具体讨论。
乔麦:小卓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是人民?这个问题在“前三十年”似乎不言自明。因为宪法上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75宪法上还写有“无产阶级专政”,82宪法改为“人民民主专政”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人民是指工人、农民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文艺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意涵呈现出普泛化的态势,逐渐与民众、公民、国民、市民之类的现代政治概念趋同,成了一种超阶级的民族共同体概念。
上世纪捌玖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曾经十分流行“市民社会”的概念。在古代西方,市民社会是指市民的共同体,中国古代和欧洲中世纪,不存在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市民社会。中世纪末期,出现了从事商品经济的市民阶层,即第三等级。从19世纪开始,市民社会被用来专指从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种种政治性支配下获得解放的近代市民阶层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一个“脱国家脱政治的领域”。调整市民间关系的法被称作市民法,是由私人所有、合同、法的主体性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黑格尔将市民社会看作是私人利益的体系,认为个人是市民活动的基础,也重视在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的作用,认为市民社会依附于国家。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把市民社会看做是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物质交往关系和由这种交往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生活领域。可见,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指资产阶级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这个概念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流行,跟市场经济改革开始后,中国社会越来越跟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趋同存在着密切关系,所以才出现刘继明老师所说的“月入不足一千的穷人和年收入动辄以亿计如马云、柳传志这些富豪同属于人民范畴”,两种以前处于敌对阶级的人群共享“人民”概念的现象。这样一种变化,表征了共和国前后两个时期的巨大裂缝。这个裂缝是如何发生的?文学应该怎样揭示这一变化的过程?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很少面对,甚至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
朱亚芳:乔老师这个梳理很重要。当人民不再用阶级分析框架去界定,就会成为资产阶级思想家眼中“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一样的超阶级共同体,而这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行为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的论述是背道而驰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黑与白》的主题是“为人民赋形,为时代作证”,就是指刘老师在这部作品中试图重新采用被主流文学丢弃已久的阶级眼光来描述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在具体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探讨一下当代文学中人民主体是怎样一步步退却、虚化和偏移,逐渐沦为一个失效的概念的。刘继明曾经在《走近陈映真》一文中讲到一件事,台湾著名左翼作家陈映真和中国大陆作家阿城在美国开会碰到一起,聊天时陈映真说文学应该关心人民,阿城却用讥诮的语气说,我就是人民,我关心自己就是关心人民啊!据说陈映真听了很尴尬,讪讪地走开了。这个故事很有反讽意义,说明在中国主流文化精英们眼里,“人民”这个词早已经被“个人”彻底消解和取代了。
在新时期文学谱系中,90年代“纯文学”最大的“功绩”,是通过个人化写作(包括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和女性主义写作),使个体在挣脱阶级话语的同时,实现了人的主体性建构,同时,也使曾经作为政治共同体概念的“人民”成为了一具空壳,这是当代文学史课堂上教给我们的权威叙述,也是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我们从新时期文学中塑造的“人民”形象看到,如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刘恒笔下的城市小市民张大民,以及赵本山、范伟小品中的农民形象,大多愚昧落后、逆来顺受、插科打诨、滑稽可笑,如同古装剧中的小丑,同前三十年文艺作品中人们熟悉的农民形象,如《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艳阳天》中的萧长春,《李双双小传》中的李双双这类勇敢质朴、刚健清新、具有创造历史的冲动和主人翁精神的人物形象构成了强烈反差。有人说,新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工人农民形象更接近鲁迅笔下的闰土和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这也表明,“人民”概念的蜕变不仅使人的概念发生了蜕变,也使人所属的阶级或阶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蜕变,“革命以后的岁月回到了革命之前”。
小卓:这种人物形象的蜕变,在电影电视剧中表现得更加严重。你现在只要打开电视,随便看一部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电影电视剧,里面的主人公不是地主乡绅和所谓民族资本家,就是少爷小姐,他们一个个义薄云天,光彩照人,比起样板戏中的工农兵形象一点不逊色,而工人农民扮演的都是那种可怜可笑的奴才小丑,跟在东家和少爷小姐后面弓着腰说“是是”,满脸谄媚相,如同清宫剧中只会在主子面前说“嗻”的奴才太监一样。前些年看电视剧《解放》,整个剧情都是中共领袖们和民主人士大资本家在协商建国,曾经做出了巨大牺牲的工人农民连影子都很少见到,即使偶尔出现一下,也是无足轻重的“路人甲路人乙”,仿佛新中国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似的。这种对历史的肆意阉割和颠倒特别让人无语。什么叫历史虚无主义?这才叫历史虚无主义!前几天从《火星》网刊中读到一篇文章《被先烈们推翻的“少爷”又回来了》,作者针对社会上称“少爷公子”蔚然成风的现象,义愤填膺地说:“我们祖辈以前碰到这种情况尚且还知道骂一句‘扒皮’,今天倒好,咱们这代人有些直接上去捧‘少爷们’的臭脚,直呼自己是奴才,摇尾乞怜,求得两口残羹。”这就不只是历史虚无主义,而是现实“反智主义”了。
《黑与白》中塑造的“人民”形象,与上面所说的那些文艺作品截然不同,用滠水农夫的话说,“它完全是站在中国占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立场,对社会历史发展进行了深刻剖析,用刘继明的话说是‘努力揭示出被各种强势和流行话语遮蔽、扭曲和阉割的现实’,因而这样再现的现实就必然与各路精英权贵眼中笔下的现实不一样,甚至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说,《黑与白》不仅是要为面目模糊不清的“人民”赋形,还要给“人民”铸魂,“将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
乔麦:《黑与白》中描写的“人民”,的确跟新时期文学中常见的那类形象不一样,虽然他们也都是被抛弃和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但没有被处理成闰土和骆驼祥子一类底层劳动人民在旧中国三座大山压迫下愚昧麻木、逆来顺受的悲苦形象,而是面对不公和黑暗势力,充满了斗争和抗争精神。例如骆正,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解放战争中从事过地下工作,新中国建立后成为了一名新闻工作者,为了查找出导致未婚妻在内的东江省委领导和军区总医院一百多名干部战士牺牲的“凤凰岛血案”的叛徒,他向有关部门检举涉嫌叛变的老领导宋乾坤,为此断送了自己的仕途,坐了好几年牢,出狱后,被当做精神病人,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当年在烈士墓园做出的“一定要查出叛徒”的承诺。与此同时,他对因被资本集团开发失去土地而上访的凤凰岛居民给予了全力以赴的帮助,并身受重伤,直至去世。这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共产党员,虽然在小说中占的篇幅不多,但给人印象很深。
还有王胜利,他曾经率领解放军攻城部队和骆正一起将五星红旗插上大江市国民党军城防司令部的楼顶,两人是共过生死的战友。因伤致残后,王胜利转业到地方工作,先是担任公社人武部部长,文革期间降职担任砖瓦厂厂长。这个曾经的战斗英雄满脑子革命英雄主义情结,不仅经常到学校讲战斗故事,还给儿子取名“王成”——电影《英雄儿女》中的主人公。他就任砖瓦厂厂长时向公社革委会立下军令状,要在五年之内让公社全体社员住上砖瓦房。但未满五年,他就从砖瓦厂厂长位置上卸任了,接替他的是副厂长巴光明。这个人在担任采购员时就损公肥私,捞了不少好处,当上厂长后更加变本加厉,一边拿厂里的钱“孝敬”上级领导,一边以“改革”之名,不断涨价和解雇工人,几年工夫,就把好端端一个“社办企业”搞得连年亏损,连职工工资都发不出来,他自己却先富起来,不仅供儿子巴东自费读大学,还在城里置办了好几处房产。面对巴光明的贪婪,已经离休的王胜利带领砖瓦厂工人向上有关部门举报,给老首长洪虎将军和老战友骆正写信反映,终于把巴光明拉下马。
这两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刚正不阿、嫉恶如仇,这样的人物形象在“前三十年”文学中十分常见,那时候叫跟“坏人坏事”和“阶级敌人”作斗争。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遗产的承续,或者说,几近失传的革命精神在他们身上发扬光大了,尽管是以一种悲剧的方式,但惟其如此,才更加令人感动、引人深思。
朱亚芳:新时期文学中的人物普遍缺少历史感,被新意识形态格式化了的,往往直接“对标”新中国建立以前的民国时期,人物的性格和行为显得荒诞怪异和匪夷所思,给人一种历史幽灵重现之感。因此,放在新时期文学人物谱系中,这两个人物显得十分特别。新时期作家们都不屑于刻画这一类“过气”的人物,即使在“底层文学”的许多作品中,也都热衷于渲染甚至赞美苦难,很少触及造成苦难的社会根源。因此,这样两个充满“斗争精神”的人物,不像是来自新时期,而像是来自“前三十年”;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对背叛共产主义信仰、损害社会主义的行为,都是充满“斗争精神”的。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问姓资姓社”,都在闷声发大财,谁富谁英雄,谁穷谁英雄,谁还讲“阶级”和“斗争”呀,谁讲谁就会被打成“极左”,就像小说中的骆正那样,被当成“三种人”和精神病人,身边人都对他避之唯恐不及。
小卓:现在许多维权作品中的主人公也“充满斗争精神”。
朱亚芳:但骆正和王胜利跟维权题材作品中的那些人物不同,前者的“斗争”,仅仅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后者的“斗争”有更高的“理由”——阶级的整体利益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这是有本质区别的。比如《黑与白》中的另一个人物郭文才,也在同黑恶腐败势力“斗争”,但他的斗争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一块手表,最后付出了沉重代价,入狱六年,这跟那类维权题材作品是一样的。
另外,我补充一下乔老师前面的发言:跟骆正和王胜利相似的还有一个人,老校长,这个人的父母和姐姐都在“凤凰岛血案”中失去了生命,他的信仰来自骆正留下的一本《共产党宣言》,他担任凤凰小学校长勤勤恳恳,把学生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几十年如一日,包括带领凤凰岛居民为保卫自己土地坚持维权斗争,都得益于此,临死之前,他面前还摆放着那本《共产党宣言》。小说通过田青青的视角这样写道:“我考上大学后第一个学期,刚放寒假,就回凤凰岛去看老校长,可一走进石屋,就看见老校长趴在那张石桌上,看上去死去了好长时间,整个人都僵硬了,面前那本《共产党宣言》摊开着,书里还划着一条条粗细不一、弯弯曲曲的横线……”这是《黑与白》中最让我感动的一个场景,读到这儿,我眼睛都湿润了。
小卓:我在想,《黑与白》中骆正、王胜利和老校长都是次要人物,作家为什么要不惜笔墨刻画这几个熟悉又陌生的“人民”形象呢?我觉得,除了塑造“有历史感人物”的冲动,还跟主要人物的塑造需要有关。这三个人跟“男1号”王晟都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王胜利是王晟的父亲,骆正是王晟的父亲王胜利的战友,而老校长与王晟暗恋的凤凰小学教师田芳情同父女。在《黑与白》中,王晟是一个异常复杂的人物,复杂程度超过了《人境》中的马垃。他身上集中了“新时期”的诸多精神特征,刘继明在《时间的证词》中说过,在王晟的成长过程中,始终存在两个“自我”或者叫“双重人格”,一个是来自父亲王胜利的革命教化,一个是来自导师郎永良的“自由主义”熏陶,两股力量在他精神深处互相拉锯,使他在“个人”与“人民”之间徘徊不定。这种对比式人物关系在《人境》中也曾出现过。王晟考上大学后把父亲取的名字“王成”改成“王晟”,就是一种再明显不过的寓意,而王胜利、骆正和老校长这三个仿佛革命年代的化石,成了他最终挣脱新意识形态束缚的一股重要合力。
乔麦:小卓的这种解读很有意思。从写作角度,每个人物都是在跟其他人物的对比、映衬和互相砥砺中塑造出来的,用刘继明的话说,具有某种“功能性”,在主人公王晟的成长过程中,骆正、王胜利和老校长在不同的阶段都对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包括另一个主要人物顾筝,刘继明自己也承认,最早构思时,也是将她作为王晟的陪衬人物设计的,只不过随着写作的展开,人物逐渐获得了“自我生长”的力量。在《黑与白》塑造的“人民”群体中,骆正、王胜利和老校长作为老一代,都像是为年青一代“人民”的出场所做的一种铺垫。如果没有他们,王晟、顾筝、田芳、宗天一、栗红以及更年青一代的宗小小、田青青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朱亚芳:从人物谱系角度分析,《黑与白》中的“人民”可以分为老中青三代,骆正、王胜利、老校长为老一代,王晟、顾筝、田芳等人为中年一代(在小说第一部和第二部前半部分他们还属于青年,从第二部后半期到第三部,则已经属于中年了),田芳和宗小小为青年一代,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民序列”。此外,《黑与白》中的“人民”还可以分为“抗争的”和“被剥削压迫的”两类,前面提到的是第一类,如凤凰镇的上访群众,东钢集团“聚众滋事”的下岗工人,以及卢佳、梦菲、程蕾这些因生活所迫卖唱和卖身的“被侮辱与损害”的底层社会女性,属于第二类。再加上作为这“人民”对立面存在的宋乾坤、武伯仲、杜威、洪太行及巴光明、巴东父子等权贵利益集团和腐败黑暗势力,使《黑与白》中的社会镜像凸显出壁垒森严的阶级分野。这时如果我们重温马克思恩格斯“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论述,一定会觉得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然,我们这里使用的“人民”,不是新时期以来主流叙事中的“人民”概念,而是借用了“前三十年”关于人民的定义,也就是工农兵以及具有共产主义信念和“创造冲动”的历史主体,这更符合刘继明对人民的定义。在《黑与白》中,这个人物谱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序列,在这个序列中,人物的情感、精神和行为都具有清晰的历史和现实依据,无论是宗天一临死前委托王晟举报武伯仲,还是顾筝最终同栗红携手,将凤凰岛腐败大案曝光,以及田芳、宗小小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都是在上一代人影响下做出的抉择,其中的逻辑一目了然,不像新时期以来大多数小说中的人物那样充满非理性冲动,要么缺少历史感,要么对历史进行单向度的简化。这个“人民”序列不仅使空虚、失效和普泛化的人民概念被重新赋予了一种鲜活生动、触手可及的样貌,而且将新中国前后两个时期之间的巨大历史空白和裂缝重新缝合起来了。
乔麦:在《黑与白》的叙事结构中,历史不是过去式,而是呈现出一种现在时的状态,如同装置艺术那样,被植入到正在行进的当下,同现实展开了激烈紧张的对话,这种结构方式,同样在《人境》出现过,现在又出现在《黑与白》中,人物关系更复杂,结构更宏大,叙述犹如行云流水,更加自由、舒展。正如滠水农夫所说,“作家运用高超的艺术技巧,以数个紧密联系的中心人物发散构成严丝合缝的人物关系网,叙事笔触收放自如,以社会典型事件为结点,在长线条勾画辅陈基础上,集中展示各色人物表演的舞台,张驰有度,构成宕荡起伏的故事情节。整个叙事结构又如同蜜蜂的蜂房,将精彩纷呈的人物和情节与百年中国史尤其是40年改开史巧妙融合,每个峰房既是别具一格的世界,又与整体完美联结浑然一体,显示作家极富匠心的高超建构。”
小卓:可不可以讲,《黑与白》塑造的人民形象序列,为我们认识今天这个时代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察坐标?著名作家张炜说过,如果我们不能对历史获得一种理性的认知,就无法真正理解今天的现实,会觉得一切都不可理喻。读完《黑与白》,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历史是怎样一步步走到现在,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大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刘继明才说,《黑与白》不仅是一部小说,而且是一份“时间的证词”吧!
朱亚芳:刘继明在接受狂飙学社访谈时说,《黑与白》是否超过《人境》,是无关紧要的。但我认为,无论从思想还是艺术上,《黑与白》都已经超过了《人境》。滠水农夫曾经在《底层文学的溃散和流变》中说:“从新左翼文学到人民现实主义文学,从曹征路到刘继明,他们从底层文学一路前行而来,而刘继明似乎走得更远,可以说他是在继续着曹征路和魏巍没有走完的路。”刚才乔老师说《黑与白》被汪晖等一众大咖联袂推荐,“有一种未出先热的节奏”,但我不这么看,我甚至有一种担心,正因为相对于《人境》,《黑与白》与主流文学偏移甚至背离得更远,会不会真的如刘继明预言,遭遇“不会比《人境》更好”的命运呢?
小卓:如果真的这样,也不一定是坏事啊。当年鲁迅先生在谈到左翼文学时说:“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我觉得,这段话用在《黑与白》上正合适。因为,评价一部“为人民赋形,为人民歌哭”的作品,最终也不会是什么主流文坛,而应该是人民。
乔麦:小卓给我们今天的谈话进行了精彩小结,时间差不多了,我就不再啰嗦。预告一下,下次我们谈的话题是:“《黑与白》与人民现实主义”。好,散会!
【孔庆东教授点评:谈得不错,人民性谈得比较全面。期待继续从艺术性方面多谈谈。】